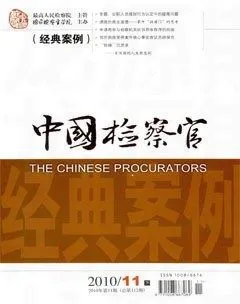如何認定信用卡犯罪中的“竊取”故意
一、基本案情
姚某于2008年11月1日10時許。陪同其同事白某到中國民生銀行北京西單支行取款機處查詢白的民生銀行信用卡的一筆錢是否到賬。查詢后,白某發現錢未到賬,于是就將卡放進錢包里離開自動取款機。此時姚某提出要幫白某再查一下。白某沒細想便將錢包給了姚某(白某之前曾告訴姚某該卡密碼)。姚某查完發現錢仍沒有到賬,就把錢包還給了白某,并順手將白某的民生銀行卡裝在自己身上,白某并未發現信用卡未歸,二人隨后離開自動取款機。姚某和白某分別后,于2008年11月1日13時35分持卡前往本市西城區黃寺大街萬家馬甸郵幣卡市場C-8093號刷卡套取人民幣11000元。后又于2008年11月6日、11月13日在黑龍江省雞西市分別從該卡內提取人民幣2700元。姚某在被抓獲后辯稱:其沒有竊取被害人信用卡。而是在幫助白某查詢后將卡“忘”在了自己身上。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姚某的行為應認定為盜竊罪。雖然姚某辯解其不是故意要將被害人的信用卡秘密竊走。而是忘在了自己口袋、后來才起意要從卡中取財。但司法機關應從客觀上推定姚某的行為系秘密竊取行為,應依照盜竊罪對其定罪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姚某的行為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姚某取得信用卡的過程首先源于被害人白某的自愿交付,后來其辯稱的“順手忘在自己口袋里”,有其合理性,或者至少不能排除該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何況,被害人的陳述并不能明確證實姚某的主觀故意,且本案也沒有其他證據能夠對姚某將卡放在自己身上時的主觀狀態予以甄別,因此,不宜強行推斷姚某具有秘密竊取的主觀故意。因此。應以信用卡詐騙罪對其定罪處罰。
三、評析意見
本案關鍵問題在于對姚某前期取得信用卡的行為如何評價,這也決定了其后來使用信用卡行為的性質是“冒用”還是“竊取”。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一)當前證據不足以認定姚某具有“竊取”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2010年6月印發的通知要求:辦理其他刑事案件。應參照該規定執行)第18條規定:對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被告人的辯解內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無矛盾。第32條規定:對證據的證明力,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從各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各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審查判斷。上述規定給司法人員明確了把握證據的方向、策略,對于那些“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證事實,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具體到盜竊罪這種“主觀方面不存在間接故意”…的犯罪而言,證據上須達到足以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積極追求竊取結果發生,且意志上不存在放任的標準。
本案中,被害人在將信用卡給姚某時,連同裝卡的錢包一起交給姚,姚聲稱其接過來查詢后,由于疏忽將錢包還給被害人白某,而將卡“忘”在自己身上。姚的辯稱是否荒謬、能否采信。需要綜合案件證據情況來分析。在案發現場,只有姚某與被害人白某二人。即只有白某的陳述能夠對姚某的供述起到印證或削弱作用。案件中,姚某將信用卡裝在自己身上、將錢包還給白某時,白某并未發現信用卡的去向,直到信用卡被套現、提現后才發現卡不在手中的事實。可以看出。白某對姚某何時占有自己信用卡的時間并不知曉,也無法分辨姚某行為時的主觀狀態是“蓄意謀取”還是“占有后忘記歸還”。因此,本案證據無法達到“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與同案犯的供述和辯解以及其他證據能否相互印證”的程度,雖然姚某具有故意竊取該卡的現實可能性,但依據此“可能”就認定姚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尚缺乏說服力,顯得不夠嚴謹、客觀。
(二)被告人的行為核心在于“冒用”信用卡
定盜竊罪還是定信用卡詐騙罪的關鍵在于:行為人是“盜竊信用卡并使用”還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其侵犯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受損害的主要是被害人因失竊遭受的財產權益;《刑法》第196條第3款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除侵害被害人的權益外,該罪行的主要危害是破壞了金融管理秩序。
本案中,被告人行為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其取得該卡后分別以刷卡套現、直接提現的方式“冒用”該卡人民幣13700元。至于姚某是蓄意謀取還是無意占有該卡,給被害人帶來的威脅不大,實際上被害人白某基于對被告人的信任曾主動將卡交給姚某。請其代替自己查賬。也就是說,假如姚某占有該卡后,未從中套現、取現,而選擇將卡歸還給白某,則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大降低。不能再以犯罪進行評價。
具體來看姚某取得信用卡的方式,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被害人白某在姚某提出幫助其查詢信用卡的情況下,將錢包(信用卡)交給了姚某,而并非姚某秘密竊取,在此階段姚某取得該信用卡是有依據的。后一階段姚某并未將信用卡放回錢包內(裝在了自己身上),而只是將錢包還給白某。此類行為應當是從行為上去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假如其并沒有犯罪的主觀故意,則其行為就不構成秘密竊取;反之,如果其有犯罪的主觀故意,對此類行為評價也有不同觀點,但在司法實踐中,此類行為一般應被認定為是詐騙的手段(俗稱為“切”),而不認定為秘密竊取的手段,即行為人不能竊取客觀上已經歸自己占有的物品。因此,結合被告人此后的使用信用卡從中套取現金、提取現金的行為。姚某的行為核心在于冒用被害人信用卡并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破壞,構成《刑法》第196條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詐騙行為。
(三)定信用卡詐騙罪更有利于被告人
實踐中對于法條和證據規定的適用,需要司法人員根據大量形形色色的案件來具體操作,因為角度不同、經驗不同、學理認識不同等原因,不同司法人員對證據的把握難免出現不同的認識。如本案當中,有些同志憑借多年的辦案經驗,認為整體從姚某的一連貫行為來看,姚某的辯解過于荒謬,此時單評價姚某的“冒用”信用卡行為,而不考量其前期“竊取”的罪過,難免有放縱之嫌:有些同志本著證據、定性出現分歧時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主張疑罪從輕,不可勉強認定被告人構成盜竊罪。
“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發源于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的含義是:在對事實存在合理的疑問時,應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裁定。該原則在具體適用中可能表現為多種情形:當事實在有罪與無罪之間存在疑問時,應該按照無罪來處理;當事實在重罪與輕罪之間存在疑問時,應該認定為輕罪;就從重處罰情節存在疑問時,應當否認從重處罰情節;當無法確信某一犯罪行為是否超過追訴時效時,應當不再追訴。㈨
姚某從信用卡中套取的現金數額為人民幣13700元。若按照《刑法》第196條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來定罪量刑,屬于“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行為,應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若按照《刑法》第196條、第264條之規定,以盜竊罪來定罪量刑,屬于“盜竊數額巨大”的行為,應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即至少判處3年有期徒刑。顯見,對于姚某的行為,如果能按信用卡詐騙罪予以定罪,處罰將會輕緩許多。因此,如果案中證據并不能足以證明姚某的行為具有盜竊信用卡的主觀故意,則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重點研究姚某冒用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后續行為,對其前期取卡行為不按盜竊性質評價。
綜上,司法機關在推定被告人是否具有“秘密竊取”的主觀故意時,應嚴格遵守“兩個證據規定”。輔以大量客觀證據加以佐證。只有在達到足以反映被告人具有該故意的證明標準時,才能以盜竊罪對其定罪量刑。在對證據的認識出現分歧時,若欲對被告人的行為實施客觀的評價,則應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進行。慎重選擇那些已有充分證據予以證實的部分事實,進而準確的適用法律。
注釋:
[1]趙秉志:《侵犯財產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頁。
[2]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