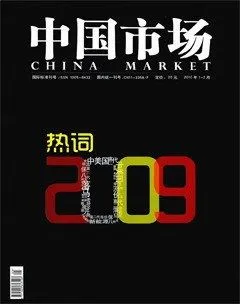胡舒立與《財經》傳奇
在中國,沒有哪一家媒體能夠像《財經》那樣,那么深地烙下一位主編的印記。
正如《財經》資深員工所說:“沒人不尊敬《財經》,除了它的敵人,甚至有些敵人也尊敬它。”
“它與你在中國見到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它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奇跡。”隨著2009年10月傳出人事動蕩新聞,《財經》成為海內外媒體報道熱點,相關搜索達到百萬。沒有任何一本雜志可以引發這樣的關注度。
這一切都是因為胡舒立——《財經》的一手締造人,中國財經新聞“女教父”,《紐約客》筆下中國媒體“夢游”狀態的挑戰者
11月9日她正式辭職,200多人團隊里有140多人集體離開,宣告了曾經針砭時弊、揭黑反腐、被譽為“中國媒體良心”的傳奇告一段落。
好萊塢版誕生故事
胡舒立與她的《財經》,有一個類似好萊塢傳奇的開端。
胡舒立的大外公是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胡愈之,中國新聞出版界的開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聞出版的老前輩,母親是《工人日報》編輯。
“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從體制內的《工人日報》開始職業征程,敢拼、勤奮、有耐性是貫穿始終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報道被“外放”廈門后,她不僅面見了政府部門每一個人,包括和市長打橋牌,還順便去廈大學習了英語;跑金融時為了接近吳敬璉,她開著吉普車送他去機場,堅持許久終于打動了吳敬璉;在第一份全國性商業報紙《中華工商時報》擔任國際版編輯后,她“決定采訪中國所有的頂級金融家”,其中也包括和胡舒立命運產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其父親王炳南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兄長王東明是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波明身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首批留學生之一,在成為紐約證交所的經濟學家后,他選擇回國和上述同為高干子弟的經濟人才一起組建了“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1998年王波明決意創建一個更面向大眾的財經媒體,他找到了當時被譽為中國最好的財經記者的胡舒立,后者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國媒體環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兩百萬元的記者工資以確保記者誠實,全權負責所有內容,采編獨立不受廣告經營影響。王波明以罕見的氣度全部答應。
《財經》,這個最初創刊名叫《Money》的雜志就此誕生。
“女教父”和“工作狂”家族
“我只能與朋友一起工作,因為我不諳世故,也需要別人對我懷以善意。”胡舒立的個人強烈風格烙印在整套雜志團隊上,尤其是在早期二三十人的核心隊伍時,《財經》編輯部里是沒人叫她“胡老師”或者“胡總”的,都叫她“舒立”。
《財經》特約作者、資深媒體人錢鋼描述胡舒立在工作時的節奏“就像一陣風般突然和迅速”。胡舒立是個不折不扣的新聞理想主義者,并將這理想貫徹到媒體實踐中,在《財經》可以做其他媒體不能做的題材,又可以接受《財經》新聞訓練,因此吸引大批媒體人,“當時內部流行一句話,主編到《財經》來做資深編輯,主任到《財經》來做普通記者,所有來的人都降一或兩級。”
“身材小、健談、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記者在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覺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胡舒立的健談是出名的,某高層曾親眼見一個記者用手機和電話那邊的胡舒立聊選題聊了兩個小時,直至記者電話被燒壞;在“女教父”的率領下,《財經》成了工作狂家族。
一位曾經在《21世紀經濟報道》和《財經》做過的記者,對《財經》的集體氛圍感觸最深:“《21世紀經濟報道》里是個人多勞多得,但只有你單打獨斗;《財經》講究群體協同,我一來,編輯就把我所跑的線相關的上千個聯絡電話打包發給我;每做一個選題,還會至少再幫你找十幾個采訪對象。這種資源上的分享對記者提升非常重要。”一篇稿件下來,往往由最初的2萬字至5萬字采訪匯總和資料,濃縮劍3千至5千字的終稿,而這終稿還常由職業素養深厚、文筆精準的編輯來重新修改一遍。
為了保持高素質的團隊與報道,胡舒立從不吝惜花錢。那些真正被胡舒立一手帶起來的記者,以被內部戲稱為“四朵金花”的主力女記者為代表,年薪可達20萬以上,年底還有分紅。普通一篇報道花一萬多是很正常的,封面報道可以花費五六萬去做。
“危險女人”的危險報道
胡舒立被《商業周刊》稱為中國證券界“最危險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財經》雜志發表的《基金黑幕》,這篇把矛頭直指中國幾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許多基金界腐敗現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國證券報》等三大報上聯合發表嚴正聲明,還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開放新生事物”的旗號給《財經》施加巨大壓力,胡舒立的反應是用義正辭嚴的《批評權、知情權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開、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業里最高道理,這篇報道直接觸發了持續一年多的股市大討論和監管當局一系列嚴厲措施的出臺。
2001年8月的《銀廣夏陷阱》始于一位《財經》記者在瀏覽海關記錄時發現,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股份在網上發布了一則偽造的8700萬美元利潤單據。這則報道的政治風險很高,因為當時這家公司的股價正在直線上升,江澤民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剛剛訪問并高度贊揚,公司的CEO甚至想要收購《財經》雜志以阻止報道,王波明第一次在出刊前給他的老朋友、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王岐山打電話,后者問:“這則報道是真實的嗎?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報道刊出幾小時后,銀廣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們先后被送進了監獄。
為《財經》贏來“年度杰出國際調查新聞獎”榮譽提名獎的是SARS系列報道,這也是胡舒立所帶來的《財經》第一次跨出單純的財經市場關注公共領域事件。2003年初,在衛生部要求下,內地媒體對SARS的蔓延普遍選擇沉默,記者曹海麗卻從香港火車站上幾乎每個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銳地覺察到情況的嚴重,胡舒立判斷:“如果這事不是被絕對禁止的,那我們就要做。”于是4月份《財經》最早詳盡報道了SARS事件,同時也是最早進入疫區實地報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VRS特刊。
2007年1月的《誰的魯能》是值得胡舒立和所有《財經》人驕傲的報道、盡管他們為此受到很大的處罰,這篇報道講述了山東的超大型國有企業魯能集川借“轉制”之名悄然落入私人手中,超過七百億人民幣的某些勢力在此事件里的主導與博弈,引發從高層到民間的強烈反響。結果,這篇文章迅速在網絡被封殺,上攤的雜志被人有組織地大批收購,國內幾家主要門戶網站事后透露的確“受到壓力”不得不撤下相關文章,《紐約客》中描述“《財經》上海記者站的員工被要求用手撕掉雜志……每個人都覺得被羞辱了”。
“舒立”文化
一個原《財經》資深員工描述:“《財經》本質上沒有企業文化,如果說有,就是所謂的‘舒立文化’。一個人影響力足夠大,她的方向就是企業的方向,她的性格就是企業的性格,甚至她的文風就是雜志的文風。”
《十億消費者》里以西方特有的修辭手法寫道“一當人們聽說胡舒立要開辦一本新的雜志,全中國的記者都發來了應聘郵件。”從1998年創刊起,《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每年選拔10名國內優秀記者進行“財經新聞”方向的3個月脫產培訓,《財經》負責所有費用,包括教學、住宿、生活費等。至2008年,這個被命名為“《財經》雜志獎學金”的項目受惠者累計達100人,多數培訓后成為各媒體機構的中堅。
辦了11年,《財經》也沒有變成大眾流行讀物,相對艱深的內容、專業的選題、精準而略顯枯燥的表述,使得它多半出現在各行各業決策人、分析家、學者的案頭,或被依賴《財經》自覺獲取知情權的讀者買走,可它散發的影響力是巨大的。用胡舒立的話說,《財經》是一只啄木鳥,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有著獨立個性、堅持職業操守、追求真實報道的媒體逐漸增多,這是時代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說,胡舒立和《財經》,開啟了一個更加多元、也更加開放的傳媒時代。(摘自:《時代周報》2009年12月1日編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