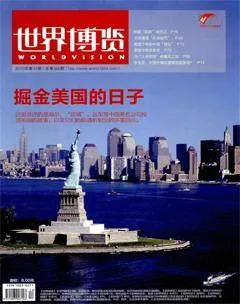“除憶詛咒”
文字可以篡改,照片可以抹去,但是記憶卻難以磨滅。
拉丁詞語“damnatio memoriae”意思是從記憶中抹去,一般翻譯成“除憶詛咒”,雖然這是歷史學家創造的現代新詞,但廣泛用于描述各個時代,尤其是古代羅馬對背離集體的個人的處罰。
被判以除憶詛咒之刑的人有可能是國家叛徒、暴君,也有可能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公敵。
羅馬人的刑法
塔西佗在他的《編年史》里記述了羅馬貴族畢索所遭遇的除憶詛咒之刑:執政官科塔提議把馬可斯·畢索從公共記錄中抹去,把他的一半財產充公,另一半財產移交給他的兒子格涅烏斯,前提是他的兒子必須改姓。馬可斯-畢索本人被剝奪元老資格……
畢索所遭到的除憶詛咒可能是最輕的,公元31年陰謀反對皇帝提庇留的謝亞努斯所遭受的才是真正的除憶詛咒。
提庇留察覺到他曾經的寵臣、禁衛軍首領謝亞努斯陰謀反叛他之后,立刻派人處死了他,謝亞努斯的每一位重要密探和其支持者均被處死,甚至連他的幼女亦未能幸免,因為法律禁止處決處女,所以她先被奸污,后被勒斃。他離異的妻子阿庇卡塔婭在自殺前曾致函提庇留,聲言皇帝的兒媳婦麗維婭曾參與謝亞努斯毒害她的丈夫——皇帝的兒子德魯蘇斯。提庇留下令審判麗維婭,但她絕食而死。不過死后也難以逃脫除憶詛咒的處罰。
羅馬施行的除憶詛咒還包括從銘文中抹去被處罰者的名字,禁止他們在葬禮上佩戴蠟質面具,把他們的作品充公或毀壞,讓他們的遺囑失效,宣布該人的生日為兇日,被處死的周年紀念日為感恩節,侮辱他的尸體等等。總之,要做到消除他們在世時的一切功跡,仿佛他們不曾存在過一樣。對于羅馬公民來說這是最嚴厲的懲罰。
除憶詛咒可以由元老院發布,有時候也由國王或者軍隊宣布。由元老院宣布遭受除憶詛咒的羅馬皇帝大約有16人,其中,尼祿最為臭名昭著。女人則可能跟著家族的男人——她的丈夫、父親或者兄弟一起遭受除憶詛咒,整個羅馬時代遭受除憶詛咒的女人有24人。
如果真的如“除憶詛咒”這個名稱所宣示的那樣有效,那后代的歷史學家就再也找不到曾被處罰的人物記錄了。但實際上,除憶詛咒施行過程并不那么簡單,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政敵,但同時也都有盟友,因此,這種消除當事人一切存在痕跡的作法,在實踐上不可能做得徹底。
比如,公元37年繼位的羅馬皇帝卡里古拉倒行逆施,公元41年被刺身亡,羅馬元老院決議對卡里古拉施以除憶詛咒,但繼任的皇帝克勞狄烏斯卻明確表示反對。尼祿敗亡之際也被元老院宣布為人民公敵,但其后的皇帝維特里烏斯卻公開地尊崇他,給予他盛大的葬禮。
并非只有羅馬人施行除憶詛咒。在猶太教中,
“他/她的名字和記憶被抹掉”是對一個人最惡毒的詛咒。古代埃及人同樣認為,保存一個人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認為毀掉一個人的名字從某種程度上就摧毀了他。
古埃及新王朝中,哈特謝普蘇特以女性之身成為法老,在她過世之后,后繼的法老圖特摩斯三世為消滅曾有女性當政的證據,下令刮除她在神廟中的銘刻,摧毀她在各地的雕像。
現代的“進化”
有關除憶詛咒更現代的例子是篡改照片。
近代照相術興起后,如果政客在后來的政治生涯中失勢,則可能會在許多檔案相片中被“修改”,從而消失掉,讓后人誤判他過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就曾對很多對手都施以類似的處罰。蘇聯政治家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的例子很具諷刺意味。在大肅反中,葉若夫掌管內務部,風光無限,報紙上經常出現他和斯大林的合影。在葉若夫掌權的1937~1938年,大清洗達到了最高峰,大概有50%~70%的最高蘇維埃成員被撤職并關押,流放至西伯利亞的古拉格或直接被處決。1938年,葉若夫因有“重大缺點和扭曲”被貝利亞接任,調任空職后被處決。他被“冠以”:“破壞分子”、“不稱職者”、“貪污公款者”和“叛國者”的罪名,被控與德國合作,支持間諜和進行破壞活動。在與斯大林的合影中,葉若夫被全部抹去。
風水輪流轉,赫魯曉夫上臺之后,就輪到斯大林的形象從某些宣傳電影中消失了。
1925年,俄國城市察里津被改名為斯大林格勒,1961年又改名為伏爾加格勒。蘇聯解體之后,很多城市放棄了以前官方宣揚的意識形態,以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比如列寧格勒紛紛恢復到蘇聯之前的名字,或者改為沒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名字。前蘇聯的領導人的雕像也大多被摧毀。
現代的除憶詛咒還蔓延到南美洲。1955年9月,阿根廷海軍發動政變,正在謀求蟬聯第三任總統的庇隆被放逐出國,此后庇隆之名在阿根廷成為禁語,媒體提到他用“免職的暴君”來稱呼,他的相片和其他能代表這個阿根廷領導人的事物全部被禁止出現在媒體上。
最近,除憶詛咒出現在西班牙。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案”,該法案正式對佛朗哥的獨裁政權進行譴責,要求從公共建筑中撤除代表佛朗哥政權的雕像、匾額和其他象征。據稱,佛朗哥時代遺物的總數超過300件,有幾百條市鎮街道以佛朗哥和他手下將軍之名命名,不過清洗行動已經開始,佛朗哥及其記憶正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當前的小說和電影對除憶詛咒也有入木三分的刻畫。美國兒童書作家洛伊絲·洛利在其1993年的小說《記憶傳授人》中提到,每個新生兒都不能以曾經被詛咒的名字命名。在美國電視系列劇《星際迷航:下一代》之中,外星人克林貢人中也實行除憶詛咒這種處罰。美國著名漫畫家弗蘭克·米勒創造的漫畫書《300》和2007年據此改變的電影《斯巴達300勇士》中都提及在古希臘和波斯文化中有除憶詛咒。
喬治·奧威爾在1949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描寫了在“真理部”上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真理部”這個部門處理的事務與頭銜截然相反,小說的主人公主要負責根據現實和宣傳需要,改寫歷史文獻、報紙和文學著作,篡改照片,“蒸發”“非人”(unpersons,違反過黨章的人)。奧威爾說:“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一針見血切中了除憶詛咒的要害。
米蘭·昆德拉在1979年出版的小說《笑忘書》中描寫了一幅照片。這是一張有關兩個政治家的照片,其中一個是來自東歐某小國的主席,另外一個是他的同志。當時,他們倆正面對很多人作演講,因為天氣很冷,旁邊的同志就把自己的帽子給了主席,以顯示他們的革命友情。過了沒多久,主席因為政治錯誤而被處決了,于是這張照片上就不能讓他出現了,所以這個人就被從照片上
抹掉了。結果就成了:照片上的人走了,但是他的帽子卻留下了,因為帽子是旁邊人的,只不過戴到了主席的頭上。
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們可以把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從記載中抹去,通過對一張照片的處理就“除掉”了一個人,但是其帽子卻無法抹掉,言外之意是說可以抹去照片,但是人的記憶是無法磨滅的。
從此走向南沙
1974年中越之間爆發的西沙海戰,不但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海戰,更是自中國擁有現代海軍以來第一次完勝。或許中國記憶中太多的屈辱來自海上,此戰所臺的亙古開天之意,更是被坊間譽為“開國運之戰”。
此戰過后,中國海軍便開始了南進的步伐,因為南海對于中國,不僅僅是領海,更是生命線。一方面需要和周邊國家交好來保證生命線的順暢,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和周邊國家的領海爭端中維護中國的主權利益。兩方面的利益訴求近乎矛盾,
“領海+生命線”的模式下,無疑使得南海成為最“難”的海……
不幸的是,截至本刊發稿時,又有3艘漁船和28名漁民在五月初被周邊國家非法扣留,對漁民而言在南沙爭議海域捕魚僅僅是為了謀生,但他們的存在早已默默地宣示了中國的主權。在危險海域作業時,如果能有一艘中國武裝船只進行保護,對于漁民而言將是何等的幸事。但現實情況是:無論南海艦隊,還是海監和漁政,相較廣袤的南海而言力量都顯得單薄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