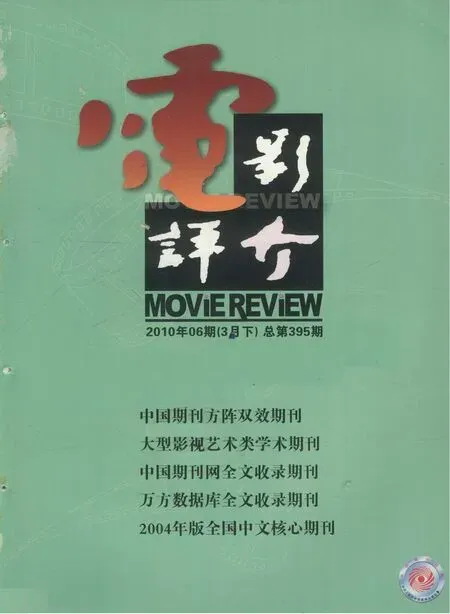淺析紀錄片創作中“情景再現”的使用
爆竹聲中,紅紅的燈籠高高掛起,大大的福字貼到門上,孩子們開心地在巷子里放著煙花,夜市上熙熙攘攘……大型紀錄片《故宮》一開始便利用情景再現把人們帶回到公元1403年元月一日這一天,向觀眾呈現了當時人們慶祝元旦的情景。片中類似于這樣的畫面還有很多,大都采用了情景再現的創作方法,帶人們回到那個時代,走進宮中,了解歷史,了解文化。毫無疑問,情景再現這種創作技法的使用,成為《故宮》創作的一個亮點,增加了影片的觀賞性,提高了收視率。但同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觀眾到底是在看一部紀錄片還是故事片?近年來,伴隨著情景再現的廣泛應用,類似的爭議日漸頻繁。那么,到底孰是孰非?該如何評論這種現象?該如何來看待情景再現呢?
一、關于情景再現
狹義上的情景再現,是指紀錄片的一種創作技法,是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過聲音與畫面的設計,表現客觀世界已經發生的、或者可能已經發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種電視創作技法。它一般是在失去現場紀錄機會的題材和場景中使用,是紀實風格的一種異化手段。
情景再現發軔于紀錄片創作領域,但它很快就超越了紀錄片的范疇。因此,廣義的情景再現是一個節目層面的概念,是一種節目的創作形態,它泛指一切運用了情景再現創作觀念與技法的紀錄類節目。在這些作品中,作為創作技法的情景再現,往往不是單獨使用的,而是與采訪、資料引用等眾多紀實手段結合起來使用。因此,廣義的情景再現,是指采用包括情景再現在內的眾多創作技法共同構成的紀錄作品,它不僅包括作品中再現部分的內容,而且包括作品中與真實再現結合使用的采訪和資料部分的內容,這類節目作為一個整體也被稱為情景再現。
情景再現的出現有其深厚的實踐背景和理論淵源。情景再現的應用源頭可以追溯到紀錄片鼻祖弗拉哈迪的影片——《北方的納努克》。1920年,弗拉哈迪在制作《北方的納努克》時,就使用“擺拍”手段拍攝納努克人造冰屋、捕獵等場面。弗拉哈迪在后來的影片中一再重復這種拍攝方式,然而這并不妨礙他的作品實現了“結果的真實”。結果要真實,為了真實不惜搬演,弗拉哈迪這種對真實性的獨特而富于啟發性的理解對今天的紀錄片創作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世界紀錄片大師伊文思推動了情景再現的發展。在他的不少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情景再現。1935年,伊文思在拍攝一部反映礦工生活的紀錄片——《博里納奇礦區》時運用了情景再現。其中一處是由礦工扮演警察,強行搬走礦工的家具。伊文思認為,“這場戲在我們的完成影片中占著重要的位置”,“在博里納奇拍攝這部影片期間,我們的電影美學經歷了重大的修改”。在當時,這種創作技法被伊文思稱為“重拾現場”或“復原補拍”。他認為,只要補拍場面不是出于捏造,而真正是來自現實生活的,那么生活本身將賦予它力量,并使它充滿了新的內容和情感。
最初在中國電視熒屏上探索使用情景再現的,是1995年中央電視臺的《東方時空》欄目。當時,《東方時空》中出現的一些以真人扮演的手法來創作紀錄片,是國內較早出現的對這一手法的自覺探索。較早的樣片之一是王子軍的《南京的血證》,短片中編導利用情景再現的手法重現了當時的一些場景。當老人講到自己當年在照相館當學徒時藏起一本反映日本人罪行的照片時,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畫面:照相館里,一個男青年正在忙碌,這時一個挎著戰刀、穿著皮靴的日本人大步走了進來。之后兩人對話。男青年在洗照片時看到了照片的內容,極為震驚,偷偷保存了一套,藏在墻磚的縫隙里,直到今天。通過這一情景再現,觀眾更直接的了解到了當時發生的事情。
通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創作者在使用情景再現這種創作技法上已經比較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益與效應,并通過經驗總結和專家的理論探討趨向成熟。此后,真實再現這種創作形態的節目呈現出了批量生產的趨勢。北京電視臺的《記錄》、《新聞故事》等欄目,河北臺、濟南臺等也直接開辦了以“真實再現”命名的欄目。這些節目大多現在仍在播出,而且收視率較高,觀眾反饋比較好。
二、情景再現的表現形式
情景再現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扮演、搬演和資料摘錄。
扮演是指利用演員扮演人物。根據情景再現程度的不同,對演員的挑選也有不同層面上的要求。與故事片不同的是,紀錄片對演員的演技不做過高要求,最多要求他們的面貌與氣質特征與作品接近。相反,對于紀錄片來說,演員的道具、服裝這些細節性因素往往比演員本身還要重要。一部謹慎的紀錄片應該盡量要求這些道具細節極端真實。
搬演是指重現一個有意味的場景或事件。搬演常有演員參加,就融入了扮演的因素,但它與扮演的不同之處在于,扮演重在表現人物,而搬演重在表現一個場景或事件,比之扮演,多了敘事性因素。搬演需要利用或設置與歷史事件情景氛圍相近似的場景,使之能有效地傳達出所要表現的主題。
資料摘錄是指利用各種影像資料(主要是故事片段落)作為紀錄片的真實再現段落。真實再現的部分不一定都需要創作者自己去制作,有時也會借用一些其他的影視作品達到同樣的目的。例如,出于文物保護或其他一些原因,中國故宮的鏡頭比較難得。但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香港電影《火燒圓明園》和意大利導演貝爾?特魯奇導演的《末代皇帝》中大量鏡頭是在故宮實景拍攝的。因此,在反映清代帝王生活以及其他與故宮有關的紀錄片中常會借用以上電影的鏡頭。
三、情景再現的作用
1、情景再現為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新的表現方式
作為一種新的創作技法,情景再現的出現打破了此前電視紀錄片的諸多束縛,可以通過各種形象化的手段表達人們豐富的內心情感世界,還能夠盡可能的表現或還原過去發生或存在的、如今已不復存在的文化歷史,增強了紀錄片的可視性。
對于創作者來說,情景再現解決了編導無米下鍋的煩惱,尤其是拍攝歷史題材的紀錄片時。歷史題材的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史料,史料是最有說服力的。可無論是文字性的、實物性的,還是影像性的,這種資料都是少之又少,無法撐起一部完整的作品。況且,這些過去發生的歷史行為和歷史事件,往往就是關鍵性事件,是節目的核心事件。如果不把這些向觀眾交代清楚,觀眾的理解就會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形成敘事斷點。而情景再現恰恰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情景再現根據歷史留下來的各種證據和痕跡,用演員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重現那些過去發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縫合敘述歷史時遭遇到的斷點,使敘述更加完整、流暢。
2、情景再現增強了紀錄片的藝術表現力
紀錄片既是技術本體,又是藝術本體;既有紀實性,又有藝術性。在情景再現的作品中,編導可以充分調動起自己的創作才能,把自己的藝術個性融入作品,以紀錄片真實的內容為基礎,輔以形象化的表現手段,使紀錄片真正與藝術接壤,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紀錄片《失落的文明》為了表現龐貝城在奢侈安逸的生活中突然遭受天災,搬演了這樣的畫面:堆滿水果的茶幾與注滿美酒的酒杯忽然翻倒在地……這種畫面與龐貝城在毫無準備中突然遭受滅頂之災極為相似。這種模擬場景的方式,不僅有效的傳達了作品所要表現的主題,還增加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
3、情景再現提高了紀錄片的觀賞性
情景再現讓鏡頭跳出史料的故紙堆,創造性的反映歷史情景,將呆板的歷史解說形象化,讓觀眾能夠置身其中,深刻地感受當時的歷史情境,給觀眾帶來更多的審美感受。大型紀錄片《故宮》中就再現了靖難之變這一歷史事件。戰場上炮火轟鳴,戰馬嘶鳴,身穿鎧甲手持長槍的士兵在進行激烈的交戰……這幾個鏡頭就很好地展現了當時的戰爭場面。影片開頭的這兩處情景再現明顯增加了作品的可視性和故事性,同時給觀眾以逼真的感受。在接下來的內容里,編導還真實再現了大殿里雍容端坐在龍椅上的皇帝、幾百個朝拜的大臣、碎步行走在宮中的太監……這些真實再現的鏡頭基本上都是模糊的,我們看不清人物的面貌,人物也沒有對白。但是,觀眾被帶進了逼真的歷史氛圍中,進入了一定的藝術情境,而這種藝術情境又符合人們對歷史的神秘、浪漫、繁華的主觀想象,自然會產生美的感受。
四、情景再現帶來的問題及使用原則
情景再現的應用的確給紀錄片創作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逐漸成為創作領域的普遍現象。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可以說,情景再現一定程度上養成了紀錄片“舍本逐末”的風氣。眾所周知,真實是紀錄片的根本,紀錄片中最有含金量的東西是歷史上真實存在和保存下來的歷史資料。對于那些有真實記錄鏡頭的段落,應盡量避免使用情景再現。只有在編導面對歷史的缺憾無能為力時,情景再現才能被派上用場,真正發揮出它的作用。中央電視臺欄目制片人周兵在發現梅蘭芳在美國百老匯演出的一段一分鐘長的影音資料后,一秒鐘都沒有剪掉。周兵說,如果有100分鐘、200分鐘梅蘭芳表演的原始資料,或者當時出現活動的膠片資料,他在節目里肯定不使用情景再現。然而,現在一些電視臺的編導卻把情景再現當成了救命的良藥,放棄對歷史資料的挖掘,完全寄托于情景再現,生生把一個紀錄片拍成了故事片。而任何使用情景再現的電視工作者都必須真切地認識到,情景再現是電視工作者面對歷史缺憾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是不得已而為之,切不可把它當成工作的重心,沉溺于其中。
另一方面,情景再現的廣泛應用使中國紀錄片開始呈現出娛樂化、泡沫化的趨勢。呂新雨在《當前中國紀錄片發展問題備忘》中寫道:“情景再現使用的底線是不能掩蓋我們對歷史真相把握的信念,否則會使觀眾喪失掉對紀錄片的信任感。情景再現是有邊界和底線的,不可以泛濫。否則,會造成我們對紀錄片最重要功能的抹殺,這個功能就是為歷史提供證據。”因此,紀錄片的發展不能在情景再現的道路上走得太遠而偏離了正軌,否則,紀錄片就失去了它內在的深度,僅僅成為一道快餐。
情景再現作為紀錄片制作的一種新的虛構方式,引起了人們對紀錄片真實性的重新思考。然而情景再現作為眾多電視手段中的一種,它本身并不會動搖紀錄片的真實性。可情景再現如果在實際操作中被不加限制地濫用,卻會影響到紀錄片的真實性。其問題的關鍵在于制作者如何使用,能否把握好分寸。因此,我們在應用情景再現時,要遵守一定的原則。
1、情景再現的使用要有必要性
說到底,情景再現畢竟是編導面對歷史缺憾的一種無奈選擇。對于那些有真實記錄鏡頭的段落,應盡量避免使用情景再現。例如,《周恩來外交風云》中有不少新拍的內容,雖然它們畫面構圖工整,影調色彩鮮艷,攝影機運動平穩,但其魅力遠不如那些陳舊的影像資料,原因就在于,歷史影像資料所具有的歷史現場感是無法復制的,真實再現的處理稍有不當就會露出馬腳。這啟示我們,真實再現的優勢是在于彌補歷史鏡頭的缺失,在于再現而非真實,可有可無的再現應該盡量避免。
2、情景再現的使用要符合真實性原則,符合邏輯
紀錄片創作不同于一般的藝術創作,必須尊重客觀事實。真實永遠是紀錄片相較其他藝術作品最具區隔性的屬性。因此,情景再現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前提,即使客觀事實難于把握,也應當要有事實根據,切忌編導從自己的主觀意志出發,為了記錄片的觀賞性而隨便臆造。某電臺報道一媒體的電視人是這樣進行“紀錄片”創作的:只差沒帶化妝師了,其他所有的場面和內容都是真人表演,用當地人演當地的戲,一個受過師范教育的年輕的鄉村教師,硬是按照導演的意圖把漂亮的小分頭用大碗扣住剪成了鍋蓋頭,以突出其意想的鄉村效果……。這樣拍出來的片子,其實質是用業余演員扮演的一部具有紀實風格的電視劇,而并非紀錄片,嚴重背離了真實性的原則。
同時,情景再現還要符合邏輯,讓觀眾看后感覺真實可信。也就是說情景再現的內容不能違反人們所感知的真實生活中的一般慣例。獲美國1999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獎的紀錄片《九月的某一天》,講述的是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11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在奧運村遭恐怖組織“黑九月”成員襲擊喪生,另有5名槍手和1名警察死亡的慘劇。這個慘劇當年曾經轟動世界。這部紀錄片有很多鏡頭是1999年補拍的,真實再現了當時的一些場景,但其中一些鏡頭卻讓觀眾感到迷惑,例如恐怖分子在房間外巡邏的鏡頭,讓觀眾有些分不清真偽。從內容常識上判斷,觀眾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懷疑:恐怖分子這么明目張膽地守在外面,難道他們就不畏懼狙擊手的子彈?這些讓觀眾產生疑惑的情景再現鏡頭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
3、情景再現的使用要注意身份標志
身份標志是情景再現不混淆視聽不誤導觀眾的前提。在使用情景再現這種創作手法時,需要在編輯中注意資料還是再現的身份標識,對容易造成認識混淆的段落加以顯著區別,以防誤導觀眾。一般說來,電視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部分都要用字幕、解說詞或是經過一些特技處理的畫面來告訴觀眾這是重現或故事片資料,讓觀眾一眼就能辨別出來。因為情景再現這種創作技法只有具備一定的間離性,才能獲得觀眾對其真實性的認可。任何抹平了觀眾與真實之間距離的情景再現的處理方式,都是失誤的。
情景再現的應用已成為紀錄片創作領域的一個普遍現象,但一直以來,關于紀錄片中能否使用情景再現,進而能否運用一定的虛構手段來進行創作,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聲音。其實,情景再現的出現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它既受紀錄片發展內在規律的影響,又與當下的媒體環境、觀眾的欣賞需求密切相連,是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市場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應該相信,只要紀錄片創作者對情景再現合理使用,遵循一定的原則,情景再現的獨特優勢必會給紀錄片帶來一片新的藝術表現天地。
[1]程宏,蘇峰,羅琴,“真相”與“造像”,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
[2]石屹,電視紀錄片——藝術、手法與中外觀照,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董長青,申思,高苒,淺議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新聞傳播,2007,(4)
[4]孫寶國,電視紀錄片形態辨析,北方傳媒研究,2006,(4)
[5]王輝,紀錄片想法與做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