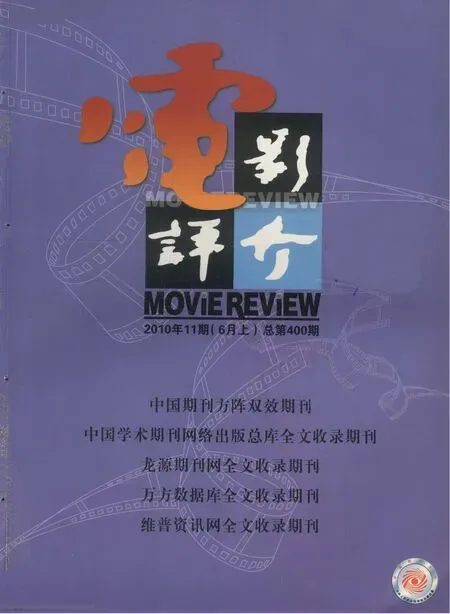余華作品中的圣經文化痕跡
一、用神學意念承載及消解生活的苦難
圣經文化的含義很廣,影響也很深遠。在這里,我們把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神學意念和神學模式等稱為圣經文化。從這個角度說,圣經文化對余華的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余華對圣經文化的了解,喜愛和接納主要體現在他有意識的閱讀文學作品上。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洪治綱說:“閱讀的啟發在余華的創作中是有決定性的影響。”[1]余華也說:“我一直強調,任何一個作家首先都是一個讀者,一個好的讀者才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這是非常重要的,作家的經驗轉化為一種分寸的把握使作家在敘述的道路上不迷失方向。”[2]余華不僅閱讀《圣經》原著,還迷戀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福克納等深受圣經文化影響的世界大師們的作品。余華有意識、有選擇地閱讀和接受這些含有圣經文化精髓的作品,以敏銳的藝術感知力和高超的敘述智慧,捕捉大師們在敘述中的細微之處和潛在欲念。圣經文化的精髓便悄悄潛入他的思維中,改變他的創作風格。他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彰顯濃厚的圣經文化色彩。
讓余華從“小偷”變“大盜”的卡夫卡[3],對余華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余華說他在讀卡夫卡的作品時,終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頓悟,——“我讀到卡夫卡的《鄉村醫生》這部作品,給我終身難忘的印象,就是自由對一個作家是多么重要,小說里有一匹馬,他想讓那匹馬出現,它就出現,他不想讓那匹馬出現,那匹馬就沒了。”[4]可以用圣經文化的神跡來形容這種自由之筆。神跡,是一種神學意念,其本質在于超越自然法則,他不被自然法則所理解,所容納,他作為超自然的力量的結果而發生。在余華的作品中也出現了這樣的神跡。余華把這樣的神跡賦予到一個個在苦難面前頑強生活的人,在《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兩篇文章中,余華借助“天”、“天命”和“血”等神學意念塑造了兩個承受生命苦難而又有著堅韌意志的籠罩神圣光環的人物——富貴和許三觀。
1、“天”,“天命”的意念
“天”和“天命”在富貴和許三觀的生活中頻頻出現。類似于圣經文化中經常出現的上帝,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也具有人的性格,能洞察一切,主宰一切,來去自由,無處不在,懲惡揚善。
富貴一生面臨巨大的變故,他不得不面對至親至愛的人一個個離自己而去的厄運,先是兒子有慶的突然死亡,接著又是女兒鳳霞和妻子家珍的死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和外孫子苦根子的死亡。富貴經歷與至親至愛的人生離死別的痛苦,也承受骨肉陰陽分離的孤苦凄清。“這輩子想起來也是很快就過來了,過的平平常常……我啊,就是這樣的命……做人還是平常點好,掙這個那個,掙來掙去賠了自己的命……”[5]富貴最終并沒有在厄運面前痛不欲生,而是平靜,寬容,豁達的接受這些殘酷的事實。在面對如此痛徹心扉的苦難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坦然,豁達和樂觀的心態?富貴把一切的厄運和災難歸結到命運,即天命。這個天命是由來無影去無蹤的上帝主宰著,普通的人只等著人去承擔、面對,去痛苦,去悔恨,去掙扎……在經歷了坎坷歲月的富貴,煉鑄了頑強生命力,他能洞察這一切,坦然面對和接受這一切。富貴最后用看似純樸的話語,詮釋了人生的大徹大悟,消解了苦難和傷痛,把一切變得自然而平常。
在許三觀眼里,始終有個至高無上的“上天”存在,神秘而讓人敬畏。
做了壞事不肯承認……老天爺的眼睛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老天爺要想懲罰你了……雖然日子過得窮過得苦,可我身體好,身體就是本錢,老天爺獎我的……[6]
一樂對我好,為什么?也是老天獎我的……[7]
做惡事的話,若不馬上改正過來,就要像何小勇一樣,遭老天的罰。[8]
老天獎我的,我就是天天賣血,也死不了。我身上的血就是搖錢樹,這棵搖錢樹,就是 上天給我的。[9]
何小勇再壞,再沒良心,也是一個躺在醫院里不死不活的人了,你還整天去說他,小心老天爺要罰你了。[10]
許三觀相信有個至高無上的上天在窺視著人間的一切。每個人的善惡行為都逃不掉上天的慧眼。人行善能得到上天的褒獎,行惡會遭到懲罰。所以許三觀小心翼翼的規范自己的言行,把一切善惡交給上天裁決和獎懲。他的行動充滿了神性的色彩,也沖淡了苦難與凄涼的生活境況。
2、“血”的意念
“血”是《圣經》中一重要意象。在《五經》中有關禮儀的法律中,“血”占特殊位置:人血絕不能流,動物的血絕不能吃,而祭祀的血必須在祭壇上作祭祀用。血是圣神的。許三觀認為他的“血”是“老天爺獎我的,我就是天天賣血,我也死不了。我身上的血就像一棵搖錢樹……是老天爺給我的”。[11]許三觀相信命運的安排,相信天意,這就為他的“血”著上了神圣的色彩。神是不可褻瀆的,他在每次賣完血之后,都有一個重要的儀式——到勝利飯店吃一盤豬肝和二兩溫黃酒,這足以表明許三觀對血的禮贊,對生命的尊重,對神的崇拜。雖然許三觀不得不承受賣血的代價和苦難——他一生中賣過12次血,其中為了籌錢給一樂治病,他連續5次賣血,賣得暈倒,還差點送了性命。但是“血”在許三觀的一生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位置,他用賣血的錢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姑娘,替一樂打傷的方鐵匠的兒子付醫療費,為家人在饑荒年代提供一頓美味的面條,“賄賂”二樂的生產隊長,給一樂治病。血已成了許三觀的萬能鑰匙,似乎能打開生活中的任何困境之鎖。這是作者的神來之筆。許三觀在賣血中得到了快樂,他的生命價值在賣血中也得到了體現和升華。這就大大削弱了生活的苦難。
許三觀和富貴,都有著鮮活的生命。他們有著耶穌似的苦難,也有耶穌似的戰勝苦難的豁達和樂觀心態,余華采用圣經文化中的神學意念——天命和血,渲染了神性的力量,承載和消解了生活的苦難。
二、罪與救贖的主題
余華喜歡的另一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是偉大的神圣小說,基本主題是“罪與救贖”這一基督教的根本問題。余華說:“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思的作品,就是《罪與罰》,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受不了了,很多時間里我都不敢讀他的作品。”[12]可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余華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沖擊。
余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兩部作品,也存在這種“罪與救贖”的模式。即圍繞“違約——懲罰——悔過——救贖”的神學觀展開。
許三觀知道一樂不是他的兒子時,他與一樂相處的九年感情似乎一下子全冷淡了。他幾乎視一樂為仇人,“(許三觀)心想一樂這雜種竟敢打我兒子,他跑出去,對準一樂的臉就是一巴掌,把一樂摑到墻邊。”,[13]當一樂闖禍,砸了方鐵匠兒子的腦袋時,許三觀要一樂去找他的親爹何小勇,“你敢不去,不去我揍扁你”[14]他在饑荒年代賣血讓家人去吃頓面條,卻惟獨不讓一樂去,“今天這錢是我賣血得來的,這錢來得不容易,這錢是我拿命去換來的,我買了血讓你去吃面條,就太便宜那個王八蛋何小勇了。”[15]許三觀人性狹隘的缺陷徹底顯露了出來。許三觀這種唯血緣是親的狹隘思想是犯了罪的。圣經文化中最擔心的罪之一是人的奴役之罪。人的奴役之罪中又包括受血緣家庭的奴役,“家族血緣的過度強調和一味發展將會把人至于奴役的囚籠之中……以血緣關系之親疏遠近為根據來決定人際關系的尊卑貴賤以及對他人的親屬冷暖,必然意味著取消天下人一視同仁的博愛……總之,上帝不容許濃于水的家庭血緣對人的奴役。”[16]犯了罪就要得到救贖,圣經文化強調人類改善的根本途徑在于每一個內在人性和個人生命的改變。許三觀在賣血的過程中,他的原罪得到救贖。救贖之物就是“血”。“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再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可以贖罪。”[17]一樂病危,需及時治療,許三觀為一樂籌醫藥費,在去上海的路上一共賣了五次血,差點還送了自己的性命。許三觀賣血救一樂這一過程,也表明許三觀已把自己狹隘的唯血緣是親的思想徹底拋棄了,他平等地寬容地接納了一樂,做到了愛人如己,實現了靈魂的復活。
在《活著》中,富貴同樣是一個有著罪孽的人。富貴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十足的紈绔子弟,他曾經在女人的胸脯上尋找快樂的眼淚,在她們的肩膀上招搖過市、風光無限,在賭場上心旌動搖的體味生命的刺激與冒險,最后還活活的氣死了親爹。富貴觸犯了人的懶惰,邪淫和人的自我中心之罪。表現為:好吃懶做,思想渙散,淫邪作樂,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他人,處處為個人利益打算,拒絕以謙悲、熱愛的態度向他人和世界開放。盡管富貴在父親的死這件事上受到了靈魂的震撼,開始要“改邪歸正”,但是他還是遭到了“上帝的嚴懲”:與他有著血緣關系的人一個個死去,先是兒子有慶的突然死亡,接著又是女兒鳳霞和妻子家珍的死亡,然后是女婿二喜和外孫子苦根子的死亡。面對親人的生離死別,富貴如同被刀割般悲痛萬分。最終富貴只與自己的老牛相依為命,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命,唯活著就好。圣經中真正的救贖必須在個體生命內部發生,是心意的轉變、精神的重生、靈魂的復活。富貴正是在接受苦難懲罰的過程中,實現了自己靈魂的蛻變,他恢復了善良同情和寬厚的人性品質,并意識到了生命存在的責任和意義,在命運面前學會了寬容,學會了容納,學會了接受。
余華正是通過了這一“罪與救贖”的主題,使《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人物和故事情節都充滿了神性的色彩,從而使這兩部作品更加具有震撼力。
科學沒有國界,文化也是沒有國界的。余華吸納了圣經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充滿神性的一面,洋溢旺盛的生命力,彰顯震撼靈魂的力量。《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被視為當代文壇的經典作品,也正說明人們對這種震撼靈魂的作品的青睞與需求。
注釋
[1][2][3][4][12]洪治綱:《余華評傳》,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余華:《活著》,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6][7][8][9][10][11][13][14][15]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16]金麗:《圣經與西方文學》,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頁
[17]羅慶才,黃錫木:《圣經——通識手冊》,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