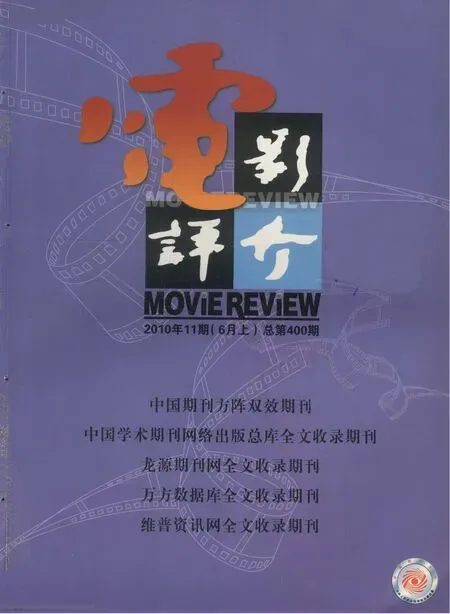《世說新語》中的曹丕形象及其成因淺探
《世說新語》作為志人小說的代表作,無疑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然今人多以此書反映了魏晉時代的真實風貌,不能不說陷入了誤區。南齊人敬胤最早為此書作注,此時距《世說新語》成書不過五十年時間,他批評“《世說》茍欲愛奇而不詳事理[1]”。傳世的劉孝標注距離《世說新語》成書也不過百年,劉孝標在注中多次說“《世說》虛也”,“疑《世說》穿鑿也。”[2]自《隋書?經籍志》起,歷來官修、私修書目都把《世說新語》置之子部小說家類。《隋書?經籍志》中還有解釋:“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紀。”[3]可見前人早已對《世說新語》的性質有了清晰的認識和定位。《世說新語》是一部劉義慶及其文人集團輯錄的小說集,它體現了輯錄者的喜好和情感傾向,甚至會和事實不同。
一
《世說新語》中,共有十則故事涉及到曹丕。細而論之,《惑溺》第1則,《尤悔》第1則,《巧藝》第1則,曹丕為故事刻畫的主要人物,他的表現是該門標題的注腳;《文學》第66則,《傷逝》第1則,《賢媛》第4則,曹丕為故事的次要人物,即曹丕雖非主要描寫人物,但可以體現其性格的側面;《方正》第2則,《方正》第3則,《言語》第10、11則,雖然故事中出現曹丕,但曹丕只能算一個道具,無任何形象。
從上述諸則故事,我們可大致將曹丕形象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荒淫無恥。《惑溺》第1則:“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聯想到后人解《洛神賦》,謂曹植以洛神喻指甄后,甄后絕色,迷倒父子三人,真乃亙古奇觀。而曹操、曹丕攻城為甄后,可謂為“沖冠一怒為紅顏”典型。曹丕還不僅在這件事上占得曹操的先機,《賢媛》第4則:“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并是昔日所愛存者。太后曰:‘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至山陵崩,亦竟不臨。”曹操甫去世,眾法師為其招魂,曹丕就迫不及待地將曹操的侍妾據為已有。后曹丕病重,其母卞太后去探望時發現這個秘密,不禁破口大罵。顯然卞太后也認為,曹丕的行為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如此這般,曹丕不僅荒淫,且已到無恥的地步。
(二)歹毒卑鄙。《文學》第66則:“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這則故事是“七步詩”的由來,為我們描寫曹植捷悟聰穎的同時,也刻畫了曹丕殘害手足的歹毒性格。《尤悔》第1則:“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并啖棗,文帝以毒置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這么卑鄙的殺人手段,實在少見,讓我們在見識曹丕歹毒的同時,也為曹丕的卑鄙所不齒。
(三)滑稽可笑。《傷逝》第1則:“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哀,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后人多以為此則贊美了曹丕的任誕。其實并非如此,該門第3則,孫子荊悼王武子,同樣為作驢鳴,惹得肅穆的靈堂上“賓客皆笑”孫、王二人生活在狂放不羈的西晉,尚且如此,何況建安時期。可見曹丕的行為一定為眾人內心所譏笑,只是礙于他的權勢,只好照做。《巧藝》第1則:“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戲。文帝于此特妙,用于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逾于帝。”“于此特妙”,可見曹丕的彈棋技藝可稱一流,表面看起來,似為正面評價,其實不然。彈棋僅為宮內消遣時光的小游戲。游戲之流,古人常以之為雕蟲小技,不值一哂,難登大雅之堂,更不會沉湎于此。身為王胄的曹丕卻精通彈棋,實為可笑。
簡之,《世說新語》中關涉曹丕的故事無一正面評價,諸故事用鮮明的事例給我們塑造了一個荒淫無恥、兇狠殘暴的滑稽之徒,是一個十足的負面形象。
二
然而,《世說新語》是一部早期小說性質的故事集,部分內容帶有演繹、虛構的成分。這一點,在曹丕的故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先看《惑溺》第1則,曹操竟聲稱,攻打鄴城的目的,是為了得到袁熙的妻子甄氏,這恐怕難為歷史學家所認同。而父子三人同為甄氏所惑,也令明代的楊慎很不解:“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爭之?”(楊慎《升庵集》)曹操破鄴為建安九年,此時正是曹丕、曹植爭奪魏王太子最激烈的時候,直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才被任命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太子爭奪中的領先地位。這幾年中,為了獲得了曹操的青睞,曹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一直為太子之位而韜光養晦。曹操最后選定曹丕,其中一個原因也是曹丕比曹植更謹慎。如果曹操攻鄴真為甄氏,曹丕斷不會橫刀奪父之愛。其實,劉孝標在他的注中已經告訴了我們這個故事的真相,《魏略》、《魏晉世語》、《魏志春秋》三部史書的說法基本相同:曹軍破鄴,曹丕為先鋒,于袁府內室中見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聞,為納之。
《賢媛》第1則的荒謬就更明顯了,“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喪服小記》注:“后招魂以復魄也,始死以衣招魂曰復。”即人剛死時,持死者衣裙登高,呼魂魄歸來。曹操逝世,曹丕沒有去想如何順利登上魏王寶座,而是先想到父親的那些貌美的侍妾,這實在難以讓人相信。《資治通鑒?魏紀一》:“(曹操在洛陽去世),是時太子(曹丕)在鄴,(洛陽)軍中騷動。群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兇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時群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從史實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陽逝世,此時曹丕在鄴。噩耗傳至鄴城,曹丕知道,曹操的突然死亡給自己平穩登上權力巔峰增添了很多變數,兄弟之中,曹植、曹彰都對自己構成一定的威脅。此時此刻,如何收攏人心,順利即位才是最關鍵的,至于接收曹操的侍妾,縱然有,也是一段時間以后的事情。
《尤悔》第1則里寫曹丕在母子三人團聚的時候用毒棗毒殺了曹彰,也有明顯的虛構成分。曹彰在曹操去世時顯露異志,為曹丕所忌恨是肯定的。再加上正史 “(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的說法語焉不詳,就給后世留下了諸多猜測。我們無法考證曹彰究竟是病死還是為曹丕所殺,但至少不是《世說》所描寫的這樣。葉嘉瑩先生指出,黃初四年,諸王來朝的時間為農歷五月,此時棗子還未熟,用棗子毒殺曹彰是不可能的,文帝約束諸王的辦法還不至于要采用這種方式,曹彰是得了暴疾而死。[4]余嘉錫先生認為:“蓋彰之暴卒,固為丕所殺,…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飾之耳。”[5]劉孝標引用了吳人孫盛所作的《魏晉世語》給另外一個解釋:“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其余數則中,《文學》第66則的“七步詩”,其真偽歷來就爭論不休。《傷逝》第1則,劉辰翁、凌濛初對此提出疑問,認為其中雜有小說家之虛構想象。[6]
曹丕之形象,固然可以見仁見智,但縱觀《世說新語》全書,無一正面評價,尤其是多處不實描寫,更是給人留下曹丕過于荒淫歹毒的印象,不能不說是輯錄者有意為之。
三
曹丕個人形象,歷史上褒貶不一,總體來說負面評價居多。除卻個人性格和歷史功績,曹丕無疑還背負著兩個歷史包袱:一為民間長期的“褒劉貶曹”傾向,曹丕作為曹操的繼承人和曹氏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理所當然也會受到一些貶低;一為首開假禪讓真篡位之先河,后代諸多權臣依仗曹丕之發明登上大位,但他們絕不會去抬高曹氏的歷史地位,反而會丑化篡位者形象,嚴防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這樣,從統治階級到下層百姓,都樂于看到曹丕卑劣行徑的故事。
曹氏集團被后人詆毀,還有其個人性格的原因。曹操奸詐,好用酷刑,曹丕氣狹,外寬內忌,兄弟鬩于墻內。這其中多少會有后人演繹的虛假成分,但他們的性格恰好與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背道而馳,所以就有了文人們將他們作為反面教材的機會。
曹氏集團的功過是非千百年來沉沉浮浮,每個朝代都根據自己的利益取舍評價。西晉禪魏而來,奉魏為正統,以顯示自己政權來源的合法性,故對曹氏父子評價較高,陳壽《三國志》、王沈《魏書》對曹氏父子頗多褒譽之詞。從東晉開始,史家文人開始對曹氏之過加以非議,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就認為曹操父子以魏承漢是篡逆之行,晉宜越魏繼漢。其原因是東晉偏居江南,仍然要自封正統,只好像蜀國那樣,貶低曹魏的正統。劉義慶生活的南朝宋代,直接承東晉而來,版圖亦與東晉相去不遠,再加上劉義慶身為王室貴胄,貶低曹魏的正統可以想見。
劉義慶等人刻意貶低曹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南朝宋劉氏乃是漢朝宗室之后。《宋書》、《南史》均著宋武帝劉裕為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之二十一世孫,《宋書?本紀第一》還將從劉交至劉裕的二十一世的名字列出,顯示了劉氏對漢宗室血統的看重和宣揚。不僅如此,史書還處處渲染這一點,以顯示宋代晉的正當性。《宋書?列傳二十一》、《資治通鑒?元熙元年》均有:“高祖(劉裕)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指漢滅亡),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
注釋
[1]宋?汪藻《世說敘錄》之考異錄《尤悔》4?敬胤語
[2]《言語》第22則、《雅量》第40則,《品藻》第19則等等
[3]魏征《隋書》中華書局
[4]《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186頁,中華書局2007年版。
[5]《世說新語箋疏》1049頁,中華書局2007年版。
[6]劉強《世說新語會評》368頁,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1]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2]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
[3]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4]司馬光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6]王根林《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7]張作耀《曹操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