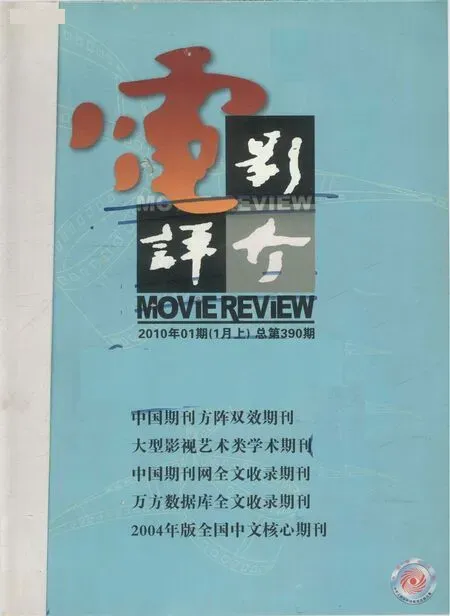華——麗《 傾的城沉之戀影》
周萌萌 暨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華
——麗《 傾的城沉之戀影》
周萌萌 暨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代表作之一,它給我們留下了一個(gè)華麗的沉影,一個(gè)舊上海的傳奇,我們或許津津樂道故事中范柳原與白流蘇演繹的雙城記,但是更多的時(shí)候透過這重重的簾幕,可以聽到作者對(duì)人性的一聲慨嘆,她對(duì)世俗的淡漠譏諷,帶著洞察世情的無奈與悲哀。張愛玲是“鏡子派”的作家,她以自己獨(dú)特的視角,完成了“在傳奇里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留給我們一個(gè)華麗的沉影,一個(gè)美麗的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 張愛玲 人性 視角 傳奇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代表作之一,它給我們留下了一個(gè)華麗的沉影,一個(gè)舊上海的傳奇,我們或許津津樂道故事中范柳原與白流蘇演繹的雙城記,但是更多的時(shí)候透過這重重的簾幕,可以聽到作者對(duì)人性的一聲慨嘆,她對(duì)世俗的淡漠譏諷,帶著洞察世情的無奈與悲哀。她曾說:“因?yàn)槭菍懶≌f的人”,“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后,也只有哀矜”。
當(dāng)時(shí)的一位評(píng)論家譚正璧曾這樣評(píng)價(jià)張愛玲的小說:“選材盡管不同,氣憤總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動(dòng),處處都為情所主宰,所以他或她的行動(dòng)沒有不是出于瘋狂的變態(tài)心理,似乎他們的生存是為著情欲……作者是個(gè)珍惜人性過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終是個(gè)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隸。”《傾城之戀》恰恰是張愛玲這種寫法的典型代表,她筆下的主人公都不是完美的人,都有人性的弱點(diǎn)。他們想要逃脫世情,但是又無法擺脫世情對(duì)自己的控制,他們的身上體現(xiàn)了矛盾的人格。
流蘇與柳原是“不徹底的人物”,而這來源于作者“不徹底的”人物觀。張愛玲拒絕采用“過分簡(jiǎn)單化的黑白劃分”,在小說中對(duì)人物未置臧否,也不對(duì)其進(jìn)行道德評(píng)判,而是在“參差”自然呈現(xiàn)出普通人性的軟弱、退縮和愚妄;情感態(tài)度上,作者沒有分明的愛憎,而是在淡漠的嘲諷中帶著一絲憐憫,鋪陳敘述都帶著一份超然冷靜的旁觀者心態(tài)。對(duì)于批評(píng)者的意見,張愛玲不承認(rèn)這種處理方式會(huì)將人物“過于倉促的送走”或是“典型的中和”,而是認(rèn)為自己采取更真實(shí)的方法塑造“疲憊”的現(xiàn)代人。在她看來,“參差的對(duì)照的寫法”才能“寫出現(xiàn)代人虛偽之中有真實(shí),浮華之中有素樸”,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古典小說“單純、絕對(duì)”和“斬釘截鐵”的寫法,開創(chuàng)出新的風(fēng)格。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她“參差的對(duì)照的寫法”,金斯伯瑞(Karen Kingsbury)認(rèn)為這個(gè)術(shù)語“不僅是勾畫主題和角色的手法,它也作用于敘事風(fēng)格層面——敘事人那揶揄的語調(diào);徘徊于自嘲和放恣,夢(mèng)幻和現(xiàn)實(shí),諷刺和同情之間”。《傾城之戀》雖名為“傾城”,卻不存在美色與傾城的關(guān)系,雖有愛戀,卻不是純粹的真心付與,而更像是一對(duì)精于算計(jì)的男女在博弈后做出對(duì)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相對(duì)于大時(shí)代的戰(zhàn)亂,大城市的傾覆,流蘇與柳原的情愛與婚姻,又有了另一層面的參差對(duì)照——“升格嘲諷”(high burlesque)。小人物的愛戀冠以“傾城”之名,似乎暗喻著這一場(chǎng)愛戀并不是什么驚天動(dòng)地的事情,而是夾雜著太多世俗利益算計(jì)的東西。追究起這場(chǎng)愛戀的開始,柳原無非是尋找一份有別以往的刺激,流蘇則是尋找一個(gè)穩(wěn)定的經(jīng)濟(jì)依靠。范柳原“把女人看成他腳下的泥”,從不對(duì)女人認(rèn)真;而白流蘇則是為了逃離離婚之后寄食娘家遭人白眼的處境。這兩個(gè)人都是“精呱呱”的,范柳原的目的很明確,將流蘇當(dāng)成尋歡的對(duì)象,調(diào)劑自己的生活;白流蘇則是為了一份更好生活。流蘇算的很清楚,這是對(duì)自己殘余青春的一場(chǎng)賭注,贏了,她或許會(huì)得到“范太太”的頭銜;輸了,不過是“聲名掃地,沒有資格作五個(gè)孩子的后娘”。而香港的陷落,將這兩個(gè)人綁在了一起,原有的格局被打破。流蘇在那一瞬,真切的感覺到“在這動(dòng)蕩的世界里,錢財(cái)?shù)禺a(chǎn),天長(zhǎng)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gè)人。”于是,在那個(gè)特定的時(shí)刻,“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然后有了“僅僅是一剎那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cè)谝黄鸷椭C地活個(gè)十年八年”。
恰如張愛玲在《燼余錄》里說:“房子可以毀掉,錢轉(zhuǎn)眼可以成為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里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gè),急于攀住一點(diǎn)踏實(shí)的東西,因而結(jié)婚了。”這段話恰是留院和流蘇結(jié)婚時(shí)心情的寫照,為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匆忙抓住現(xiàn)世中的東西。
從表面上看,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蘇,她終于如愿以償?shù)漠?dāng)上了范太太,然而柳原不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別的女人聽”,完全把她當(dāng)成“正言順的妻”,流蘇難免有一絲悵惘,這一紙婚書,終究沒有成就自己的一份愛情。而從更深層面上來看,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柳原,戰(zhàn)爭(zhēng)使他撕下自己慣于“裝假”的面具,回復(fù)了一個(gè)男子原本的面貌,不再逃避婚姻,他的身上那種“彼得潘”的特性雖未隨著婚姻的到來而改變,但是他戰(zhàn)勝了自己對(duì)婚姻的恐懼。這兩者的得到與失去,又構(gòu)成了一個(gè)參差的對(duì)照。
除了流蘇與柳原的對(duì)照,《傾城之戀》中還有一人與流蘇形成了對(duì)照,她就是薩黑夷尼公主,她名字中的“黑”與白流蘇的“白”恰好是一對(duì)反義詞,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就是白流蘇的反襯,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個(gè)形象投射,仿佛《紅樓夢(mèng)》中賈寶玉與甄寶玉一般。薩黑夷尼在小說中一共出現(xiàn)了三次,第一次是背面出場(chǎng),“披著一頭漆黑的頭發(fā),直垂到腳踝上,腳踝上套著赤金扭麻花的鐲子,光著腳,底下看不仔細(xì)是否伋著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的桃紅皺褶窄腳袴。”第二次是正面,“玄色輕紗氅底下,穿著金魚黃緊身長(zhǎng)衣,蓋住了手……她的臉色黃而油潤(rùn),像飛了金的觀音菩薩,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躲著妖魔。”第三次流蘇見到她時(shí),她已經(jīng)落魄了,“黃著臉,把蓬松的辮子胡亂編了個(gè)麻花髻,身子不知從那里借來一件青布棉袍穿著,腳下卻依舊伋著印度式七寶嵌花紋皮拖鞋”。反觀流蘇的出場(chǎng),一開始就是“臉龐原是相當(dāng)?shù)恼?可是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的清水眼……依著那抑揚(yáng)頓挫的調(diào)子,流蘇不由的偏著頭,微微飛了個(gè)眼風(fēng),做了個(gè)手勢(shì)”,而后她“向左走了幾步,又向右走了幾步,她每走一步路都仿佛合著失了傳的古代的音樂的節(jié)拍”,第二次則是“她自己月光中的臉,那嬌脆的輪廓,眉與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 ,而第三次則頗有些蠻霸之氣,“流蘇慢騰騰摘下了發(fā)網(wǎng),把頭發(fā)一擾,擾亂了,夾叉叮鈴當(dāng)郎掉下地來。她又戴上網(wǎng)子,把那發(fā)網(wǎng)的梢狠狠的銜在嘴里,擰著眉毛,蹲下去把夾叉一只一只揀了起來。”這一對(duì)照,薩黑夷尼的形象仿佛是印度教中的飛天魔女,而流蘇則像是中國(guó)古典戲劇中的花旦。關(guān)于流蘇這一點(diǎn),柳原也有所發(fā)覺:“你不像這世界上的人。你有許多小動(dòng)作,有一種羅曼蒂克的氣氛,很像唱京戲。”關(guān)于她們的命運(yùn),張愛玲很清楚的在《傳奇?再版自序》的指出:“將來的荒原下,斷瓦殘?jiān)?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時(shí)代,任何社會(huì)里,到處是她的家。”所以,薩黑夷尼雖是流蘇追逐范太太頭銜路上的勁敵,但是終究敵不過善于演戲的流蘇。即使她們最初都被命運(yùn)撥弄,然而她們應(yīng)對(duì)世事變化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早就決定了她們之間的勝負(fù)。流蘇善于及時(shí)應(yīng)變,像一個(gè)出色的演員一樣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而薩黑夷尼則像是塵封在歷史中一個(gè)雕像,始終活在過去的時(shí)代中,因而也就造成了她們之間蹺蹺板式的升降沉浮。
《傾城之戀》的結(jié)構(gòu)是反傳統(tǒng)的,相對(duì)于傳統(tǒng)話語中單向、直線、偏重因果邏輯的事理觀照和時(shí)間認(rèn)知,張愛玲的模式更類似是“鋸齒”加“螺旋”式的。男女彼此既進(jìn)且退的態(tài)度,頗似“鋸齒”。而兩個(gè)人的人生軌跡,出而復(fù)回,卻又岔開原點(diǎn),又似“螺旋”。張愛玲的“參差”就是“鋸齒”,她的“對(duì)照”就是“螺旋”,而這“鋸齒+螺旋=張氏風(fēng)格”。這種風(fēng)格衍生出的小說美,具有錯(cuò)綜回映的多重唱式觀感,并以此展演出瑣細(xì)幽微的人生萬象。
《傾城之戀》的結(jié)局多少有些不合傳統(tǒng)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頗類悲劇底色上打上的一點(diǎn)喜色。讀者或許習(xí)于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對(duì)于張愛玲設(shè)定給范柳原和白流蘇兩人的結(jié)局感到一絲不滿。它更像是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談判后雙方達(dá)成的協(xié)議,而不是一個(gè)幸福的結(jié)局。對(duì)此,張愛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這樣陳訴自己的觀點(diǎn):“《傾城之戀》里,從腐舊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zhàn)的洗禮并不將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戰(zhàn)影響范柳原,使他轉(zhuǎn)向平實(shí)的生活,終于結(jié)婚了,但結(jié)婚并不使他變?yōu)槭ト?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xí)慣與作風(fēng)。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jié)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也只能如此。”《傾城之戀》中這種凄清蒼涼的基調(diào),源于張愛玲對(duì)生活的看法,她覺得人生充滿了悲涼感和無力感,“生命如一襲華美的袍子,上面布滿了虱子”,“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愿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感傷”
不可否認(rèn)的是,張愛玲是世俗的,她自己也承認(rèn)“不知從哪來的一身俗骨”。她也一向被評(píng)論家認(rèn)為是“徹底的都市的”、“代表了上海的文明”、“具有城市血液和城市本能”,原因就在于她作品中流露出的實(shí)用的世俗態(tài)度和相應(yīng)的思維方式。但張愛玲的傾向世俗化,并不是說她媚俗,純粹的迎合大眾。她是“鏡子派”的作家,既如實(shí)反映人性的世俗形態(tài),同時(shí)又對(duì)世俗的人性保持著審慎的距離,保持了自己獨(dú)特的一份位置。她以自己獨(dú)特的視角,完成了“在傳奇里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留給我們一個(gè)華麗的沉影,一個(gè)美麗的傾城之戀。
[1] 艾曉明.反傳奇——重讀張愛玲《傾城之戀》[J].學(xué)術(shù)研究,1996,(09)
[2] 陳暉.張愛玲與現(xiàn)代主義[M].北京:新世紀(jì)出版社,2004
[3] 今冶.張迷世界[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4] 李歐梵.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與現(xiàn)代性十講[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2
[5] 劉紹銘,梁秉鈞,許子?xùn)|編.再讀張愛玲[M].濟(jì)南:山東畫報(bào)出版社,2004
[6] 水晶.替張愛玲補(bǔ)妝[M]. 濟(jì)南:山東畫報(bào)出版社,2004
[7] 楊澤.閱讀張愛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
[8] 張愛玲.張愛玲文集[C].北京:華僑出版社,2002
周萌萌,暨南大學(xué)文藝學(xué)專業(yè)2008級(j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