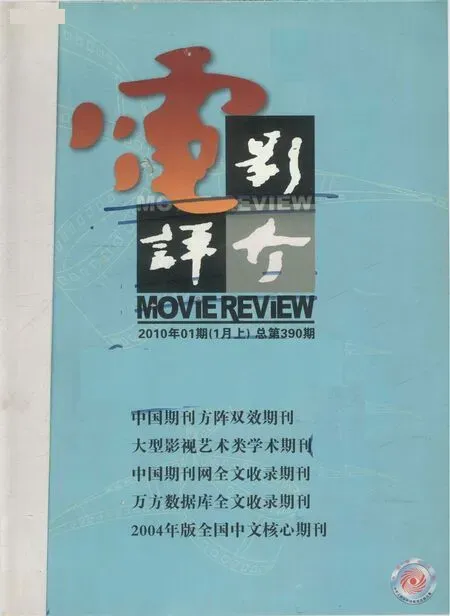日常生活審美化抑或審美符號化
一、“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提出及其形成的具體語境
1、“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提出及其文化背景
“日常生活審美化”(又譯“日常生活審美呈現”)作為西方消費文化催生的產物,這一議題的討論出現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美學界,是由邁克?費瑟斯通提出的。1988年費瑟斯通在新奧爾良的“大眾文化協會大會”上作了題為《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的講演,并將此講演稿作為《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一書的相關章節。同時,包括博德里亞、詹姆遜在內的諸多理論家都對此問題有所論述。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也指出,如今人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聞的被美化的真實世界里,裝飾與時尚隨處可見。 中國學術界對此議題的廣泛關注始自于2000年。是年首都師范大學陶東風教授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議題,由此引發學術界廣泛爭議,并成為近年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作為消費社會催生的一種新現象,日常生活審美化論題在國內學術界的討論并不乏對該現象的深入解讀與理論分析,然就其命題自身的提法及其指向的特定文化語境言說不明。①
這一現象的興起,正是發生在西方社會的七、八十年代。當時西方文化從現代主義轉入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大眾文化在當時的西方社會異軍突起;后現代主義的誕生,正逢資本主義后工業時期大眾文化工業與娛樂文化市場盛行之際。藝術的革命與大膽嘗試,恰好成為大眾文化補充自身文化資源庫空缺的外來給養,它豐富并更新著大眾文化時尚車輪不斷翻新的要求。雅俗距離消失;藝術與生活的邊界變得模糊難以辨別,藝術符號、色彩、形式等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消費品,大到居室、廣場,小至湯勺、杯托等都被精美的設計和絢麗的色彩、圖案、紋飾裝飾。這加速了藝術進人日常生活的步伐。尤其是文化工業中文化產品的生產將眾多的藝術形式或直接將藝術品吸納進來,賦予商品以藝術的附加值。對于日常生活主體的大眾來說,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領域似乎生活被賦予了更多的藝術色彩及其藝術民主化的審美普世感。在文化產品的媒介化和文化產業的推動下,形成了當代社會獨特的審美化的文化景觀。
2、文化工業所倡導的“感覺審美觀”與文化媒介人的參與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種注重感官的“感覺審美觀”。它不需要太多理智的參與,也無需靜心凝視的審美心境,它是一種易知易感的常識化感官美學。英國學者R?w?費夫爾認為“常識確實有一種審美觀——這種審美觀關注事物的外表,因為事物的外表也引發感覺。當涉及到人的時候,就特別有可能對其做常識性的判斷,說其漂亮還是不漂亮。常識不僅審美,同樣也審丑。”[1]這也就表現為娛樂文化中審美與審丑具有等效的功能,即最終是對感覺的欣賞和對感官刺激的需要。日常生活審美符號的泛化與視覺化、身體化,感官化,正是科技發展與商品生產的表現,這是用“感知”、“感覺”文化的“感覺審美觀”取代了“觀念文化”和“理想藝術”的“情感美學觀”。 因為科技的能力與日商生活用品的生產,使得藝術的東西越來越多地被技藝應用于大眾文化用品的符號生產過程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對感覺的重視取代了對藝術世界中人的內心深處情感的珍視。
然而,當代社會這種獨特的文化景觀的出現,除了當時社會文化工業的興起和文化傳媒業的勃興之外。連接著機器與產品的文化媒介人功不可沒。“現代符號生產能力最強的是都市新型文化人。他們善于制造各種新奇的符號商品——圖像、聲音、數碼等。他們的文化消費就是文化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能夠在各種文化符號之間進行生產性轉換。比如“泡吧”消費就能夠生產出酒吧小說,旅游休閑就能夠生產出旅游小說或者民俗圖片。……都市新型文化人作為文化符號商品生產工場的工人,他們和投資者和管理者一起操縱著符號消費市場,……他們巧妙地將意義,從真理價值和人文價值領域,移植到了符號的經濟學邏輯,或者說利潤邏輯之中。”[2]正是這些文化媒介人的加入及其推波助瀾之勢,加速了藝術符號流入市場的速度,拉近了文化工業、文化符號與民眾之間的連接。因此,在整個文化工業的娛樂消費中,“娛樂加速取代了藝術,成為我們主要的、活的文化產品——而且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產品。”[3]
二、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與符號消費
1、流行文化的整合作用
現代主義藝術的形式化傾向和后現代主義藝術反藝術的變革創新,使各類藝術的存在表現出一種現代性的“短暫、過度和偶然”(波德萊爾)特性。然而,“更有趣的是,當新逐漸被體制所吸納,成為一種藝術的時尚而具有商品性質時,新的崇拜便成為反對自身的沖動”[4]正如鮑曼所說,“無論先鋒派藝術如何激進和偏激,都會很快衰落,因為市場收容和銷售這些激進作品的能力在迅速提高。一切帶有反抗性的新藝術都將被市場充分利用。”[5]這種情況具體表現為:在文化領域,后工業時代機械復制的藝術作品已經取消了雅與俗的差距與界限。流行文化消除了雅與俗的不同文化品味,它們以科技的制作方式、流水線式的生產以及商品化的包裝與現代傳媒的宣傳等種種手段和方式培養著大眾審美趣味的一致性。這種流行文化以藝術、文化的符號為標簽,承載著商品本身的交換價值。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為幌子來完成自身的利益獲取。流行文化的內在動機以獲取利潤為驅動原則,以實現資本增殖為目的,通過對大眾藝術、文化、精神方面的虛假需求的外在滿足,整合了人們的個性及審美品味。“而我們所‘消費’的,就是根據這種極具技術性又具‘傳奇性’的編碼規則切分、過濾、重新詮釋了的世界實體。世界所有的物質、所有的文化都被當作成品、符號材料而受到工業式處理,以至于所有的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價值都煙消云散了。”[6]因此,我們可以說,對符號的審美消費或對藝術符號的消費美學,這里的“審美”、“美學”是取其工業審美設計、形式的功能化、符號的感官消費之義。
而這一現象,無疑證明了流行文化自身驚人的同化力量和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把藝術作為“文化資本”的強大吸納能力和整合策略。正如德國學者沃爾夫岡?韋爾施在論述公共空間中的當代藝術時所說:“永遠不能低估語境(市場)的同化力量:稍稍有點離軌的作品,也會被直接整合進審美化的功能性活動中;它們展示的某些新異性,更多地被看成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一個補充。”[7]就拿“后現代主義通俗文化理論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領域之一”的時裝業來說(史蒂文?康納)。時裝業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亞文化風格進行整理、簡化,有時甚至多樣化,以供市場的需要(例子之一是在時裝展中亮相的穩重形式的龐克),在刺激自己的市場的同時吸收亞文化獵物中的能量。”[8]為此,朱麗亞?恩伯利無不沮喪地說道:“盡管反時裝在揭露主導和壓抑的時裝話語或‘生活方式’的過程中可能取得零星的、間斷的成功,但是后現代晚期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傾向通過對其過程的必然在創造,有效地抵消和分解它的潛能。”[9]就此來看,流行文化將藝術形式作為商品的符碼,增加了商品的符號價值,也就消融了藝術的社會對抗性角色, 而成為一種與社會流行時尚同步的同質性文化,即藝術反映著市場的走向和價值觀念并且吹捧消費時尚的新理念。
2、“失序狂歡”中的秩序與審美符號消費
后現代主義藝術的誕生,正逢資本主義后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工業與娛樂文化市場盛行之際。后現代主義文化的顛覆運動與大眾文化的制作策略竟也表現出頗具迷惑性的相似之處:后現代主義文化的多元化吸納、非個性化表達、反藝術的新奇、消解傳統的自由、反規訓的沖動、形式化的狂歡等,與大眾文化的多元拼貼、偽個性表達(個性方式的非個性流行)、視覺的新奇、欲望的自由、渴望沖破傳統的沖動、調侃權威的狂歡等特征,正是這些表面的相似性和可以融合的可能性使后現代主義藝術的革新與大膽嘗試,恰好成為大眾文化補充自身文化資源庫空缺的外來給養,它豐富并更新著大眾文化時尚車輪的不斷翻新的要求。所有曾經意味著革命的后現代主義文化實驗,在消費社會的技術仿像與批量復制過程中,淪為僵死而又絢爛的時尚符號,而它內在的生命與意義已經蕩然無存,符號變成了失去意義和深度的“死尸”或“排泄物”,充斥于后工業社會的精神荒原之上。文化工業把消費對象朝向所有的人群,有文化的沒文化的都在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與普及化購買中,似乎成為了后工業時代的“文化人”。尤其是大眾文化也將消費對象指向了叛逆的一代青年,借用現代藝術與反叛事件中的特定符號或是被符號化,使其眾多的藝術實踐行為與革新嘗試都最終淪為商品的附加值,把這些新奇的、叛逆的符號拼貼成為“文化衫”進行批量的兜售,繼而從中牟取暴利。這樣既安慰了叛逆的一代青年的激情與騷動,又使他們在叛逆符號的消費與幻想天堂巡游之后,然重新回到現實時卻徒留下精神的空虛。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將占生活總體消費的大部分投入作為我們情感消費的投資,拋撒于日間快樂的歡樂場。在假日勝地、廣場、交易會、超市、游樂園、購物中心、酒吧、歌舞廳等場合,這些都成為人們放松的特定空間。他們盡情的玩、盡情的放松,這是一個文明秩序統治下的“秩序失序”的場所,它們散發出特有的誘惑,身體、眼睛、耳朵、情感等都在非控制狀態下經歷了“放縱”的體驗和自娛的快樂,流汗的發泄與恣意扭動的身體宣泄,實現了片刻的自由放縱和越界的刺激。然而,破壞的沖動與顛覆的欲望在“失序”狀態下,重新回歸從前的平靜,涌動的波浪重新退回河谷,消失的“堤岸”又復現于眼前。 其結果就是,“符號變成了失去意義和深度的‘死去的意義之代碼’,復制把同樣的信息無限度地廣泛蔓延。影像符號在當代條件下無窮增長和擴張,……復制取代生產,意義被符號和代碼的增值所取代,同一的無窮復制取消了意義的存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空虛的,無根的后現代世界。”[10]藝術自身的反思性與批判立場,在后現代大眾文化的恣意宣泄和縱情狂歡中被徹底地消解了。藝術的使命淪落為商業化的審美符號游戲與仿真復制中,審美的東西向審美符號化的消費轉化,藝術迎來了它不可抗拒的衰敗與死亡。
三、真實消失之后,世界性審美疲勞時代的到來
是審美疲勞,還是審美匱乏?在后工業社會的消費時代,琳瑯滿目的商品,飄飛閃耀的廣告,誘人且具有鼓動性的廣告詞,媒體的全天候宣傳,使人們陷入商品的購買與消費的狂潮之中,對虛假需求的瘋狂追求,遮蔽了個體真正的需求,也導致物質的滿足與精神的需求嚴重脫節。技術引領的大工業時代,個體成了被流行文化與娛樂消費牽引著的被動承受者,一切被這些虛假的需求所掩蓋,完成著大眾文化撫慰民眾和資本增值的目的。我們的需求看似在公園、電視、電影、超市、市場、旅行社等場所得到滿足了。但是這些活動帶給我們的快樂越來越短暫、微弱,而精神領域的空虛、壓抑、無聊感卻越來越強。瘋狂的購買和消費可能暫時以生理上的消費快感,視覺上的刺激等轉移了對心靈空寂的注視,但卻無法消除更大的孤獨與虛無感。
因此,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缺失的或渴望的都被以商品的形式向民眾兜售,這些喪失了意義的符號形象,盡管它曾是活物的象征。而且,這些商品形象即物象符號往往冠以審美的名義進行審美符號的情感消費。事實上,“透過大眾傳播我們已經看到,各類新聞中的偽善煽情都用種種災難符號(死亡、兇殺、墻報、革命)作為反襯來頌揚日常生活的寧靜。而符號的這種冗長煽情隨處可見:對青春和耄耋的稱頌、為貴族婚禮而激動不已的頭版頭條、對身體和性進行歌頌的大眾傳媒——無論何處,人們都參與了對某些結構的歷史性分解活動,即在消費符號下以某種方式同時慶祝著真實自我消失和漫畫版自我復活。家庭在解體嗎?那么人們便歌頌家庭。孩子們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們便將童年神圣化。老人們很孤獨、被遺棄?人們就一致對老年人表示同情。還有更為明顯的是:身體功能越是衰退,越是受到城市、職業、官僚等控制和束縛系統的圍困,人們就越是對身體進行贊美。”[11]至此,我們將迎來或者已經迎來了一個世界性的審美疲勞時代的到來(博德里亞),“通過消費,最后我們只是來到了一個充滿了普遍化、總體化競爭的社會中,這種競爭表現在一切層面:經濟、知識、欲望、身體、符號和沖動”。[12]
注釋
①“日常生活審美化”(又譯“日常生活審美呈現”)——這一議題在當前中西學術界的爭議,及其作為西方消費主義文化興起后催生的產物。本文對這一話題的信息可以參見桂俊榮女士的《審美與生活》、陳正勇先生《文化美學視野中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批判》兩篇文章,及其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韋爾施《重構美學》等著作。
[1][2][英]R?w?費夫爾著 丁萬江 曾艷兵 譯.西方文化的終結[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23頁,第132頁,
[2]張檸.文學報——自由談版.符號商品和消費者[J].2005-12-29
[4][5]周憲 著.審美現代性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年版,第241頁,第241頁
[6][11][12][法]讓?博德里亞 著 劉成富 全志鋼譯.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頁,第86頁,第183頁
[7][德]沃爾夫岡?韋爾施 著 陸揚 張巖冰 譯 重構美學[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頁,
[8][9][英]史蒂文?康納 著 嚴忠志譯.后現代主義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97頁, 第297頁,
[10]劉象愚 楊恒達 曾艷兵 主編.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