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不移地弘揚白求恩精神
/季 余
堅定不移地弘揚白求恩精神
文/季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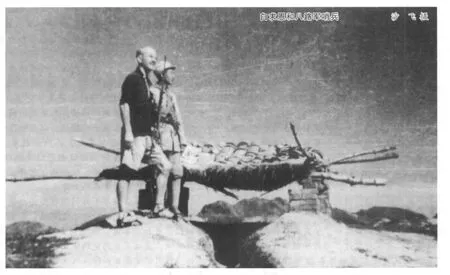
今年3月3日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誕辰120周年。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72年前,他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中國人民最艱苦的歲月里,真心誠意、竭盡全力地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最后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民永遠懷念這位可親可敬的朋友,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這位真正的純粹的共產黨人。
我們都知道,白求恩犧牲后,毛澤東立即寫下了著名的 《紀念白求恩》這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學習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指出,從這點出發,就可以成為 “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是對白求恩的高度評價,也是我們共產黨人要終生堅持的無產階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事實正是如此。正由于白求恩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他才能在國際法西斯勢力猖狂肆虐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然地舍棄自己優越的生活條件,拋棄自己已有的名譽地位,不顧個人安危,英勇地奔赴反法西斯的戰場。正因為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發揚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他對人民對同志極端地熱忱,對工作對傷員高度地負責任,總是給予無微不至的愛護。他寧肯自己挨餓受累,也要盡量減輕傷員的痛苦。他曾一連六七十個小時不下手術臺,一口氣為一百多位傷員施行手術。他把布鞋拿給傷員穿,自己穿草鞋,甚至打赤腳。他在手術之余,還自己編寫教材,為中國培養醫護人員。他是技術高超的專家,卻拒絕享受高于別人的津貼。他曾說: “你們不要把我當作古董,我是來工作的。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來使用。”這種感天地、泣鬼神的自我犧牲精神,不知道感動和激勵過多少中國的軍民。可以說,中國抗日戰爭后來的勝利以及中國建設事業偉大成就的取得,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我們黨充分發揚了這種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
就像許多偉人、英雄以及一切革命真理有時也會遭到曲解和攻擊一樣,在今天,白求恩和他的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也受到了曲解、非議乃至誹謗和謾罵。十多年前,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著文說,提倡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就是 “完全扼殺人的個人性”;提倡 “為共產主義這樣一種全人類的 ‘共同理想’貢獻一切”,就是 “強迫你犧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殺人”,這是 “很可怕的”。錢先生這番高論,活活畫出了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的靈魂。個人主義者堅持剝削階級世界觀和利己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要他們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無異于要他們的命,當然 “很可怕”了。可是,白求恩是共產主義者,堅持的是共產主義世界觀,是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后者和前者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在共產黨人看來,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它的最終實現而奮斗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終生追求的價值目標。提倡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當然不是不要個人利益,但必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當個人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發生矛盾時,要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這是完全自覺自愿的,絲毫沒有“強迫”的成分。但這在堅信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主義者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他們也就無話可說了。
無獨有偶。繼錢先生之后,2009年第11期 《炎黃春秋》雜志上又刊出 “廣州學者”林賢治先生的一篇同樣是張揚 “個人主義”的文章,題目是 《白求恩:孤獨的異邦人》。這回不是直接謾罵白求恩精神了,而改為從作者的主觀想象出發,用虛構和幻想,用斷章取義和歪曲文獻的手法,給我們 “塑造”了一個與真實的白求恩絲毫不搭界的 “白求恩形象”。文章認為,白求恩的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只是外在的表現,他內心深處還保留著 “個人主義的特質”;在組織關系上他是共產黨員,本質上卻是一個保留著“個人化”,追求著絕對 “自由”的“西方知識分子”,一個充滿著 “幻想的熱情”的 “烏托邦主義者”。據說,這表現在他與黨組織、與革命戰爭的格格不入上。他是受斯諾的 《西行漫記》等書的 “誘惑”才來到中國的,并沒有真正融入中國的革命隊伍,始終不過是一個 “孤獨的異邦人”……聽著作者這樣的敘述,簡直像是在聽一個新編的拙劣的神話。
先來看林先生是怎樣描寫黨組織以及白求恩與黨組織的關系的。林文說,黨組織是一個 “機械主義的”, “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機構,它要求個人 “無條件服從”, “但知識分子不能。他要在組織內部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無論何時,維護個人的尊嚴甚于生命”。這里的所謂“組織”純屬虛構。戰爭年代的共產黨內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何來 “官僚化、非人化”?這只要看看毛澤東在延安穿著打補釘的褲子給席地而坐的戰士們作報告的照片就明白了。黨作為組織當然要有組織紀律,不過這種紀律是建立在自覺基礎上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當一個黨員認識到黨的歷史使命同歷史發展規律相一致,認識到黨的紀律同黨的奮斗目標相一致時,他就會感到紀律與自由是統一的。他既是組織的一分子,又是一個獨立的奮發有為的個人。白求恩正是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到戰火紛飛的中國來,到槍林彈雨的前線去,都是主動請纓的。他在工作崗位上總是主動地創造性地工作,充分發揮了“自身的獨立性”,從而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他對黨組織非常忠誠,非常敬重。當他把黨證交給毛澤東時,他是那樣的激動,仿佛一個游子回到了久別的家。不管在多么困難的條件下,也不管工作多忙,他都堅持給美國、加拿大和中國的黨組織寫信,匯報工作。……只有戴著有色眼鏡如林先生那樣的人,才會從這里看出什么黨組織對白求恩的“壓抑”和白求恩同黨的疏離來。
再看看林先生怎樣描寫 “革命戰爭”以及白求恩與革命戰爭的關系吧。林文認為, “革命戰爭”容不得 “個人友誼、欲望、感情、志趣之類”。 “倘若革命不是以一種盡可能民主的、溫和的形式進行,拒絕 ‘請客吃飯’”,批判 “人類之愛”, “知識分子與革命的沖突便變得不可避免了”。這真是對不起,抗日戰爭不可能按照林先生的愿望, “民主的溫和的”,像 “請客吃飯”那樣進行,否則就等于不戰而束手被擒,引頸就戮。革命戰士也不可能有什么抽象的 “人類之愛”,白求恩只愛中國人民和他的戰友們,他經常表示 “要用最大的體貼、愛護和技術”來 “報答”傷員們。他不可能去愛日本鬼子,他常憤怒地說: “我們的敵人是法西斯強盜,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人道主義。”在革命的大熔爐里,白求恩和他周圍的同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和革命的友誼。他對革命的最后勝利充滿了信心:“我相信,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這便是真實的白求恩。在這里,人們看不到任何白求恩與革命的“沖突”,因為白求恩根本不是林先生構擬的那種“個人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而是鋼鐵般的無產階級戰士!
林先生為什么一定要堅持說白求恩是一個始終沒有融入中國革命大家庭的 “孤獨的異邦人”呢?原來他抓到了并夸大了白求恩有時流露出來的思鄉情緒和有時對長期收不到報刊雜志、聽不到外界消息而感到的 “遺憾”。其實這些在我們看來是完全正常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遠離祖國,在語言和生活習慣都不一樣的異國他鄉工作的人,產生思鄉情緒不是很正常的嗎?在殘酷的戰爭環境里郵路不通,消息阻隔,誰會沒有一點遺憾呢?但這些都不是白求恩的本質。 “德不孤,必有鄰”。白求恩這樣具有共產主義道德的人在人類的正義事業中是不會孤獨的。他在西班牙很快便同那里的反法西斯戰友們融為一體;來到中國先后受到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高級領導人熱情的接待,到了前線,他熱情開朗、詼諧幽默的性格使他很快便與同志們打成一片。他曾激動地說:“沒有任何種族、膚色、語言、國家的界線把我們分開。”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示過:“這兒生活相當艱苦,……但是我過得很快樂。” “我萬分幸運,能夠來到這些人中間,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已經愛上他們,我知道他們也愛我。”這是他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見, “孤獨”不是白求恩的感受,而是林先生的杜撰。
我們不得不說,林先生在虛構 “白求恩形象”時采用了不夠光明正大的手法。例如,1939年末,為了向歐美人民宣傳八路軍英勇抗日事跡,爭取國際援助,揭露日寇在中國的暴行和蔣介石封鎖解放區的真相,白求恩準備動身回加拿大一趟,這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他在向朋友報告計劃的信中說: “中日戰爭將是一個長期的戰爭,我打算持久下去。我們計劃這次戰爭起碼要持續十年,我們必須幫助這個優秀民族比我們現在做的多些。” “這兒的人需要我。這兒將是 ‘我的’生活領域。我一定回來。”但是,這些內容統統被省略了,而只突出他臨行前想到了 “咖啡、上等烤牛肉,蘋果派和冰激凌”等(這些在西方生活中其實是很普通的)。這樣便使引用的文字儼然成了白求恩 “追求享樂”的自白。于是林先生斷言,白求恩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反烏托邦主義 (空想主義)者”, “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獨立王國’。”這實屬強詞奪理,乖謬已極!
行文至此,不妨化用杜甫的一首詩: “白求恩氏高風范,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錢先生的辱罵也好,林先生的編派也罷,都無損于白求恩精神的光輝,只能暴露他們一類人的不良用心。這種情況表明,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弘揚白求恩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各行各業都弘揚白求恩精神,社會風氣必將進一步好轉,唯利是圖的假藥、假酒、毒奶粉之類必然大大減少。公務員們弘揚白求恩精神,焦裕祿、孔繁森式的英雄模范必會更大量涌現,反腐倡廉也會抓到“源頭”,貪官、庸官或將大量減少。誠然,在私有制還存在的條件下,徹底地消除私心雜念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高舉起“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的旗幟,建設社會主義就會有不竭的精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