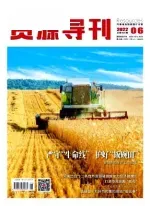報刊文摘
報刊文摘
最低工資上調陷競爭怪圈
截至目前,今年已經有北京、上海、四川、江西等14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從調整后的情況來看,目前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15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14元。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已經陷入競爭怪圈,各地區只是盲目跟風上調,調控過程尚缺乏公開透明的依據。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車偉就指出,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卻也增加了企業用工成本,從而增加了物價上漲壓力。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彭劍鋒表示,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只是盲目跟風調整,并未考慮自身特點,未來該標準的調整可以和物價掛鉤,并可讓不同地區根據地區內部勞動力成本來進行測算,這樣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才更有實際意義。
(摘自5月2日《北京商報》)
從“托兒”看公共服務的漏洞
近日,陪朋友去城東北一處辦理車檢等事務。人尚未下車,“托兒”們已圍了上來,說是這里停電了,可以帶我們到城西或者城南去辦理相關手續。出于警惕的本能,我們還是要到該辦事機構看個究竟,發現真的停電了,無公務人員接待,也無相關服務公告。
情急之下,車主只好從 “托兒”中選擇一貌似干練可托之人,談妥300元協助辦理相關手續。而在城西的車檢點,歷經交稅、車檢、交保險費、選車牌、辦車證等諸多繁瑣環節,到處都能看到“托兒”領著“辦證菜鳥”穿行其間的忙碌場景。
據悉,除了前述車輛辦證外,“托兒”在辦理勞動保險、土地征用、房產交易等諸多領域大量存在。“托兒”們的“親民”,顯然是為了從中漁利。而相關公職人員呢?難道納稅人沒有供養著他們?從“托兒”身上不難看到公共服務的差距和漏洞有多大。
(摘自5月2日《長江日報》)
“最美女教師”為何沒編制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語文教師張麗莉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救出兩名學生,被譽為“最美女教師”。可就是這樣一位優秀教師,居然沒有編制,也沒有醫保。也就是說,她是一名教師中的“臨時工”。
現實中,青年教師中沒有編制的情況很多,特別在一些實現教師陽光工資的地方,因總數固定,每進一個教師,就要從總數里分走一杯羹,導致其他教師的陽光工資下降。所以,許多地方嚴控進人,導致許多年輕人,畢業多年都是無編制的“臨時工”。
一方面,為了爭奪編制,家有門路者不惜送錢送禮,打通關系把資質平庸、成績不好或是缺乏責任心的年輕人送進正式的教師隊伍。另一方面,許多熱愛教育事業、業務出眾,懷揣教師夢的年輕人,卻不得不離開這個隊伍。
教育行業留下的,本應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這些年來,我們是否把最適合做老師、最有資格做老師的人留在了教師隊伍里?我們還需反思,對于那些委曲求全留下的精英,為何要讓他們承受低工資、無保證、無尊嚴,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委屈與痛苦呢?
(摘自5月18日《廣州日報》)
賴昌星案一審凸顯“追贓”挑戰
5月18日,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賴昌星無期徒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違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繳。記者獲悉,有關部門正在進一步了解賴昌星在國外的資產狀況,并擬與加拿大簽訂“關于返還和分享被沒收財產的協定”。
對于兩國如何分配被沒收財產,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這主要視該國在執法合作中貢獻的大小來定。“這是斗爭和妥協的產物,也是基于解決問題的需要。”他表示,將外逃犯罪嫌疑人引渡或遣返回國內,對中國有力打擊犯罪、特別是外逃的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意義重大,利大于弊。但不能忽視的現實是,追逃成本大、追贓返還難,大量嫌疑人因無被引渡之憂且提前轉移大量財產,而在異鄉逍遙法外。具體到遠華案件,追贓并不是那么順利。
今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其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增設了第五編“特別程序”,其中第三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大大壓縮了外逃犯罪嫌疑人生存空間,同時也為中外執法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反腐敗國際合作問題專家陳雷說。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第18期)
官員任免:將“網絡公示”進行徹底
人事領域的不正之風,正被一種新的監督方式所制約,這就是微博上的集中圍觀。
山西長治“神童官員”扎堆以及“女商人吃空餉15年變身副縣長”、湖南湘潭“擬任90后女副局長”的事件調查和處理結果,已經陸續曝光。這幾起因微博發酵的事件刺激著大眾的神經,也推動著問題的處理。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李瑞昌副教授認為,“以前這類不正之風也存在,但是因為傳播的途徑有限,受關注度也不高,所以很難統計。”李瑞昌認為,電子政務的推開,干部選拔的網絡公示程序,使得過去可能發現不了的問題,現在容易被發現。
李瑞昌也坦言,目前全國鄉鎮一級政府中,還無法完全做到電子政務的配套,很多信息的紙質公示效果也并不明顯。“不過,縣級政府的干部選拔任命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網絡公示,今后可以考慮在縣級政府網上公示鄉鎮干部的選拔任用。”
要實現“讓選人用人權在陽光下運行”,李瑞昌指出,應該進一步“加大網絡公示的力度,尤其是對于擬提拔任用的干部,其工作年限、業績能力應該有更加詳盡的介紹,最好采用公開競聘的方式”。
((摘自5月2日《第一財經日報》))
該下河的不僅僅是環保局長
日前,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表示,“檢驗溫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門報上來的數據為準,要以環保局長和公用集團董事長帶頭下河游泳作為河水治理好的標準”。
這真的是個好辦法。想要徹底治理水源污染,環保局長確實是首當其沖。不過,環保困境,單靠環保部門,實在難以打破。
當下,不少地方奉行的標準是:“小污染可以倒、大污染則要保”,甚至是:“污染事小,財政事大”。一些污染企業的存在,會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對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但其對于地方財政收入的貢獻卻是不可忽視的。地方政府官員權衡利弊,很可能多數是求經濟效益和政績打眼而放棄環保。
眾所周知,環保部門通常只是地方政府的下屬部門,上級下的命令,環保部門敢不執行?曾有環保官員無奈地說:“有些地方的經濟發展從來不考慮環境和資源的承載量。”如今環保部門責大權輕,沒有地方政府其他部門的全力配合,環保局長把命搭進去,也未必真能見到環保治理的真效果。
有網友戲稱,要說下河游泳,最該下河的非市長、市委書記莫屬。當然,要是市長能夠帶著三套班子一起下河,那老百姓肯定對于環境治理相當放心。
(摘自5月8日《北京晚報》)
武漢平均2年消失3個湖“城市之肺”變“城市之淚”
曾經數百個大小湖泊星羅棋布的武漢,當之無愧地被稱為“百湖之市”。然而,最近幾年,大小湖泊周圍鱗次櫛比蓋起的高樓越來越多。曾經引以為豪的湖泊,給市民帶來的不再是美景和水韻,而是環境惡化和城市內澇。被生態學家譽為“城市之肺”的湖泊,變成了“城市之淚”。
據武漢市水務局統計,2002年武漢市共有200多個湖泊,10年之后的今天,只剩下了160多個。其中,消失最快的是中心城區,新中國成立初的127個湖泊現在僅保留了38個,平均每兩年消失了3個湖。
目前城區僅剩的38個湖泊,情形也不容樂觀。曾經清冽甘甜、捧之即飲的湖水,不少已變得污濁臟膩,甚至臭氣撲鼻,垃圾遍布;碧波蕩漾的水面一片一片遭到蠶食,變成繁華的街市、寬闊的馬路和成群的樓宇。許多環保人士呼吁:如果不進行搶救性保護,這38個湖也難逃消失的噩運。
據武漢水務部門統計,1995年以來,這38個湖泊的總水面減少了1083公頃,相當于25個沙湖的水面消失了。而環保部門對湖泊水質的監測數據顯示,全市沒有一個湖泊的水可以直接飲用,中心城區絕大部分湖泊已不適合游泳,甚至湖撈起來的魚也沒人敢吃。這座因水得名、因水而優的城市,正忍受著來自各方的傷害。
(摘自5月9日《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