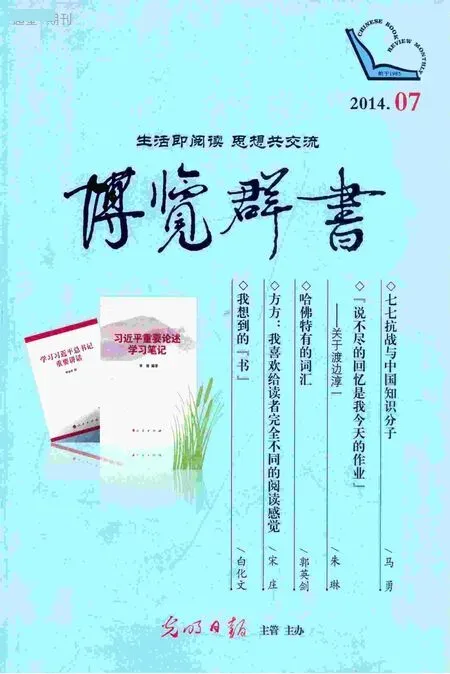獨上高樓,望盡無涯路——讀彭程的散文
○袁利榮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起,彭程的散文特別是他的一些讀書隨筆,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因為在讀彭程的文字的過程中我聯想到了一個詞:辭費。“辭費”這里是中性詞,是指文辭鋪張使人有炫耀之感的意思。
彭程自述,在編輯職業之外,他有兩個也只有兩個愛好:讀書與寫作。在《寫作的理由》一文中,彭程是這樣坦白自己的:“說來著實慚愧,不會跳舞,不會搓麻,不會打撲克,甚至沒有耐心看電視。既然如此,謀生的職業之外,又如何排遣生存的寂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所作的選擇是讀書和寫作,或者更進一步,讀書為主,寫作為輔。”彭程的“老實”或“大聰明”就在于他明白自己應該以“讀書為主,寫作為輔”。除了主要依賴自身內在激情的抒情詩人,從事任何體裁的文學作品寫作的人,如想有“大出息”,都必須以“讀書為主,寫作為輔”。真正的寫作,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閱讀的補充或升華。

彭程前些年出版的幾冊散文隨筆集《紅草莓》、《鏡子和容貌》和《漂泊的屋頂》,我都先后讀過。我敢確信一點:彭程讀書的數量,與他的同齡人相較,肯定是位居前列的。我讀的書不算太少,但在彭程讀書隨筆中羅列并加以點評的上百個書名,有許多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受過嚴格的高等教育之訓練的又沒有其他“愛好”的彭程,首先是一個腹笥充盈的苦讀者,其次才是當代文壇上似應予以特別關注的散文作家。
最近,我仔細閱讀了他新出的散文集《急管繁弦》,我感到彭程成熟了。相對于《急管繁弦》,前三本書是鋪墊;相對于前三本書,《急管繁弦》是登高。彭程的散文獨立不依,自出機杼,充滿了王小波所推崇的“情趣和智慧”,十分耐讀。我不揣淺陋,對《急管繁弦》中的部分作品做些浮光掠影式的文本解讀。
《娩》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描述了寫作的艱難以及超越艱難后巨大的成就感與幸福感。彭程是這樣“夫子自道”的:“你不喜歡喧囂,又羞于向外人吐露自己,這時這支筆成全了你。你寫下自己的熱情與悲哀,夢想與譫妄,開始不過是出于一種幽秘的好奇心,還有一點兒自我表現的愿欲。但有一天你卻發現再也無法放下筆,盡管那引起你惡毒詛咒的寫作的艱難,依然纏繞著你。”彭程的明智就明智在他洞悉了“寫作的艱難”,并清醒自覺地迎難而上的。而寫作尤其是散文的寫作,在當今絕大多數作者那里是沒有難度的,甚至是一點難度也沒有的。彭程將“寫作”定位于“創造”,并宣稱:“創造是消滅死”。可見,彭程是想借助自己手中的筆,走向永恒。而只有在追求永恒的作家那里,“寫作”才會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急管繁弦》也是集子中一篇的篇名。以篇名作書名也可看出作者對自己這篇作品特別的看重。這篇作品寫透了中年人生對時光匆促的徹骨感受,濃墨重彩,繁復鋪陳,仿佛白居易的《琵琶行》,“嘈嘈切切錯雜彈”,中年人生的無奈、不甘以及“拼最后一把”的決絕,宛如丹青高手的工筆素描,纖毫畢現,寫得縱橫捭闔、不同凡響。同時,“急管繁弦”這四個字也準確地寫照了作者自己的當前人生狀態,一些同齡人讀來也一定會有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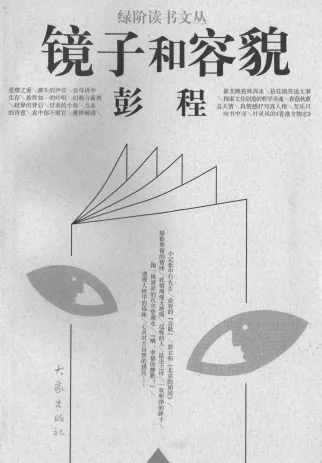
《破碎》闡述了這樣一個哲理:具備“完整的內心”和內心的定力的人必是非凡的,而沒有“完整的內心”和內心的定力的人定是平庸的。《父母老去》將歲月在不知不覺中帶來的生命變化寫得如鐫如刻、觸目驚心!
《燕園的半日》兩萬余字,是收入集子中的篇幅最長的一篇散文。作者于仲夏一個綠意深濃、陽光燦爛的下午,重返北大校園——美麗的燕園,自己曾在此生活了四年的故地,沿著熟悉的未名湖邊的小路,獨自盤桓了整整半日。此時作者大學畢業已近十七年。該文詳盡記述了自己在這半日內的所思所想,對人生的感悟,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因所思所想已進入人生哲學的高度與層次,所以讀來并不覺得冗長,相反,隨著閱讀的推進,作者的所思所想深深感染了讀者。寫作此文時作者三十七歲,此文濃縮了作者近半生對人生的思考,是一篇“大散文”。
《解讀節氣》是彭程散文中特別才華橫溢的一篇,六千余字的篇幅幾乎全是詩性的充滿彈力與張力的語言。通過對二十四節氣的詩性解讀,春風的溫暖,秋雨的纏綿,陽光的恩賜,雨露的無私,炎熱的夏夜,雪覆的原野——此文全部詩性的解讀全部指向:揭示大地上的秘密連同大地上的故事。而大地上的秘密與故事,不正是以大地為舞臺的一代又一代人生的秘密與故事嗎?二十四個節氣,二十四塊積木,彭程用它們拼出了一篇十分機智且耐讀的“才子散文”。該文無論措辭或謀篇,都是才子式的,或充滿才子氣質的。彭程充滿才子氣質的散文還有《地圖上的中國》和《大事不著急》等篇,都是我百讀不厭、特別喜歡的。
《歲月河流上的碼頭》將中華民族一年四季中的民俗節日比喻為“歲月河流上的碼頭”——作者像導游一樣,帶領讀者游覽了幾個“碼頭”,并就碼頭上的“風景”向游客們做了傳神的解說。標題《滾燙的石頭》是用來比喻民歌的——該文動情且不厭其詳地抒寫了民歌的深摯與純粹,同時該文還告訴我們:民歌之所以深摯與純粹,是因為民歌的詞曲里蘊含著兩個字——“神性”!滿世界飄蕩的流行歌曲,夜總會點歌本上的淺斟低唱或歇斯底里,與已漸行漸遠的民歌,與在物欲橫流的后工業化的今天只沉睡在純精神世界里的民歌,是完全不相干的。《王子與玫瑰》對“愛”做了透徹乃至極致的論述。
《閱讀的季節》闡述了閱讀的內容、范圍與年齡、愛好之間的有趣關系,同一本書“此一時彼一時”迥然相異的閱讀感受與領悟,讀來很受啟迪。《在母語中生存》對母語與作家的關系,包括母語與人生的關系,做了非常精湛的論斷。該文告訴讀者:失去了母語及其所支撐的環境,人生也就沒有了依托。厚厚一大本的《急管繁弦》中幾乎篇篇文章都值得評點,但為了節省筆墨我只好帶著割愛的心情強做取舍。
在《抵達事物核心最近的路途》中,“路途”指的是詩歌。彭程在該文中表達了自己對詩歌的理解與認識,包括敬畏乃至膜拜的心情。彭程認為“詩是文學的最高境界”,“作為一名散文寫作者,散文中的詩意一直是我心儀的一個維度,一種尺度”。“我認為,倘若一名散文家的作品被認為具有某種詩的特質,是一種很高的褒獎。我期待著將來的某一天會得到這樣的獎賞。”作為彭程散文的一個認真的讀者,同時又是一個對詩歌十分熟悉的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彭程的散文是富有“詩意”乃至“詩性”的。這里“詩意”指的是文章外在呈現出的“詩的氣韻”,而“詩性”指的則是文章內在蘊含著的“詩的血脈”。“詩意”能為文章鍍上一層光芒,而“詩性”則賦予文章能流傳下去所必需的一種“靈光”。在彭程那些充滿才子氣質的篇章中,“詩性”是直觀的;而在彭程數量上要占絕大部分的那些解讀人生和生活以及讀書隨筆之類的篇章中,“詩性”則是潛隱的。“詩性”在彭程大部分散文中之所以是“潛隱”的,是因為恣肆深透的“闡釋性”遮蔽了“詩性”。彭程早年如果寫詩的話,我想十有八九會成為一個優秀的“闡釋性”詩人。彭程的“自我期許”是以堅實的面向當代與未來的“文本存在”為依據的。在彭程散文的字里行間,散發著強大的“理性”。彭程散文的風格與法國16世紀后半葉的大散文家蒙田十分類似——而蒙田恰恰是彭程十分仰慕的“域外大師”。
彭程剛屆四十幾歲,春秋鼎盛,“可能性”尚多。就散文寫作本身而言,彭程應該算“根正苗紅”。愿彭程在現實人生中能夠繼續拒絕各種誘惑,堅守清靜平淡的書齋生活,直到善終如始——至死不移人生初始時對永恒之目標的追求。我擬借用宋朝大詩人晏殊極著名的詩句“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比喻,期冀彭程再經過若干年的含辛茹苦與有效積累,能勝利穿越“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人生長途,成功進入大器晚成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最高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