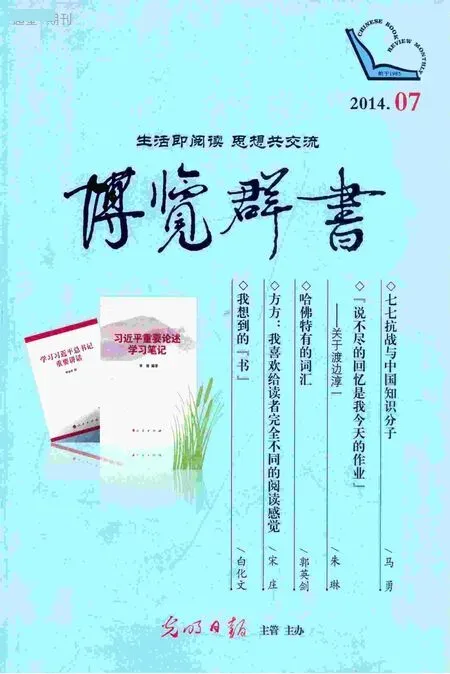經(jīng)典閱讀:讀,還是不讀——當代中外閱讀的現(xiàn)狀與前景
○郭英劍
(2010年4月23日,國家圖書館)
什么是經(jīng)典,為什么要閱讀經(jīng)典
中文語境下,經(jīng)典通常指“傳統(tǒng)的具有權(quán)威性的著作”。它有幾個特點:第一,經(jīng)久不衰;第二,具有典范性或者說權(quán)威性;第三,是經(jīng)過了歷史選擇的、最有價值的書。在西方語境下,經(jīng)典有兩個詞匯,一個是classics,一個是canon。classics一般用于指代文學作品。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應(yīng)該至少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具有良好的品質(zhì);第二,具有良好的聲譽。第二個西方語境下的詞匯是canon,這個詞的來源是希伯來語,其意為一種衡量的尺度。后來這個詞匯多被宗教社會所用,特指那些經(jīng)典的、官方承認的重要作品。再后來,canon這個詞運用到了文學作品當中,指代那些傳世的精品之作。
通過對比,我們發(fā)現(xiàn)中西方對于經(jīng)典的認識有共同的特征:既要有優(yōu)良的品質(zhì)也要有良好的聲譽。那么,我們?yōu)槭裁匆ラ喿x經(jīng)典呢?
人們一般認為閱讀經(jīng)典有兩大理由:第一,經(jīng)典作品微言大義。雖然它是一部小小的書,但是隱含了大大的道理在里面。人們閱讀之后,能夠從中悟出一些為人處事以及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道理。第二,閱讀經(jīng)典作品有現(xiàn)實意義,即它對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在我看來,閱讀的理由是:人生太短,好書太多,我們只有去閱讀經(jīng)典。
中外當代閱讀的現(xiàn)狀與問題
經(jīng)典閱讀在當代社會經(jīng)歷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對經(jīng)典閱讀已經(jīng)提出了各種質(zhì)疑。根據(jù)國內(nèi)最近的調(diào)查,中國連續(xù)六七年來閱讀率一直在下降,目前已經(jīng)低于50%。很多人說沒有時間讀書,還有一些人說不習慣讀書,這兩者加起來,超過70%。中國每年出版圖書超過30萬本,但是家庭戶均消費圖書還不到兩本,據(jù)稱是世界上人均閱讀量最少的國家之一。復旦大學做過一個調(diào)查,說我們目前大學生閱讀本專業(yè)經(jīng)典著作的只有15.2%,閱讀人文社會科學經(jīng)典著作的有22.8%,閱讀專業(yè)期刊的有9.3%,閱讀英文文獻的只有5.2%。而美國大學生平均每周的閱讀量要超過500頁。以上兩組數(shù)據(jù)基本上反映了我們的大眾與大學生閱讀的普遍狀態(tài)。
就中外當代閱讀的現(xiàn)狀而言,兩者有一些相同點。第一,經(jīng)典閱讀受到?jīng)_擊,經(jīng)典閱讀量與興趣有所下降。第二,電子讀物、網(wǎng)絡(luò)閱讀、手機閱讀的流行,都給傳統(tǒng)的出版方式與閱讀方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人們的思想觀念發(fā)生了變化:實用主義盛行。
但是,中外之間還有一些不同點,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外經(jīng)典閱讀受到?jīng)_擊的程度不同。相對來說,中國當代閱讀受到的沖擊無疑更為嚴重。即大家對于閱讀沒有什么太大的興趣;人們幾乎不去讀經(jīng)典,不去讀古典,而相比之下,快餐文化盛行。
第二,網(wǎng)絡(luò)閱讀、電子圖書對中外都有影響,但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它改變的是閱讀方式還是閱讀內(nèi)容。目前在中國,它更多的是改變了閱讀內(nèi)容,即不再是經(jīng)典閱讀;而在發(fā)達國家,更多改變的是一種閱讀的方式。
第三,受到實用主義的沖擊程度不同,導致的結(jié)果也有所不同。在中國,情形似乎要更嚴重一些。兩種傾向值得我們重視。一是目前的閱讀趣味有低俗化的傾向,一是作家的寫作也有淺薄化的傾向。這兩種傾向所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普遍地缺乏思想深度,甚至有可能造成全社會文化水平的下降。
第四,比較中外的閱讀,還有一種差別值得重視。在中國,我們太多的人都會講沒有時間去閱讀。但是在發(fā)達國家,比如美國,閱讀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在美國的很多地方,比如說在地鐵上、飛機上、火車上,美國人都會沉浸在自己的書籍閱讀之中。需要特別提醒的是,我們中國人也有在上述地方閱讀的習慣,但大多數(shù)人似乎更喜歡閱讀雜志。
從經(jīng)典閱讀,到人文學科,再到人文教育
中外都在經(jīng)歷的一個共同點是實用主義盛行,這對經(jīng)典閱讀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閱讀經(jīng)典究竟有用還是沒用?讀它到底有什么價值?
通常意義上的經(jīng)典閱讀,讀到的大都是文學、哲學、歷史及藝術(shù)作品等。這樣一類經(jīng)典作品,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等教育里人文學科的內(nèi)容,而人文學科是與人文教育緊密相連的。
西方現(xiàn)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的功能,除了早期的宗教因素以外,最終就源起于人文學科的功能。美國的教育思想源于歐洲,其高等教育最初的發(fā)展同樣注重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學、哲學、歷史、藝術(shù)等等。這樣一種教育功能,在美國的大學里面占據(jù)著上風,或者說占據(jù)著絕對的上風。
在美國,由于實用主義的沖擊,人們對高等教育或者說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當中的人文學科同樣提出了質(zhì)疑,問題直指“人文學科有用還是沒有用”。
一場“人文學科有用與否”的學術(shù)爭論
2008年至今,美國學術(shù)界和高等教育界一直在進行著一場有關(guān)“人文學科有用與否”的學術(shù)爭論。
這場爭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斯坦利·費什教授。費什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在美國有非常崇高的學術(shù)地位。2008年1月6日,費什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這篇文章針對一份報告和一本新書,談了人文學科的作用與價值。
他所針對的報告,是當時紐約州高等教育委員會的一個報告。這份報告在論述高等教育的時候,幾乎沒有提到藝術(shù)與人文學科。在隨后人們對這個報告的眾多評論當中,大家?guī)缀跤幸粋€一致的觀點:藝術(shù)與人文學科是最不容易得到資助的。
費什針對的一本書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科隆曼教授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終結(jié)——為什么我們的高校放棄了人生的意義》。在這本書里,科隆曼教授提出了這么幾個主要觀點:第一,“過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養(yǎng)人的品性的地方,是培養(yǎng)智識與道德修養(yǎng)習慣的地方,這兩者的目的是要使一個人能夠過上最好的人生,但現(xiàn)在卻不一樣了,科學、技術(shù)以及各種名利已經(jīng)成為了種種的障礙,妨礙人們?nèi)ミ^一種有意義的人生”;第二,“如果我們還想要在一個龐大但卻空洞無力的時代去尋找意義,那我們就必須轉(zhuǎn)向人文學科,因為惟有人文學科才能幫我們?nèi)ソ鉀Q生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第三,“人文學科總是能夠呈現(xiàn)給學生一系列的文本,他們以無與倫比的力量針對上述問題提供了諸多強有力的答案”,在這樣的專業(yè)性課程當中,“學生們會受到感動,進而去思考哪一種選擇最接近自我的一種演化過程”。總之,科隆曼說,在當代世界中,只有人文學科才能夠解決我們當下所面臨的精神危機。
“人文學科,怎么看都毫無用處”
費什教授針對紐約州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和科隆曼教授的這本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人文學科怎么看都毫無用處。”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科隆曼的觀點聽上去很棒,但我還是有疑問,人文學科是否真的就是那樣起作用的呢,人文學科真的就那么高貴嗎?”費什說:“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現(xiàn)世的人文學科的前提是,那些經(jīng)久不衰的文學、哲學和歷史作品中,所描繪的那樣一種行動與思維的例子,能夠在讀者中產(chǎn)生努力趕超的欲望。“這種觀念很好,但是卻很少有證據(jù)去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證據(jù)在反對它。”他說,“如果上述觀點屬實的話,那么在這個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為誠實的人必定是文學系與哲學系的成員,因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閱讀偉大的書籍與偉大的思想。……但是,作為一直呆在那里(長達45年)的一員,我可以告訴你們,事實并非如此。”他說,文學系與哲學系的師生,并不是學習如何變得更加善良,變得更加聰慧,他們是在學習怎樣去分析文學所達到的種種效果,如何去甄別知識的基本原理的那些不同的說法而已。
第二,科隆曼教授聲稱他所推薦的文本都與人生的意義有關(guān),但是“那些學了這些文本的人們在離開的時候,并沒有一個全新意義的人生,而不過是具有了一種新近擴充的學科知識而已”,于是,費什說,“我相信這才是事實的真相,文學系與哲學系的師生所勝任的是一門科目,而不是一個神職,拯救不拯救我們,這無關(guān)乎人文學科的意義,或者說不關(guān)人文學科的事,他們不過是給一個州或者一所大學帶來收益罷了。”費什教授還強調(diào)了人文學科或者說文學作品所帶給人的只是一份愉悅而已。
第三,如果真要追究人文學科有何用處,在費什教授看來,“唯一誠實的答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無用處”。
在這篇文章發(fā)表了7天后,2008年1月13日,費什教授又發(fā)表了長文《人文學科的用途(II)》,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他首先修正了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說他在1月6日的文章當中,所討論的是人文學科的研究,而不是人文學科的作品本身。也就是說,他并不是在說文學、哲學、歷史這些作品本身有無工具性價值的問題,而是在探討針對文學、哲學、歷史的作品所進行的學術(shù)性分析有沒有工具性價值的問題。
第四,費什繼續(xù)補充自己的觀點說,當我們在為人文學科研究的價值所辯護的時候,我們會說學習文學、哲學、歷史,能夠鍛煉人們的批評式思維(criticalthinking)的能力。對此,他提出了嚴重質(zhì)疑。
費什教授的這兩篇文章在美國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我想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他的觀點代表了現(xiàn)實生活當中特別流行的一種觀點,即實用主義的觀點,認為人文學科不能夠帶給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一種價值;第二,他本人原本從事的是人文學科研究,今天質(zhì)疑人文學科的價值,本身就具有一種反諷意味,這自然會在學術(shù)界引起巨大的影響。
斯坦福大學十大著名學者對爭論的回應(yīng)
在費什的文章發(fā)表了1年之后,即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學的校報記者約請了十位著名人文學者,對費什教授的觀點作出了正面回應(yīng)。這些專家談了怎樣去看待藝術(shù)與人文學科的未來,在21世紀,藝術(shù)與人文學科在大學的語境中該怎樣進行革新等問題。接受采訪的學者全部是英語、文學、音樂、藝術(shù)、歷史領(lǐng)域的專家。這些人文學者的回應(yīng)大都是片斷式的,但是旗幟鮮明,主要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所有學者對費什的觀點持明確的反對態(tài)度。他們都認為費什的觀點是狹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場來源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冷戰(zhàn)時期的世界觀。他們認為,費什教授是在那樣一個時代接受的教育,也是在那個時期成長起來的,所以他有這樣的一種觀點也不奇怪。其中斯坦福的音樂教授辛頓說,若是超越費什成長的那個年代的學術(shù)圈去回顧世界的時候,“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人文學科怎么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歷史”。他還特別強調(diào)說,“人文學科或許不能夠拯救我們,但若是沒有人文學科,我們一定會迷失方向。”
第二,一些學者明確指出,人文學科的確賦予人們以愉悅感,但是假如認為只有愉悅感,那么,這顯然貶低了或者是低估了人文學科的價值。斯坦福藝術(shù)創(chuàng)新研究院的沃爾夫院長說,“人文學科鼓勵各種思維方式,這不是那些硬性的規(guī)定所能界定的……它是關(guān)于世界的思維方式。而這一點,應(yīng)該置于一所一流大學的教育的中心地帶。”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班德指出,就在前不久,《紐約時報》還刊登了一組各大公司CEO的訪談,他們都表示自己管理能力的培養(yǎng),與他們長期閱讀各類書籍,包括小說與詩歌有極大的關(guān)系。班德教授說,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級官員還是當代的CEO們,沒有人會認為人文學科沒有用處。
第三,費什教授在文章當中提供了兩種可能性,就是人文學科要么是拯救我們,要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無用處。對此,有些專家就認為,這樣對立的兩分法沒有必要,同時也不夠聰慧。英語教授朗斯福德認為,“人文學科既‘有益于自身’,也能給‘世界上帶來效果’,比如費什本人就談到了人文學科的效果之一——來自出眾之美的那份完全的愉悅感”。除此之外,“人文學科還有其他功用:通過人文學科,學生會更加適應(yīng)復雜多元的世界,從容應(yīng)對多元的主張;分析會漸趨縝密精確;交流方式也會更加文雅——的確,會自我增長新的知識,就像他們通過科學所學到的知識一樣。因為,對于費什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我的回答是兩者皆可。”針對人文學科能否“拯救我們”的問題,比較文學教授伯曼強調(diào)指出,人文學科無疑教給我們的是“各種能力,理解與闡釋,評價與欣賞,辯論與同意,言說與寫作,當然還有思想的愉悅”。
第四,費什的人文學科只有愉悅而沒有社會價值的說法,同樣遭到了一些學者的猛烈批評。歷史學教授、斯坦福大學亞裔美國藝術(shù)項目的創(chuàng)始主任之一張說:“人文學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們直觀所能看到與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夠直接改變世界的地步。”人文學科教授小伊拉姆批評說,費什忽略了歷史,“在各個時代、在世界的各個地方,都出現(xiàn)過禁書、焚書、小說家被捕入獄、演員被殺的情形,這都不僅僅是因為那些地區(qū)或是國家的人質(zhì)疑了某個具體作品的‘愉悅化’問題,而是因為他們恐懼藝術(shù)與文學實實在在的能動性會影響人們的頭腦,從而動搖他們的社會秩序”。
無論今天怎么樣去評價雙方的觀點,我們都必須承認,在當代的社會當中,當大學不斷地、并且還在更深層次上滑向市場的漩渦時,當有用與無用更多地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時,費什的觀點無疑代表著人們在當下語境中,對人文學科前途的一種深深的憂慮。
經(jīng)典閱讀的價值,以及哈佛大學的高等教育實踐
第一,經(jīng)典閱讀或者說人文學科與現(xiàn)實深入相聯(lián)結(jié)。在這里,舉一個例子,看看哈佛大學的高等教育實踐是怎樣的。
2009年9月3日,哈佛大學在新學期開學的時候,出臺了最新的通識教育方案。這個方案被認為是“適應(yīng)新世紀的一個嶄新的培養(yǎng)方案”。這個最新的通識教育分為八個大的門類,其中包括:美學與闡釋性理解、文化與信仰、經(jīng)驗與數(shù)學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tǒng)的科學、物質(zhì)宇宙的科學、國際社會、世界中的美國等。
這里所羅列的八大學術(shù)門類,跟技術(shù)性的課程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都是理論性的課程,其中也包括了像數(shù)學、生命科學這樣的理論性課程。哈佛大學要求學生修完八門課程才能夠畢業(yè)。哈佛通識教育改革領(lǐng)導小組的組長西蒙斯教授在強調(diào)這樣一次改革重要性的時候,單單點出了人文學科,(我認為,她仿佛是在回應(yīng)人文學科是否有用的這樣一場爭論)并明確提出,“人文教育并非與現(xiàn)實生活相脫節(jié),而是通向現(xiàn)實生活的一座橋梁”。
第二,經(jīng)典閱讀,或者人文學科,關(guān)乎人的教育。美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視通識教育。所謂通識教育通常就是人文學科的代名詞。在美國,人文教育歷史悠久,主要學習文學、外語、歷史、哲學、數(shù)學與科學等等。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在過去的七十年當中歷經(jīng)三次變化,這告訴我們,人文學科、人文教育至關(guān)重要。
第三,經(jīng)典閱讀,或者人文學科,關(guān)乎大學的本質(zhì)。福斯特校長說,“一所大學關(guān)乎學問,影響終身的學問,將傳承千年的學問,創(chuàng)造未來的學問。……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而看的方法必須也應(yīng)該與大眾當下所關(guān)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對應(yīng)”。那么,我們今天的大學,能不能跟當下的社會相對應(yīng)呢?我們的大學歷來講的培養(yǎng)目標,就是要培養(yǎng)對社會有用的人才。為社會培養(yǎng)人才沒有錯,也是大學的功能之一,但不要忘記了,大學還應(yīng)該有一種引領(lǐng)社會的作用,否則它只是一所職業(yè)學院。福斯特校長講,“就其本質(zhì)而言,大學培育的是一種變化的文化,甚至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文化,這是大學為未來承擔責任的核心。”這個世界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學習一種應(yīng)對、學習一種變化、學習一種思維能力,這才是大學所能夠賦予你的最重要的價值。
福斯特校長說,“教育、研究、教學常常都是有關(guān)變化的——當人們學習時,他改變了個人;當我們的疑問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時,它改變了世界;當我們的知識應(yīng)用到政策之中時,它改變了社會。”福斯特校長的話實際上在告訴我們:什么是大學的使命。首先,要培養(yǎng)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使之具有一種批評性的思維能力。其次,大學的使命是要引領(lǐng)和改變社會,而不是被社會所改變。“是大學改變社會,而不是社會改變大學”。
第四,經(jīng)典閱讀,或者人文學科,關(guān)乎從有用之中發(fā)現(xiàn)高貴與美。在當代高等教育中,主要有兩種培養(yǎng)方式:第一種就是非常具體的以就業(yè)為導向的高等教育,第二種就是沒有什么明確的目標的通才教育。中國現(xiàn)在最提倡的一個口號是,要以就業(yè)為導向,推動高等教育改革。但是,當我們在理性思考如何看待新一輪高等教育改革的時候,把所有的大學都定位在以就業(yè)為導向是錯誤的,長此以往,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一定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回答“為什么要學習人文學科”時說了三句話,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思考:第一句話,“大學所授予的學位是某一特定領(lǐng)域的,但生活卻是不分專業(yè)的”。第二句話,“無論我們的社會多么發(fā)達,我們都必須去反省人生、甄別善惡、區(qū)別正義與非正義,從有用之中辨別出高貴與美”。第三句話,“人文教育為學生未來迎接現(xiàn)實生活的挑戰(zhàn)所做的準備,是那些職業(yè)學院常常無法提供的”。
經(jīng)典閱讀,通向現(xiàn)實生活的一座橋梁
首先,閱讀經(jīng)典有現(xiàn)實意義,它也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我們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們怎么樣去應(yīng)對未來的變化?我們怎么樣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其次,閱讀經(jīng)典可以引發(fā)寧靜的感悟和睿智的思考。再次,科學技術(shù)勇往直前,而由經(jīng)典閱讀形成的人文教育又負有要努力把握前進方向的責任。
“經(jīng)典閱讀:讀,還是不讀?”我的回答是:讀。因為它與人文學科有關(guān),而人文學科關(guān)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則關(guān)乎人的教育。它們“有助于我們反省人生,甄別善惡,區(qū)別正義與非正義,從有用之中辨別出高貴與美”。同樣,它們關(guān)乎大學的本質(zhì),“人文教育為學生未來迎接現(xiàn)實生活的挑戰(zhàn)所做的準備,是那些職業(yè)學院常常無法提供的”。如果上述這些觀點您都沒有記住,我希望您能記住一句話,那就是經(jīng)典閱讀“并非與現(xiàn)實生活相脫節(jié),而是通向現(xiàn)實生活的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