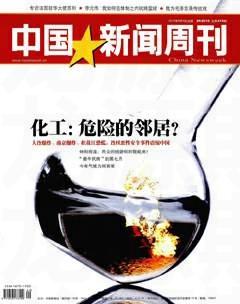“最牛民房”的黑七月
周華蕾


以往在北山門口村,提起村西那棟地標性的23層大樓,大伙總是樂呵呵地帶著一股翻身農奴的自豪勁兒,給好奇的路人義務導游兼解說。
可現在不成了。自打落下“違章建筑”的名聲,它那在民房堆里顯得不怎么和諧的“參天”海拔,便成為難堪的標記。村里人甚至避諱提起它,跟老鼠躲貓一樣。空氣微微發脹的下午,偶爾一個腆肚子的老漢路過,嘆口氣,“這樓把人害苦嘍!”
2010年7月23日,西安市雁塔區北山門口村。
村子位于南三環內,城市中軸線的西側,離市區核心的鐘樓不到9公里。商人們更愿意把這里叫做“CBD輻射區”。
村里的路一如既往地狹長坑洼。親嘴樓、牽手樓一眼望不到頭,“招待所”“出租”和“計生用品”的招牌層層疊疊,沒生意的理發店里Lady GaGa的英文歌震天地響。這是古都西安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的初級階段里,毫不稀奇的城中村一景。
唯一具特色的,是這棟無奈地矗在村中央的、已經火遍中國論壇的“最牛民房”。它像植物優先生長的頂芽,遠遠地把同伴們拋在腳下。左側是一家百姓川菜,右側是一家“云佳超市”,它竭盡所能地撐出更大的面積,那暗紅色的磚面和鋁合金窗戶,幾乎跟右側的居民樓面貼面了。
連著下了好幾天的雨,“雁塔區建設和住房保障部”7月13日貼的封條,和樓前等待封頂用的兩堆泥沙,都泡在湯里。
黑七月。高樓眼看著要竣工,被封了,蓋房子的老胡失蹤了,一切關于電梯房的遐想和喬遷之喜亦都中止。
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老胡本名胡夢如,55歲光景,因為說話直,威信高,現任北山門口行政村11小組的組長。在村委會入口處的宣傳欄里,鼻子旁邊有一顆肉痣的老胡排在“先進黨員”的第一位。
北山門口村歷史悠長。據村史載,該村因毗鄰唐都外郭城的安化門得名,原為“北三門”。它由兩個自然村組成,以南北貫穿村莊的電子正街為界,村東叫北山門口村,村西是唐家圍墻堡子,統一歸屬北山門口行政村。
胡夢如住在唐家圍墻堡子。在這個以唐、桑姓傳承的自然村落里,胡姓人是舊社會逃難來的。
解放初期的北山門口村一千來人,2700畝地。然而人均兩畝地的日子,早就像童年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北山門口村,已然陷落在城市的大包圍中,進入了寸土寸金的新世紀。
城市化颶風說刮就刮起來了。那些祖祖輩輩種滿西紅柿、黃瓜和玉米的莊稼地,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便大畝大畝地割讓出去。先是石油學院,然后是山溝里搬出來的軍工企業……
十幾家廠礦企業入駐北山門口村,每畝地約1萬2的補償,算下來每家能拿到八九萬,在赤貧的1980年代,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錢的村民,心頭歡喜。
北山門口村的所在地是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和走文化路線的曲江不同,高新區是一個政府沒有投入開發資金的國家級新區,當年靠著10萬元的資本起家,最大的優勢就是土地。
比起望天吃飯,賣地建工廠的思路更快地讓高新區的GDP騰飛了起來。
而東一片西一塊的征地,也讓北山門口村于1990年代正式成為一個只剩下約500畝宅基地的光禿禿的村莊。
等到通通失去了,村民們才慢慢意識到土地的緊要。最頭疼的,就是結婚生子分宅基地的事。按村里習俗,一旦成家,就得向村里乃至區里申請宅基地,可這些年土地數量不變,北山門口村的戶籍人口卻翻了一倍,達到了3567人。
申請宅基地的村民與日俱增。有的村民小組已經10年沒有宅基地可分了。有人結婚的時候就寫申請,娃都會打醬油了,地也沒批下來。一大家子人混住一起,兄弟妯娌間的齟齬也多起來。
老胡所在的11組算運氣好的,挨到2008年,終于有5戶的宅基地批下來了,村西那塊7分地,自行協商分配。可怎么分配,也到不了每戶2分地的標準。再說了,還有好幾戶等著批宅基地,這已經是11組最后的7分地了。
2008年的西安早就高樓林立了,只有城中村還矮著。盡管如此,它還是在以緩慢的速度生長著。農村人的腦海里有兩個根深蒂固的概念:種地和蓋房子。地換了錢,錢沒地兒使,于是蓋房子。土房推了建瓦房,瓦房改磚混,建了磚混就小康了。一層修了建兩層,兩層搭三層,反正就跟俄羅斯方塊一樣往上砌。
即便西安市有文在先——按2006年出臺的《西安市城中村村民房屋建設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列入城中村改造目錄的村莊,不再審批宅基地,不得新建、改建和擴建房屋,且確需翻建的房屋,“翻建房屋不得超過二層”——但這些年,不管是即將改造的城中村,還是改造遙遙無期的城中村,最積極主動的事情無非還是蓋房子。西安的城中村高度普遍在五六層,漸漸的有了八九層,在“最牛民房”問世以前,西安的最高紀錄由糜家橋村13層的電梯民房保持著。
在尚未進入城中村改造序列的北山門口村,11組的村民們很快從“全中國向上看”的趨勢里得到了啟發。“這世界的理就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一個上了年紀的村民這樣想。
老胡試探著和村支書曹松林商量,想把樓蓋高點,把大伙的問題一并解決。曹松林點頭了,提的要求是,保證房屋質量。
大伙湊了錢,請了單位設計圖紙,挖了個好深的地基大坑,這樓就在眾村民的目瞪口呆中,紅紅火火蓋起來了——一蓋就是23層,單價2600到3000元不等。據村支書曹松林表示,這套房只賣給村里人。老胡要的是頂層,躍層式結構。
大家都評價老胡,“看得長遠”。
老胡的長遠不止于此,那兩年西安的地價早就今非昔比了。距北山門口村不到1公里的太白南路,于2006年出現了“地王”,每畝的拍賣價格是159萬元,其時周邊村民的土地轉讓價格只有十幾萬每畝。而今,地王里長出的樓盤,每平方米的均價為6400元。
好人“嚇呱呱了”
北山門口村從來都走在時代的前頭。當年安裝閉路監控,這是全西安最早的地方之一,后來村民使用電子門鎖,也是最早的。過去,北山門口村都以正面示人,可這回,它成了負面新聞。
村里人至今認為,如果不是記者曝光,這好端端的樓不會黃掉。
大樓自2008年動工,修修停停建了兩年多,中途有過規劃部門的人來查土地證,但從來安然無事。直到2010年7月11日,這棟高層民房猝然登上當地報紙的頭版頭條。老胡,被詡為“最牛民房的締造者”,自此被聚焦。
兩天后,高樓就被查封了,兩個入口處落上了鐵鎖。本來,這個月底,村民們該分房子搬新家了。那五戶原本分到宅基地的村民急燎燎地追問老胡,房子怎么辦。
打那后,村里人都說,老胡被“嚇呱呱了”(注:嚇傻了)。
村支書曹松林找到老胡,說,你要把資金來源、分配情況、招標設計圖準備好,交給相關部門調查。提到高樓老胡就一聲不吭。然后前言不搭后語地對曹說,你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在黨內表現咋樣,你是清楚的。
再之后,老胡就失蹤了。手機關機,家里沒人。原本他每天早上在村西的丁字路口買兩根玉米,現在卻“好長時間不見人咧。”賣玉米的外鄉大嬸說。
那些投了資的村民們,也像受到驚嚇的兔子躲起來,他們會對上門的陌生房客抱怨,投了幾十萬的房子眼看就“打了水漂”,但面對記者絕口不提一個字,只說,“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仿佛他們所說的一切都將成為壓垮高樓的最后一根稻草。這些年,在大拆大建的西安,遠的文物陳樹藩故居被強拆不說,近的三爻村堵路、姜村上訪,他們見多了。
只有外鄉人的口氣稍微松動些。那些扛著鍋碗瓢盆、拖兒帶女的農村小生意人,那些染黃毛打耳洞的新生代農民工,從更遠的農村,陸續來到這更靠近城市的農村,像螞蟻一樣填充到罅隙的空房子里。
北山門口村迅速膨脹。而今,外來人口的比例是本地村民的22倍,這430畝見縫插針的建筑里,壅塞著7萬余人。建筑工地的廢棄品和垃圾隨處堆放,以至村民們用詛咒般的標語整治村容村貌,比如“不自覺雜種斷自(子)絕后”。
有的外鄉人會逮著記者說個沒完。他們說這些天來了好多記者,對著大樓咔咔拍個不停,又說老胡天天蹲守在工地上,是好人辦好事,結果辦砸了。老街上,一個來自陜南商洛的菜農,對高樓被封似乎見怪不怪。她說,他們老家村里,房子總是蓋好了才“違章”。
法理之外,《中國新聞周刊》接觸到的二十幾位村民和外鄉人,無一例外地對高樓表示理解——
“兩層以上的樓房就算違章,那西安的城中村都得拆!”
“村民不自己蓋,啥時能住上兩室一廳?”
“23層算個啥,華西村還蓋100多層咧!”
不蓋房子,拿啥致富?
事到如今,23層的最牛民房,連同北山門口村都在忐忑等待著。正如北山門口村村委會的黑板報所寫,《北山門口村距城中村改造究竟有多遠》,文后是十七個問號。
2002年以來,西安懷著再造唐都的夢想,要打造“九宮格局”的全新面貌。六城區共有城中村286個。北山門口村落在西南隅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里。
據西安城中村改造工作領導小組2006年表態,城中村改造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期行動”,將在8到10年完成。
對于前途未卜的北山門口村,這些漫長的年月意味著,改造要么是場持久戰,要么是場閃電戰,但誰都說不清哪天“拆”字當頭。比如舉辦一次全城動員的大盛會,這一攬子城市問題也就跟著解決了。這兩年,西安要搞世界園博會,村民們都傳著要“拆”,但最終也沒等來聲響。
北山門口村村委最愁的是,在等待改造的日子里,拿什么來壯大村集體經濟,讓村民發家致富?
這里有句土話,“好出門不如哈在家”。村民鮮有外出務工。
90年代那陣,地剛被征,村里大量閑散人員沒事干,天天打麻將,村委跟征地單位辦起了“雁山天線廠”“雁山電子元件廠”等一系列村辦企業,解決了600余人次的就業問題,一時成為市里的“明星村”。可到2000年前后,大環境開始走下坡路,村辦企業相繼破產。
現今,“可以說,這里99%的農民都靠房租活。”一位村干部表示。1289戶人家,每年收入房租1個億多。
要增加村民收入,立竿見影的做法就是蓋房子。這算是踩紅線的事情。但在一個尚未進入改造序列的城中村,建不建房子,能建多高的房子,仍屬于管理的盲區。
蓋房子被認為是不會賠本的營生。等待拆遷的日子里,村民可以把房子出租,把土地效益最大化。待到拆遷來臨,也還有兜底的補償條款。誰知道,蓋5樓沒事,蓋8樓也沒事,蓋23層,這“出頭”的樓就被封了呢?
對于這棟既成事實的高樓,可茲參考的命運無非二種:一、像北京通州郊區的農業生態別墅,一聲令下即被鏟除;二、像天津的宅基地換房,搞農村城市化,自上而下搞“農地流轉”。
目前,西安市的相關部門仍在研究對策。
消失后的某個夜晚,老胡用一個陌生的座機給曹松林打來電話。
他說他在秦嶺的農家樂里,喝了一斤白酒,心頭憋屈,說,本來想做好事,給大家謀福利,沒想到辦成這樣了。
曹松林說,回來吧,該面對的遲早要面對。
但老胡至今沒有回來。
曹松林記得那時候醉醺醺的老胡說,哪天我把記者叫來,把情況一說,從23樓頂上一跳,這事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