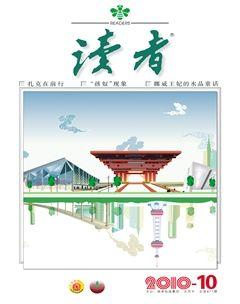為了夢想,含淚活著
蕭東兮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點,烏黑的天空飄著冷冷的細雨。日本北海道最東部的小鎮阿寒鎮,一群中國學生在夜色的掩護下疾步穿行。
凌晨3點,他們穿過了小鎮,穿過了機場。被淋濕的襯衫皺巴巴地貼在身上。他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握著一根木棍,那是準備用來與隨時可能撲上來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幾小時的徒步疾走,讓他們的小腿肚酸腫發脹。
漸漸地,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霧。前方就是釧路市,逃亡者帶著一身疲憊,悄悄在釧路站后面一間無人的小棚里換上了干衣服。當開往札幌的電車還有一分鐘就要發車時,他們奔進車站,幾乎是在關門的一剎那跳進了車廂。隨著電車發動,他們的“逃亡”成功了。
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鎮這群中國學生的此次夜行,后來成為震驚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時年35歲。“逃亡”的半年前,在上海,這名青年花了5角錢從別人那里買了一份飛鳥學院阿寒鎮分校的資料,并舉債4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萬元),將妻女留在上海,獨自一人來到了日本。
早年由于“下鄉”而錯過讀書機會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發點。
按照設想,念完阿寒鎮的語言學校后,他會考入日本的大學,日后再將妻女都接來日本一起生活。而到了阿寒鎮才知道,這個“蜷縮”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鎮人口極其稀少,幾乎全是老人和兒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這批學生,是為了解決該地區人口過少的問題。
對中國學生來說,他們本打算邊學習,邊打工還債,可學校一帶連便利店都沒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還債?
飛鳥學院阿寒鎮分校首批的56名學生,半年后只剩下7個人。
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當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東京,一待就是8年。他的簽證很快過了期,他淪為在日非法滯留人員。
在東京打工還債的這幾年里,他逐漸確立了自己的新目標:努力賺錢,將來把女兒送去國外一流的大學深造——把自己無法實現的求學夢,寄托到女兒的身上。
這是東京豐島區一棟30年前修建的木板樓。丁尚彪做飯、洗澡、如廁、睡覺都在樓上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內。洗澡的設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個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灑就是洗碗用的熱水噴頭。洗澡時,人必須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會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來,從洗碗池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剛跑來的時候,家里人想不通,總猜測我在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實我就是想為女兒拼命賺些錢。”望著墻上女兒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離開上海時,女兒還只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畢業班里做著高考前的最后沖刺。
“文革”風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安排到當時中國最窮的地方——安徽五河縣。他每天都要干十幾個小時的活。就是在那種忍受著饑渴、令人痛苦絕望的日子里,丁尚彪邂逅了他的妻子陳忻星。
陳忻星和丁尚彪一樣,也是從上海到五河縣的。在那個沒有電燈、煤氣,連自來水都沒有的環境中,他們兩人共同許下“要同甘共苦,協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不久,“文革”結束,他們回到了上海,隨后他們的女兒出生。
丁尚彪上海的家,在一棟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樓。一樓的公用廚房昏暗、狹小,陳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飯,再端到樓上房間和女兒一起吃。晚飯后,女兒在角落的書桌邊做功課,陳忻星就在一邊讀報。兩人共睡一張床。為了貯備留學費用,母女倆相依為命,過著簡樸的生活。
1997年夏天,女兒丁晽收到了紐約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女兒在上海的最后一晚,陳忻星和女兒并排坐在沙發上,相顧無語。突然陳忻星好像想起了什么,叮嚀道:“以后你要自己一個人去闖了,我們都老了。”
8年前,同樣在虹橋機場,陳忻星送別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團聚;此地此刻,她將送別女兒,不知何日再見。
兩個人的東京
丁晽乘坐的飛機在東京中轉,再飛往紐約,她有24小時的停留時間。從她小學時就分別的父親,8年后,終于能在東京與她再見面。
兩人約在日暮里站,列車還沒停穩,丁晽就興奮地喊道:“我看見我爸了!”丁尚彪也立刻迎了上來,從女兒的手中接過了行李箱。沒有擁抱,就像一次平常的回家。
列車里,父親調侃著女兒:“該減肥啦!”“還割了雙眼皮嘛!”丁晽嬌嗔地答道:“不要和別人說嘛。”
吃完飯,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丁尚彪開口:“當年臨走的時候,隔著機場的玻璃窗,你在哭,我也在哭,還記得嗎?”
“記得一點。”
“你那時候那么小,就是蒙著臉哭。”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第二天,丁尚彪只能把女兒送到機場的前一站——由于是非法滯留,他無法進入需要出示身份證件的機場。
列車在站臺上停靠了足有半分鐘,丁晽捂著臉,父女倆隔著一扇窗,就像當年丁尚彪離開上海的時候一樣。
“見到爸爸的時候,我本以為8年了,多少會有點生疏,但不管怎么樣,爸爸還是爸爸。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想表現得開心。不然我難過,他會比我更難過的。”丁晽說。
18歲,丁晽獨自去紐約求學,父親繼續留在東京打拼。在上海,單身一人的陳忻星也在拼命工作著。陳忻星在一家建立已久的制衣廠工作,入廠至今已有20個年頭。
為了去探望女兒,她一直在申請赴美的簽證。從丁晽出國那年算起,連續申請了5年11次,可惜,星條旗卻不懂母親的心思。
2002年春,陳忻星的第12次申請獲批了。在她的心中,還有一個期盼已久的愿望——在飛往紐約的途中,利用在東京中轉的時間(最長可停留72個小時)見一見丈夫,這是她和丈夫見面的難得機會。
臨行前一天,她特地去附近的一家裁縫店,用外甥送的料子做了件衣服,還燙了個頭。而此時在東京,丁尚彪也忙著準備迎接妻子的到來。
丁尚彪翻出了一個大紅色的枕套。“這是我們結婚時用的枕套。25年前,她親手縫的。我帶了一個過來,她留了一個。”他憨憨地笑。丁尚彪的門牙已經稀疏,裝了假牙。
同樣是在日暮里站,同樣是未及列車停穩,陳忻星就認出了13年未見的丈夫的身影,同樣沒有擁抱……丁尚彪接過妻子的旅行箱,等車的間隙,他默默地從背后注視這個女人良久。
這幾年,丁尚彪年齡大了,再加上日本經濟不景氣,他只能去掃掃地,洗洗碗,一周工作7天,全年無休。看著丈夫在廚房做菜的背影,看著墻上女兒的照片和自己親手縫制的枕套,陳忻星欣慰的笑容中充滿了憐惜。
第二天,他們兩個人一起去旅游。丁尚彪挽著妻子拍合影,帶妻子嘗東京的小吃,賞櫻花,看夜景,一同燒香祈福。
這是兩個人的東京。72個小時,3天的中轉時間,終于,只剩下默然。
5年前的夏天,也是在開往成田機場的這趟列車里,丁尚彪與女兒分別;此時此刻,再與妻子分別。
仿佛一切在重演,直到列車開出站臺,陳忻星才頻頻回望。窗外的景色飛快掠過,在這個陌生的國家,丈夫奮斗了13年!
2004年6月,丁尚彪決定回國了。
回國前,丁尚彪決定再去一次阿寒鎮。15年前,也正值這個季節,他的日本之旅就是從那里開始的。
看著如今已經廢棄的教學樓、堆在墻角的課本,丁尚彪不禁有些悲傷。
“雖然當時的債務很沉重,但是經過了15年,還是多虧了這個地方。15年前,我走到這里的時候想,人生也許是悲哀的,(但現在看來)人生是絕不可以放棄的。”
如今,丁尚彪的女兒已在美國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她將父母接到了底特律一同生活。20年,曾經天各一方的一家三口,終于團聚到了一起。
(龍巖摘自《看天下》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