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小說敘事策略的新變
馬偉業
如果有人撰寫中國新式小說的藝術演進史,當他寫到當代小說尤其是新時期小說的藝術新變時,他肯定會興奮不已。因為他會發現,中國新式小說的敘事藝術在進入當代文學史階段尤其是新時期以后竟然新法迭出,花樣翻新。諸如意識流、黑色幽默、象征、復調、魔幻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等等新的敘事藝術都紛至沓來,爭奇斗妍,使發端于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新式小說在藝術上不再像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階段那樣單一甚至單調,而是變得豐富多樣起來。而在這新出現的豐富多姿的敘事藝術中,有幾種方法不曾以自身的招搖引起過人們的特殊注意,而是以更潛隱更踏實的姿態默默運行著,那就是設謎人物、孿生故事和反觀視角。它們雖未受到過太多的熱捧和經歷過太多的繁華,但卻為中國當代小說藝術留下了全新的印記。
一、設謎人物
假如我們從藝術演進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新式小說,就會看到,當中國新式小說進入當代文學史階段以后,有一種此前從未出現過的嶄新藝術方法突然出現了,那就是有些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故意設謎,他們的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都呈現出明顯的謎語性特征。他們在進行構思時,既設計一個具體的人,又設計一個或多個與之相似的人,讓作品中的敘事者在辨認時發生誤會,使他覺得此人既像某個人,又不是某個人;雖然不是某個人,但在整個精神世界和靈魂深處又與某個人如出一轍。有的作品最后揭出了謎底,確認作品中的此人不是某個人,而是另一個人;有的作品則最后也沒有揭破謎底,不知道此人是否確系某人。在這些作品中,那個具體的人與他的相似者之間都存在著一種似是而非的謎語關系。這種故意設謎的藝術最初出現在“十七年”間,它的始作俑者似乎是著名作家茹志鵑。她在《高高的白楊樹》中,敘述一個戰爭年代的女護理員“我”在建國后去尋找當年的同事、大姐張愛珍,“我”到大姐的家鄉張家沖尋找她,但找到的卻不是當年的大姐張愛珍,而是一個養兔姑娘張愛珍,同時還聽說附近有個種麥能手也叫張愛珍。養兔姑娘雖然不是當年在戰火中沖殺的大姐,但整個精神世界卻與當年的大姐一脈相承。“我”在這里沒有找到當年的大姐,卻從夏書記那里聽說了在過去年代一個女孩小鳳兒的往事,“我”突然覺得小鳳兒就是離家出走參加革命隊伍之前的大姐張愛珍,但夏書記卻說不是。這樣,作品在大姐張愛珍與養兔姑娘張愛珍之間,在大姐與小鳳兒之間就構成了一種謎語式關系。此后這種人物設謎的方法也被其他作家所運用。當年曾經一度崇拜并有意學習茹志鵑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短暫復出中寫下的《眼睛》,就運用了這一方法。小說寫一個大學畢業生蘇淼如在作鄉村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時,在秋收時節,遇到一個女孩兒來借《紅巖》,并說她們的團支部準備組織團員學習《紅巖》以配合秋收。這個女孩兒的一對眼睛引起了蘇淼如的特殊注意,他覺得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林燕子,因為她的“雪亮的、充滿熱情的、望得很遠又很堅定的眼睛”跟林燕子的眼睛一模一樣。他深為自己在圖書館已無此書可借的情況下沒將手中留給戀人的這本書借給她而遺憾。后來有人對他說,那個姑娘不是林燕子,而是另一個農村姑娘。即使如此,蘇淼如仍然覺得她同樣令人敬重。小說同樣在農村姑娘與林燕子之間制造了謎語。其實,在“十七年”間,不僅小說家在運用這種設謎的藝術,甚至電影藝術家也在運用這種設謎藝術,著名影片《五朵金花》就是明證。在“文革”后期出現的某些敘事作品中,作者們仍然沿用著這種方法,《烏蘭其其格》、《雪蓮》等等都是如此。進入新時期以后,這種設謎藝術雖然未受到過更多作家的垂青,但仍然有人在沿用它,著名作家賈平凹的小說《二月杏》就是用這種方法寫成的。小說敘述了 “文革”開始時中學生大亮為了能加入 “造反隊”,便狠心地拋棄了與他相愛著的出身富農家庭的女同學二月杏,給這個少女造成了深重的心靈創傷。15年后,已經成了地質隊員的大亮在一個鎮子里意外地遇到一位與二月杏長得一模一樣的姑娘,他覺得她就是當年的二月杏,但她卻矢口否認。她說自己不是他說的那個二月杏,但大亮卻發現她的身世經歷和心靈傷痛與當年的二月杏十分相像。直至作品結束,讀者也未最后弄清她究竟是不是大亮當年的那位女同學二月杏。這樣,在兩個姑娘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謎語關系,而且謎底始終未被揭破。可以說,故意在人物形象上設謎,是當代某些作家曾經熱衷的藝術方法,也是中國新式小說在進入當代文學史階段后,在藝術上出現的一種引人注目的新方法。那么,這種全新的敘事方法為這些小說帶來了怎樣的藝術效果呢?
這種新的敘事方法為作品帶來了強烈的隱喻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作家在創作時都有一個明顯的社會目的,那就是或者為了歌頌,如茹志鵑、王蒙的作品,或者為了批判,如賈平凹的作品,但不論是歌頌還是批判,作家都想強化他所寫的人物和生活的普遍性,以此向世人證明,他寫的人和事絕不是個別的單獨的存在,而是涉及很多人的廣泛的普遍的存在,以此增強歌頌或批判的力量。為了表明他們所寫的人和事具有普遍性,他們不僅寫某個人,而且還寫了一個或幾個與之相似的人,使彼此之間形成一種謎語關系,這樣作品中的人就不僅是某個人,而且也是某類人,非常便利地向讀者證明這種人和事確實普遍存在著。這樣,出現在他們作品中的人,無疑具備了一種隱喻性。茹志鵑《高高的白楊樹》是歌頌社會主義的創造者和建設者的,她既寫了戰爭年代的張愛珍,又寫了建設年代的養兔姑娘張愛珍、種麥能手張愛珍,讓三個女性名字相同,以此在是否同為一人的問題上出現謎團,于是張愛珍既是具體的個人,同時也成了同類人的代名詞,是一個隱喻。作家通過這個人物仿佛在告訴人們,從開創新中國到建設新中國,像張愛珍這樣的奉獻者何其多也!在此之外,作家又設置了張愛珍與小鳳兒的謎語關系,進一步揭示了這類人成長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使作品所寫的人和事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增強了作品的歌頌力量。王蒙的《眼睛》也是如此。作家意在歌頌新時代新生活中涌現出來的社會主義新人,他既寫了模范人物林燕子,又寫了一位與之相似的農村姑娘,在這位農村姑娘與林燕子是否同屬一人的問題上制造謎團。在兩者的極其相像中,表明整個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有林燕子式的先進人物,以此強調作品所寫的人與事的廣泛性。于是,在這里,林燕子就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類人,她也成了一種隱喻。賈平凹的《二月杏》的創作意圖在于批判“文革”給廣大民眾造成的災難,進而控訴“文革”的罪行。他既寫了心靈受傷的大亮的同學二月杏,又寫了一個與她相似的姑娘。兩個二月杏構成了謎語關系。她們的相像甚或相同向世人表明,當年大亮的二月杏所遭受的不幸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從而加深了對“文革”批判的力度。這樣,二月杏也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類人,她也成了隱喻。由此可見,這種設謎人物確實都有極強的隱喻性。
這種人物設謎的藝術方法也為小說增添了趣味性。趣味性對于一篇(部)小說來說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小說畢竟不是必讀文件,不是操作須知,不是農藥說明”,“人們讀它首先是因為它有趣”。那些有經驗的作家總是設法“把小說寫得更有趣”(王蒙:《漫話小說》)。而人物設謎的方法無疑增強了小說的趣味性。因為它們都存在著 “差頭”,都出現了“誤會”。而誤會在生活中是趣味生成的重要條件,當一個人誤把張三當作李四的時候,其結果必定是有趣的甚至是可笑的。《高高的白楊樹》中的“我”來找大姐張愛珍,打聽到了一個叫張愛珍的人,“我”便以為真的找到了要找的大姐,待到見面,卻發現她是另一個人,一個與大姐張愛珍年齡差別很大的姑娘。這個誤會為作品平添了幾分趣味。《眼睛》中的蘇淼如把一位農村姑娘當成了著名人物林燕子,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還特意手捧《中國婦女》這本雜志,認真盯著上面刊印的林燕子的照片,反復端詳辨認,越看越像,于是認定那個借書姑娘就“是她”!然而后來別人卻告訴他那位姑娘真的不是林燕子,他誤會了。他誤會了,作品的趣味也就出現了。當年著名評論家黃秋耘先生在讀過這篇小說后特別指出,“最后證明女主人公并不是林燕子,這使小說不落窠臼,頗有意趣”(王蒙:《半生多事》)。這位著名批評家當年的“接受”事實也證明著這一點。《二月杏》中的誤會同樣為作品增添了情趣。大亮把在一個小鎮上見到的姑娘當成了他當年的戀人二月杏,但這個姑娘卻說自己不是那個二月杏,這一“誤會”同樣讓人感到妙趣橫生。正是這些“誤會”使作品不斷節外生枝,趣味頻仍,在它們所寫的生活所表達的思想早已隨同那頁歷史被翻過去的今天,讀起來仍然感到興味盎然。可以設想,假若不是如此,作家當初在創作時不做這樣的設計,讓尋找張愛珍的人隨后真的找到了張愛珍,讓被認定為林燕子的姑娘后來真的成了林燕子,讓遠在千里之外的小鎮上出現的姑娘后來真的成了大亮的二月杏,其結果也許會有另一種風云際會,演繹出另一種人間活劇,而且這樣的作品也不無新意,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創造出這種情趣美!
這種人物設謎的方法,還為作品創造了一種朦朧美。朦朧美同樣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美感類型,而且是一種很高的美的境界,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都有意追求這種境界。人物設謎的方法無疑為作品造成了朦朧美。因為它寫的幾個相似人物之間那種似是而非、似真實假的關系,本身就顯得云里霧里,迷離恍惚。在當年的大姐張愛珍與養兔姑娘張愛珍,種麥能手張愛珍的似而不是的關系中,就有一種迷蒙感。特別是在大姐張愛珍與小鳳兒的關系上更有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兩者是否同為一人始終是個未解之謎,謎的存在使作品籠罩著一層迷蒙的輕紗。林燕子與農村姑娘的似而不是,在蘇淼如的心里曾經是個謎,在讀者心中也曾是個謎,雖然最后謎被解開,但在整個展開的過程中卻讓人覺得朦朦朧朧,因此作品也就產生了一種朦朧美。最能說明這個特點的還是《二月杏》。大亮當了地質隊員后,在異地他鄉的樹林里意外地遇到一位姑娘,當他看到姑娘的眼光后,不僅大驚失色地“啊”地叫了一聲,因為他發現“這是何等熟悉的眼光”!毫無疑問,他覺得自己眼前的這位姑娘肯定是在“文革”開始時被他拋棄的二月杏。他滿以為姑娘肯定能認出他,但得到的答復卻是“不認識”。在隨后的接觸中,他仔細端詳了“她的頭發,眉毛,鼻子,嘴巴,腰身”,發現果然“這不是那個她”,“自己果真是認錯了人”!至此,讀者以為這個女性絕不是大亮的女同學二月杏了。但緊接著,她的“一個笑”又“使他驟然間又證實了這種笑就是他的那個她的笑容”,事情仿佛又出現了轉機,以為她可能是大亮的同學二月杏。但當這次分手時大亮在后面叫了一聲“二月杏”的時候,她卻回過頭來說“你說什么?”證明她又不是那個二月杏了。但當大亮前去她的酒館喝酒時,正逢酒館人多,做招待的老太婆趕大亮走時,她卻像對待多年的熟人那樣制止了老太婆,讓大亮留下喝酒,并問他“你為什么到這里來?”似乎她又是二月杏,她不僅認識他,而且這么多年一直沒有忘記他。在此后的敘述中,讀者也仿佛覺得她就是二月杏:大亮托人帶給她兩百元錢和“十幾片無香無色而潔凈完好的杏花”時,她病了;大亮在電影院前遇到她,她早已買了兩張票,好像早就知道大亮會來似的;看完電影走出劇院門口時大亮在她后面喊了一聲 “二月杏”,“她一個趔趄站住了,回過頭來,突然滿臉淚水”,此后她還讓大亮在樹下等她。所有這些都給人一種感覺:她果真是大亮的同學二月杏,她肯定要跟大亮破鏡重圓,但結果卻出人意料:她遠嫁他方,走了!那么,她究竟是不是大亮那個二月杏呢?最后也讓人無法斷定。是與不是之間的模糊,創造出一種朦朧之美,真可謂“是花還是非花”!
總之,這種在人物形象上故意設謎的方法,是當代小說藝術的一大創新,它為當代小說創作帶來了新面貌。
二、孿生故事
在以往的小說創作中,一篇(部)小說只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盡管在這個完整的故事中也許套裝著很多相對獨立的故事,但它們卻都統一在一個大故事中,中國古代的小說是這樣,19世紀以前的西方小說以及這種小說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被引入中國后所繁衍出的中國新式小說也是這樣。在中國新式小說的歷史上,從它發端那天起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大都走著這樣的路。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卻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那就是不論是長篇小說創作,還是中短篇小說創作,某些作家都在一個作品中同時寫進兩個獨立的故事,有的作品中的兩個故事在人物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系,而有的則毫無聯系。在這些作品中,故事都呈現著雙胞胎嬰兒的特點,它們是孿生的。邵振國的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麥客》,就是人物有某種聯系而兩個故事則完全獨立的小說。作品既寫了父親吳河東當麥客為人割麥的一次經歷,也寫了兒子吳順昌當麥客為人割麥的一次經歷。兩個故事各自獨立,各有自己的起承轉合。霍達的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葬禮》也是如此。作家在這個長篇中,同樣講述了兩個彼此獨立的故事,一個是“玉”的故事,講述的是韓子奇、梁君璧、梁冰玉的婚愛悲劇;一個是“月”的故事,講述的是韓新月、楚雁潮的愛情悲劇。兩個故事中的人物盡管有一定聯系,但彼此又各自獨立。而古華的引起過爭鳴的中篇小說《貞女》則講述了兩個在人物之間沒有任何聯系的故事,一個是“清末一個年少寡婦守節不貞的故事”,另一個是“當今一個年輕女子不守節倒又甚為貞潔的故事”,“兩個故事互不相關”(《貞女》第一章)。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作家本來可以把兩個故事分別寫成兩篇(部)完全獨立的作品,此時乃至此前此后的絕大多數作家也都是這樣做的,但霍達等人卻沒有這樣做,而是讓兩個故事共棲于一個作品中。這種構思和結構方式,可能是受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引進的復調小說創作及其相應理論的影響,但它們卻不是復調小說。因為復調小說是在一個作品中回響著兩個以上截然對立的聲音,是將 “一把雨傘和一臺縫紉機同時擺在一個平臺上”(米蘭·昆德拉語)。中國這些作家不僅沒有追求不同聲音的同時出現,而是始終保持音調的和諧。既然不追求復調,又把兩個故事裝在一個作品中,這樣做究竟有什么好處呢?它給作品帶來了怎樣的藝術效果呢?
實際上,只要做些認真的觀察就會發現,這種敘事方法的好處首先是增強了作品所描寫的生活的縱深感,使作品的內容獲得了厚實的底蘊。對此,古華曾做過直接說明。他說自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作品的兩個故事雖然“互不相關”,但它們“卻交錯滲透”,把它們組合在一起,可以實現作品的“歷史縱深意識”(《貞女》第一章)。其他作家雖未明確道破初衷,但無疑也都是這樣理解的。因為盡管兩個故事在人物和情節上“互不相關”,但在精神內涵上“卻交錯滲透”,它們一旦被組合在一個共同體中,便把出現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生活連為一體,彼此形成互為參照、互為滲透、互為拓展、互為豐富的多重關系,從而極大地強化了作品所描寫的生活的歷史縱深感,在意蘊上遠比單寫一個故事要豐厚得多。《麥客》寫的是已經絕跡多年、在新時期重又出現的麥客生活,邵振國將兩個故事寫在一個小說中。作為老一代麥客的吳河東的這次麥客遭遇,無疑帶有歷史上傳統的麥客生活的特點,他所遇到的顧主張根發也與歷史上敲骨吸髓的地主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而他兒子吳順昌的這次麥客經歷,更帶有新的時代里和新的環境中新一代麥客生活的特點,他的顧主水香也是人性開始覺醒的新一代人,兩個故事組合在一起的結果,是互為拓展,展示了麥客這一古老職業的過去和現在,使作品獲得了深邃的歷史感。《貞女》更是如此。楊青玉的故事發生在前清,作家在這個故事中,講述了歷史上一個被傳統文化中的罪惡的貞潔觀念的繩索捆綁致死的女性的悲劇;姚桂花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作家在這個故事里講述了現實中一個被貞潔觀念壓迫的女性的悲劇,兩個故事人物情節毫不相關。將兩者組合在一起,卻又互為拓展,既讓人看到了這種文化在昔日肆虐的真相,也看到了它在今天仍然殘存著的景象,以及正在逐漸喪失威力的事實,從而使作品形成很強的縱深感。《穆斯林的葬禮》中韓子奇與梁冰玉的愛情悲劇發生在20世紀前半葉,它揭示了歷史和命運對人的捉弄,韓新月與楚雁潮的愛情悲劇發生在20世紀后半葉,它揭示了文化與命運對人的捉弄。兩個發生在不同時空中的故事的組合,互為拓展,使讀者在更開闊的視野里看到了社會和命運給生命個體制造的災難,作品也無疑形成了縱深之感。也就是說,孿生故事大大深化了作品的內涵,它遠比單寫一個故事使作品深邃豐富得多。
在這類作品中,兩個孿生故事除了有相通處之外,還有相異處。如果說相通處增加了作品的縱深感,那么相異處則使兩個故事形成了強烈的對照性。而在文學作品中,對照既可以使事物的特征更為明晰地凸顯出來,也可以使兩個事物構成互相映襯、各美其美的關系,從而獲得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孿生故事之間就具有這種對照關系。《麥客》中吳河東的故事與順昌的故事在對照中顯示了各自的特點,那就是吳河東的故事涂上了舊時代舊生活的色彩,而吳順昌的故事則染有新時代新生活的色彩,二者互為參照,不僅使各自舊或新的特征更為突出,而且舊與新互為襯托,構成了作品的豐富色調。《貞女》中的楊青玉的故事與姚桂花的故事也在對照中顯示了各自的特點,那就是在傳統文化統治密不透風的年代,楊青玉面對這種壓抑無處告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姚桂花雖然同樣受著這種文化的壓迫,但她卻可以求助法律,能自主掌握命運。同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楊青玉在這種文化的森嚴統治下卻“守節不貞”,而姚桂花在這種文化有所松動的統治下“守節倒又甚為貞潔”。這種對照,不僅使各自的特征更為明顯,而且也相映成趣,使作品斑斕多姿。《穆斯林的葬禮》中兩個悲劇故事同樣在對照中顯示了各自的特點,那就是造成韓子奇與梁冰玉的愛情悲劇的是倫理與人性的沖突,而造成韓新月與楚雁潮的愛情悲劇的是文化與人性的沖突。兩個故事的存在形態也大不相同,韓子奇與梁冰玉不僅有愛情經歷,而且也有婚姻生活,并留下婚姻的結晶,就是他們的女兒;而韓新月與楚雁潮僅有愛情,沒有婚姻,更沒有結晶留存。這樣,兩個故事的對照不僅令各自特征鮮明,而且它們的相互襯托也使作品相映生輝。雖然這些作品的創造者們在借鑒復調小說時沒有追求主題的復調性,但他們所設置的孿生故事卻使作品在藝術上具備了復調小說的繁復色彩。
此外,孿生故事還為作品制造了強烈的閱讀懸念。因為既然要把兩個故事裝在一個作品中,那么就出現了如何擺布的問題,即結構問題。檢視這類作品的結構方式,便可以發現它們大體上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對折交叉式,即將一個有情節聯系的故事從中間對折,構成兩個故事,然后又將這兩個故事交叉敘述,《穆斯林的葬禮》即用了這種方法。二是總分交叉式,即開始時本來是一個故事,但隨即一分為二,再將二者交叉敘述,《麥客》就是如此。三是平行交叉式,即兩個故事沒有任何情節與人物上的聯系,是兩個彼此完全獨立的故事,只是被作家組合在一起,在敘述時便采用了平行交叉的辦法,《貞女》即為其代表。不論運用哪種方法,都沒有離開交叉,這恰恰是這類作品在結構上的最鮮明的特性。交叉的后果,是造成了強烈的懸念,也有人稱其為“懸疑”。在敘事文學中,只要有故事存在,懸念就永遠是一種可貴的元素,它能使讀者始終保持強烈的閱讀興趣。特別是交叉造成的懸念還有用其他方式制造的懸念所不能比拼的優勢,因為用其它方式所造成的懸念,如在每章結束時的故意設疑即“且聽下回分解”之類,會在緊隨其后的敘述中很快被釋開,因為作品畢竟是沿著同一情節線索在敘述著。而交叉所制造的懸念則不同,因為作品是在沿著兩個情節線索敘述,每條線索的中斷都要等待同樣長度的另一個情節線索敘述過后才能接上,懸念只能等到那時才會被解開,這樣它更需讀者有較長時間的等待。等待愈久,懸念的力量就愈強。如《穆斯林的葬禮》所敘述的兩個故事,“玉”與“月”字章等量交叉,即一“玉”過后便是一“月”,然后再是“玉”、“月”,如此往復。正當讀者興趣盎然地沉浸在“玉”字章中所敘述的韓子奇與梁冰玉、梁君璧的故事的時候,情節突然中斷,進入“月”字章所敘述的韓新月與楚雁潮的故事,于是懸念出現了。急于知道“玉”字章的后續情節的欲望被強行切斷,便形成了作品的強烈吸引力。同樣,隨著新的情節的推進,讀者不斷地沉浸在這個新的情節中,興趣逐漸高漲起來,然而恰在此時,“月”字情節中斷,又轉入“玉”字故事,讀者的好奇心再次經受了新一輪的刺激。因此,作品在一個又一個懸疑與釋疑的交替中走向兩個故事的終點,讀者也在一波又一波的興趣涌動中讀完了作品。《麥客》、《貞女》也都是如此。總之,孿生故事確有其優勢和魅力。
三、反觀視角
任何一篇(部)小說都存在著從什么視角去敘述的問題。在當代小說創作中,作家特別注重對敘述視角的選擇,并且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和深刻闡釋,但其中仍然有一個問題似乎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反觀視角的運用以及由此產生的獨特效果。這里所說的反觀視角,是指作家的敘述是從作品中的否定性人物的眼睛和心靈里展開的。之所以應該充分重視這種敘述,是因為自從新式小說出現以后,作家在用作品中人物的視角進行敘述時,總是選擇肯定性人物。上世紀20年代蔣光慈曾試圖出新,在《麗莎的哀怨》中嘗試著用否定性人物,即一個流亡上海的白俄舊貴族女性作為敘事者,通過她的“哀怨”表現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但小說發表后卻招致了激烈批評,批評家不約而同地指責蔣光慈同情白俄貴族。此后這種反觀視角再也沒人敢用了。到上世紀50年代以后,情況仍無多大改觀。著名老作家魏金枝有感于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曾經站出來進行呼吁,主張不妨嘗試著從反面去寫。他說:“為了殺敵致果,難道不應該運用一些襲擊、側擊,以及從敵后打敗敵人的戰術么?”“在選取題材時,首先應該從多種角度來著眼”,“運用多種角度,作多方面描寫”(魏金枝:《大紐結和小紐結》)。盡管他說得極有道理,但可能擔心被安上同情否定性人物的罪名,這種視角始終無人敢于問津。及至上世紀80年代初,這種僵局方才被打破。那些熱衷于改革文學創作的人,率先在創作中重新啟用了這種視角。金河的獲得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不僅僅是留戀》,矯健的同獲這一獎項的《老霜的苦悶》以及隨后出現的魯彥周的《啊,萬松莊……》等等,都無不如此。它們一改此時或以往通過肯定性人物的視角來反映某種社會運動的老套,選用反觀視角來反映改革生活。《不僅僅是留戀》從張家溝大隊黨支部書記鞏大明的角度來寫改革。鞏大明這樣的在以往的文學創作中總是被設計成正面形象的角色,在這里被作家設計成了否定性人物,通過寫他在集體解散牲畜分給個人時對昨天的留戀、失落、悲哀等等灰暗情緒,從反面展示了改革春潮對生活的激蕩。《老霜的苦悶》則把以往文學作品中總是寫成正面人物的老貧協主任、老勞模田霜設計成否定性角色,通過寫他對政府鼓勵個人發家致富的政策不能理解和由此引發的苦悶,從反面再現了改革引起的社會震蕩。《啊,萬松莊……》也是如此,作家同樣把昔日的勞動模范、人民代表“老主任”金松康設計成否定性角色,通過寫他對先前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恪守,對改革政策的抵制,以及面對失敗所產生的“傷心”和“彷徨”,寫出了改革的大趨勢的不可抗拒。它們都從反面背面來敘述,成功地運用了反觀視角,使作品顯得新穎別致。
反觀視角的選用,不僅使作品新穎別致,而且還產生了某些特殊的效果,這突出地表現為作品具有明顯的折射感,一種強烈的藝術折光。我們知道,追求藝術作品的折射感,是很多藝術家千方百計地要達到的目標,不論是攝影藝術家、繪畫藝術家,還是詩人、小說家,無不特別重視運用這種表現藝術。在小說創作中,尤其是短篇小說創作中,那些有經驗的作家都特別注重對折光的追求。從上世紀20年代魯迅的《風波》,到上世紀60年代艾蕪的《雨》,都莫不如此。但是,實現折射的途徑卻多種多樣,反觀視角的運用就是其中的重要途徑之一。這類作品大都意在展現重大的社會生活,但它們卻不直接地正面地切入生活,而是從反面或背面來寫,從作品所設置的否定性人物的心理和情緒的變化中,折射出重大的社會生活的某種狀況,作品由此便獲得了一種折射感。當年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就是如此,它通過麗莎這一白俄貴族女性流落中國上海后的境遇和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詛咒,間接表現了這一革命的偉大勝利。上述新時期小說家的表現中國社會改革現實的作品也是如此,它們的主要創作目的是反映改革生活,但卻不是正面展開,而是從否定性人物的感受和情緒活動中展開,讀者所見到的不是直接展示的改革現實,而是在人物種種不適應的內心反映中折射出來的現實,從而間接地窺見了改革生活的真相,這樣作品便形成了明顯的折射感,也就是一種強烈的藝術折光。比如,在《啊,萬松莊……》中,讀者跟隨被改革的車輪所拋下的原萬松莊大隊“老主任”金松康回鄉的腳步來到了萬松莊,透過他午睡起來站在堂屋前向東望去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座新樓已經蓋好了”;從他“覺得腿有點兒酸,便順勢在石頭臺階上坐了下來,怔怔地望著門前那條路”的視線里,看到的是一條舊路的廢棄和一條新路的修成;隨著他“拖著疲軟的步子慢慢離開自己的家”到村中漫步,我們又從他的視線里看到了廢棄的場院和在這里新建的校舍,然后又看見了精耕細作的農田和長勢旺盛的莊稼,特別是看到了廢棄多年的池塘里養起了鯉魚的興旺景象。這種種興旺景象當然不是金松康愿意承認和正確理解的,在他的內心深處仍然充滿了拒絕承認和強烈的失落情緒,但讀者卻從他的視野里和心靈活動中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化,間接地感觸到了改革現實。同樣,從《不僅僅是留戀》中的鞏大明灰暗的眼睛中所展現出來的生產責任制正在實行的景象,從《老霜的苦悶》中田霜灰暗的心理展現出來的人們正在忙于個人發家致富的景象,都是間接反映,都是一種藝術折光。可以說,反觀視角的選用使這些作品帶上了一種折射感,它們有如高明的攝影師在鏡子里拍下的拍攝對象的影像,呈現出一種曲折變幻之感。
正是由于作家通過人物的心理情緒來反映外部現實,因而為作品帶來了另一個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把外在現實內在化,把社會生活心靈化,使作品呈現出明顯的心理性特征。讀者在這里看到的就不僅僅是外部現實的真實圖景,而且更有人物的心理圖景。這種心理圖景都是在這些否定性人物面對變化了的現實所引發的心理沖突中展開的。在作品中,他們都不能與時俱進,不能跟隨新的現實腳步不斷前進,而是頭腦僵化地固守著昨天,當昨天即將過去時,他們仍然死死地抓住它不放,從而對已經到來的今天產生了強烈的對抗情緒。正是在他們的心理與現實的強烈沖突中,他們的心理圖景得到了真切的呈現。在《不僅僅是留戀》中,我們就清楚地看到了鞏大明的心理圖景:面對昔日的社員分畜到戶的火熱場面,他心里先是不滿,總是無端地發火,沒有好氣地對待與他搭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深情的懷念:他懷念1955年冬天他是如何在這個院子里給鄉親們做入社動員的,懷念1958年秋天他又如何在這里主持召開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他久久地沉浸在對當年的火紅熱鬧的回憶中。當懷念無法改變眼前的事實時,接踵而來的便是憤怒:當他看見今天在分牲畜時有人的那股高興勁兒,便想起了1947年土改分地主財產時翻身農民高興的情景,但他認為當年分地主財產時你高興是正常的,而今天是在分人民公社的財產,你還高興什么?于是他真想對著高興的人“一巴掌甩過去”。由于憤怒,他再也壓抑不住火氣了,他不僅斥責別的社員,而且斥責自己的兒子。最后面對空空如也的院子他心里又升出了無限的留戀:“這個馬棚是1958年他任三隊隊長時蓋的,已經沒有什么保留價值,該拆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也許再也看不到這個大院的昔日景象了,后人還會說起鞏大明么?”作家圍繞鞏大明的心理與現實的沖突,非常清晰準確地勾畫出他的心理變化過程,色彩分明地描繪出他的心理圖景,把一幕集體解散時的生活景象內化成人物的心理畫面,讀者所見到的早已不是單純的外部現實,而且更有人物的心靈現實。《老霜的苦悶》、《啊,萬松莊……》所寫出的同樣是田霜、金松康的心理現實。可以說,這種化外部生活為心靈活動的敘事藝術,使文學有可能真正走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最終完成文學是人學的藝術使命。在人物的激烈心靈沖突中,除了能間接窺見引起這些沖突的外部生活之外,還能更深入地揭示人的靈魂和人性深處的某些隱秘的東西。我們在鞏大明等人的靈魂深處,就看到了人永遠不愿打碎自己親手搭建的七寶樓臺這一人性特點,它無疑加深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深度。
更為引人注意的是,反觀視角的運用,也為作品帶來了悲喜交融的審美效果。在文學創作中,通過悲劇的形式獲得喜劇的效果,是很多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標,因為這種悲喜交融的審美形態可以給讀者帶來獨特的閱讀感受。這些作品就是如此。它們描寫的是昔日的主任、書記、貧協主任面對改革后變化了的農村現實引起的種種心理沖突,沖突的結果造成了強烈的內心痛苦。這些昔日的英雄們的內心痛苦,表面上確有濃重的悲劇感。鞏大明面對集體解散時的內心痛苦,田霜面對社會允許個人發家致富的內心痛苦,金松康面對心中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被改變時的內心痛苦,都帶有悲劇感。特別是作家在整個敘述過程中又總是沿著人物的心理邏輯展開,這就更使這種悲劇顯示出局部的真實感,尤其是作品細致準確地描寫的人物因不理解而與現實發生抵觸所造成的巨大內心苦悶,是很感人的。如老霜每當自己苦悶至極而又無法排解時,就偷偷地走進幽黑的小倉房里翻看作為自己輝煌過去的標志的各種獎狀的行為,確實使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個苦悶的無所依皈的靈魂,讓人感到一種濃濃的悲劇情緒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然而,這種悲劇又被裝在了喜劇的大框架中,使悲劇只成為一種表象,而喜劇則是更內在更根本的因素。由于這些“英雄”都是在逆時代潮流而動,他們妄圖扯歷史的后腿,在必然前進的生活大勢面前,他們的行為無疑是極為滑稽的,作家將這種“無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魯迅語),自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喜劇效果。鞏大明、田霜和金松康們的不識大局和由此引起的失落和無奈,留戀和苦悶,不僅違背了社會行進的方向,背逆了時代的潮流,而且事實上根本阻擋不了歷史車輪的前進。他們硬要抓住已經風化的骸骨,以此排拒新生事物,不論他們自身的行為顯得多么莊重和悲壯,也都是可笑的,是喜劇式的。他們的各種各樣的苦悶情緒只能引人發笑。作品就是在形式上的悲劇與實質上的喜劇的交融中創造出豐富的悲喜交加的審美效果,帶給讀者的是一種“含淚的微笑”。可以說,反觀視角的運用為中國當代小說增添了很多新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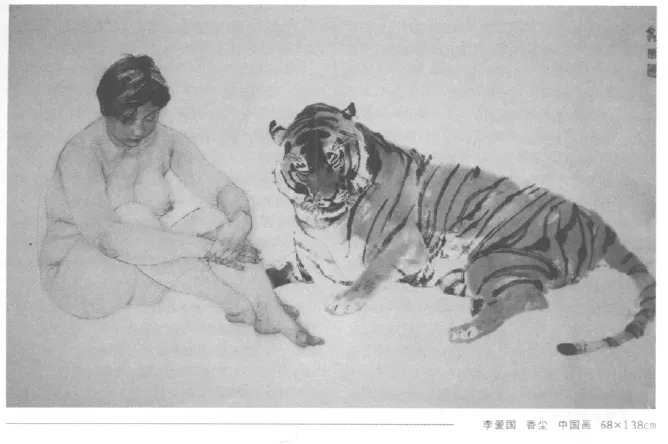
當然,中國當代小說在藝術上的新變,絕不限于設謎人物、孿生故事和反觀視角這幾種,而是在這之外還很多很多,值得研究者多方探討,本文僅為引玉之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