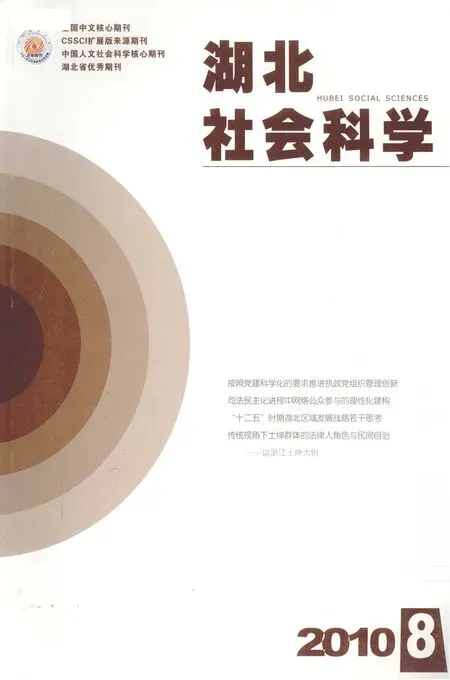孟荀人性論的再審視
譚紹江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2)
孟荀人性論的再審視
譚紹江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2)
“論說”是先秦諸子為實現各自理想所采取的重要手段。論說主旨和所面對的論說對象的同異決定了諸子某些具體的思想內容的同異。孟荀二子在闡述人性論時,主旨同為實現儒家理想,所面對的對象也都包括了“在上者”和“庶民”兩種對象。從這種視角出發,二子在人性論上的觀點之同異可以被再解讀。
孟子;荀子;人性論;在上者;庶民
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作為先秦時期兩位儒學巨擘,二人迥異的觀點差異帶來了后世數千年的紛紜聚訟。筆者發現一個前人或有所忽略的問題,那就是,二子在進行立論之時,是如同今日文章一般,將所有觀點統一地面對全體讀者呢,還是每篇、每段論說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象,按照對象的不同在進行分別的論說呢?這值得分析。
論說是先秦時代知識分子都致力從事的主要工作,孟、荀也不例外。他們在各自的年代圍繞著能否實現儒家的理想主張,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進行了大量“論說”。從這種論說的角度出發,我們發現,孟、荀在許多理論的闡述上都是有著鮮明的“對象性”特點的。也即,對于同一個問題,二子文章是在面對不同言說對象進行不同的言說。雖要旨為一,但在具體論述、觀點上有相應之差異。而再以此“論說對象”的特點出發,我們發現二子的關于“人性”的思想內容可以進行重新的解讀。
二子在“人性”上的論說對象大體可以分成兩個類型。一個是面對“在位者”“、在上者”或者“為君者”這樣一些掌握權力者或者將要掌握權力者的論說;另一個則是面對庶民、眾庶也即面對全體人群、一般人類的論說。按照這種論說對象的劃分,二子在“人性論”上的觀點有一番異同需要重新審視。
一
為達成自己的政治主張,孟、荀都孜孜奔走于各國諸侯之間,用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對諸侯們進行勸導,以期見用,在其論說中就包含著“人性論”的內容。
先看孟子。他在與梁惠王對話時講道“: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這里孟子的主旨不是在討論“人性”,但是他言論中的內容卻無疑正是將人性中所包含的某些內容透露了出來,也能窺見他對于人性的部分看法。他認為“士”與“民”在人性上是有區別的,這個區別也即能否保有“恒心”。朱熹注曰“: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1](p203)也即,孟子認為于“民”而言,若無恒產常處困窘中,則人性中的“善心”并不能常駐。“善心”不常駐,則會作惡。因此,為君者必須把握“民”在“人性”上的這個特點,先解決庶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問題,方能引導成善。“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無疑,此處站在“民”的立場上,孟子認同了“人性”中作為自然欲望的內容。這與他的論說目的密切相關。此時面對掌握了實際政治權力的梁惠王這位“在上者”,他必須鮮明地指出這一點。只有將人的一般自然欲望都算作“人性”——而且對于“民”而言是必須首要滿足的“人性”,才會讓“在上者”去著手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他所極力推行的“仁政”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再看荀子。荀子之書,對話式較少,大部分都是直接論述的,所以他某些論說對象不能像孟子那樣直接就知道,但是也并非就看不出來。從言論內容、態度以及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仔細分析,大體可以窺見他論說時所面對的對象是什么樣子的。圍繞著他的主張,他的論說對象有分別。“與很多具有勸說傾向的著作不同,《荀子》有選擇地設定說服對象。”[2](p17)他講“性惡”的時候,對象就不是一般庶民百姓,而是“在上者”或者潛在的“在上者”。
我們來看他論述的邏輯以及最終之目的。他是從人的天生之性說起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荀子·性惡》)他認為,能被稱為“人性”的應該是天然而具有的,這種東西最直接就是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天生能力。如“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煊,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惡》)這是講欲望。“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荀子·性惡》)這是講天生的能力。對這種欲望和天生能力本身,他無意定其善惡。真正的“惡”來自對欲望的放縱。“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王先謙注曰:“性,天生性也;順是,順其天性也。”[3](p434)顯然,荀子不是直接將人性定義為“原罪”的“惡”,他是先承認了人具有“好利疾惡”、“耳目聲色”這樣一些“天生”的基本欲望,如果完全順從、放縱下去就會演變成“惡”。
那么此時,他的論說對象是誰呢,是面向庶民嗎?我們看他下面的說明:“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他此處是在對上述“性惡”現象提出的解決之道——“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從上下文結合起來的傾向上看,在荀子的思維中,“師法”、“禮義”不可能是一般民眾自己能具有的,而應該是來自庶民個體之外的力量,包括“圣人”、“圣王”。“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為,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惡》)這里就更進一步表明了這種態度,解決人性本身可能帶來“惡”的弊端的方法之“禮義”,不在一般人自己那里,而在“圣人”。“圣人”應該是庶民還是在上者呢?“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這一段話講得很清楚,靠“人”、靠庶民自己的話,則會在一連串“不能不”之后,必然”會達到“爭則亂,亂則窮”的地步。真正在最后能起到解決問題作用的還是能“制”“禮義”的“先王”,他顯然不是一般的庶民,而應該是能夠引導、領導眾人的“在上者”。他當然也講到過“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荀子·禮論》),但他這么講只是在強調“圣人”的來源問題,并不影響“圣人”在地位上應高于眾人的判斷。荀子在此處所強調的“性惡”,與其說是專論一般之人性,不如說是站在“在上者”的角度審視一般庶民的人性。對于要達到“治”的“在上者”而言,他應該明白,在普通庶民人性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自然欲望,這是庶民自身無法控制的。如“在上者”不加以節制疏導,則后果便是惡”的流行。這樣就為“在上者”從外在的路徑通過“隆禮重法”的方法推行儒家的理想以引導與管理社會秩序[4](p89—94)找到了人性上的根據。
以上內容是孟荀二子在面對“在上者”時的“人性”論說,我們發現,二子共同點是都試圖讓“在上者”明白一個道理,即庶民人性中的自然欲望是需要重視的。二子差異在于孟子是要讓“在上者”想法去滿足庶民的基本欲望,荀子則讓“在上者”想法去節制庶民欲望的過度。
二
再來看二子是如何面對另一種對象——庶民或說一般人群進行“人性”論說的。
孟子講“性善”從人心中皆有之“端”說起。他認為人皆有與生俱來的“仁”、“義”、“禮”、“智”四者之“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人若保持這四端不喪失,并將這“四端”不斷培育、推廣開去,便能成“善”乃至成“圣”。他強調,此乃人應具有之本性,是一種人“固有之”的能力,“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這也就是他所謂“人性善”的基本涵義。那么,他講“性善”是面向什么對象在進行的呢?從《孟子》文本本身來看,孟子講“性善”有不同的場合,有時是獨白,有時在和人辯論,有時是在向學生宣講。但若進一步分析他之所以持“性善”之論的背后原因,我們可以確定他講“性善”最主要面對的對象應是“庶民”或者說一般人群。孟子講“性善”,最根本的原因是要上繼子思《中庸》的主旨,為在一般人中挺立“君子”這個“道德主體”夯實先天的依據。[5](p5—12)同時,有些時候,他在激烈地強調“性善”還有更直接的動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桊乎?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桮桊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桊,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章句上》)朱熹注曰:“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1](p308)顯然,孟子此時講“性善”的直接動機就是非常擔心一旦告子將“人性”與“仁義”分開的理論被傳播開去,會使得天下民眾思想混亂而不肯再勉力行仁義,鑄成巨禍。所以,他要竭力批駁告子,以正視聽。由上可知,孟子講“性善”是想告訴以庶民為主的天下人,一方面,大家都先天具有為善的能力,是性善之人;若是有人為惡,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問題,而是自己將之喪失而不找尋的問題。另一方面,若是有人向大家宣揚人性不是“善”的理論,大家千萬不能相信,因為那樣會讓大家迷失人生道路進而迷失社會的方向以致天下大亂。所以,無論孟子是要為人能挺立“道德主體”夯實先天依據,還是擔憂“非性善論”的泛濫會使得天下人心錯亂而帶來社會動亂,他都是以全體人群或者說庶民為對象的。
荀子講“人性”也有個面對庶民的論說問題。我們仔細審視荀子之文,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天生的自然欲望和能力之外,分明還有一部分內容也是人性的題中應有之義。比如,“義”和“辨”。“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生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荀子·非相》)上文中第一段中所論之“義”不僅屬于“人性”,而且是人特有之性,因為因它才使人“最為天下貴”,優于其他非人類事物。第二、三段又進一步強調了“辨”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那么他這樣講人性的時候是在對誰講呢?其實在他的言辭里面我們已經可以找到答案。他在性惡》中寫道:“‘涂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能可知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為禹明矣。’”
很明顯,他說這么多關于在人性中具有的“最為天下貴”的特性,就是要講給“涂之人”聽的,也即面對最普通的大眾,以庶民為主的天下人為對象。其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擁有“為禹”的信心,勉勵人行善。
將以上內容對比,我們同樣發現,在面對庶民時,孟荀二子在“人性”內容的觀點上也有極大的相類性。他們都積極強調人性中具有主動為善、進行道德理想追求的內容。不同的是,孟子講“性善”的時候有意排斥其他人性成分,而荀子在講人這種“仁義法正”之質具時,并不排斥其他的人性內容。
三
通過審視孟、荀二子在面對“在上者”和“庶民”時所進行的具體的“人性”觀點論說,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新的結論:其一,孟、荀二子原來看似水火不容的兩種“人性論”主張,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十分相同的內容。這種相同一方面體現在具有相同的推行儒家理想的主旨,他們都是想通過對社會中個體的良好培育推展到社會的整體和諧;另一方面,他們在思考如何去推行儒家主旨時所選取的角度也是相同的。他們都是選擇面對“在上者”和“庶民”時進行不同的“人性”論說。并且,面對“在上者”時,都會強調“人性”中自然欲望的內容需要重視,面對“庶民”時,都會強調“人性”中道德能力的內容需要重視。其二,孟、荀二子的“人性論”都是多層次的。自然欲望與道德能力,起碼這兩種內容在他們的“人性論”觀點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當然,對這兩種內容的位置排布有所不同。一方面,各自有突出的重點,孟子當然突出了道德能力的內容,而荀子更強調自然欲望的內容。另一方面,在對待這兩種內容的態度上有差異。孟子在強調一個內容的時候,會排斥另一個內容。例如,他在強調人的“道德能力”時候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盡心章句下》)他告訴大家,人性中有自然欲望,但是人的自然欲望在現實中會受到許多客觀因素(所謂“命”)的制約,根本無法真正自主地追求,不是人性的本真,故而應將之排斥在“君子”所確認的“性”之外。荀子異于是,他講兩種內容時采取的是將二者合而言之的態度。上文已經提到過,荀子論“人性”時很注重“合”的問題,他在強調人比其他事物“貴”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人有“義”時,也并不因此就把人性中與其他事物相同的那部分屬性排斥掉。其三,二子論說“人性”時所選取的論說對象的重心不同是導致二子差異的主要原因。顯然,孟子更為看重的是對庶民、普通大眾的論說。從孟子的態度來看,他對自己通過說服“在上者”來推行“仁政”的現實可能性是有憂慮的。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章句下》)朱熹注曰:“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于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1](p240)孟子口中說的是樂觀而無豫,其心中實憂。因此,通過“在上者”這條路徑去推行“仁政”不是他真正的學術重心,其重心在于在當時復雜的生存狀態下,為眾庶找到一條反身向內、成己成人的道路,他希冀讓所有人(尤其是生存狀態不理想的人)通過心靈的修持而達到維系信念、保有信心的道路,保持住生活的希望。在個體成善的基礎上,使得社會能真正和諧。所以他要強調“性善”的問題,強調“善端”的問題。
而荀子更看重的則是針對“在上者”的論說。對于通過“在上者”來推行儒家理想,“隆禮重法”,他有一定的信心,并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有較為全面的論證。所以他指責“思孟學派”時很大的原因是擔心在面對“在上者”時過于強調人性中“性善”的東西不能達到說服的目的。他認為“思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在這段話里面,他首先就指出孟子的錯誤在于“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也即對儒學如何通過“先王”這條路徑的傳播是弄錯了的。結合前文的分析,荀子認為以“先王”立場推行儒學應該以“人性惡”為基礎,否則,就不需要“先王”、“圣人”來特地引導了。而在下者的庶民們也就失去了“為學”的動力。“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荀子·性惡》)我們看到了荀子站在他的主要論說立場上體現出來的巨大憂慮與擔心。這與孟子對告子的擔心如出一轍。
總之,從“論說對象”這個視角進行簡要關照,我們發現,孟、荀二子對人性的真正看法都是清醒而全面的,并非偏狹之論,且作為儒家,二子在人性論說的主旨上也是相同的。造成二子在某些具體觀點的激烈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的論說重心的差異。孟荀二子在“人性”論上的主張可以互為補充,我們不應對之過于對立地看,而應更多地采取綜合的態度。
[1]朱熹.四書集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2]陳文潔.荀子的辯說[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3]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4]化濤.“隆禮重法”與王霸兼用——荀子政治思想研讀[J].臨沂師范學院學報,2007,(1).
[5]胡治洪.中庸新詮[J].齊魯學刊,2007,(4).
[6]米繼軍.荀子“隆禮重法”觀辨析[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3).
[7]陸建華.荀子禮法關系論[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
責任編輯 高思新
B222.5 B222.6
A
1003-8477(2010)06-0112-03
譚紹江(1981—),男,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