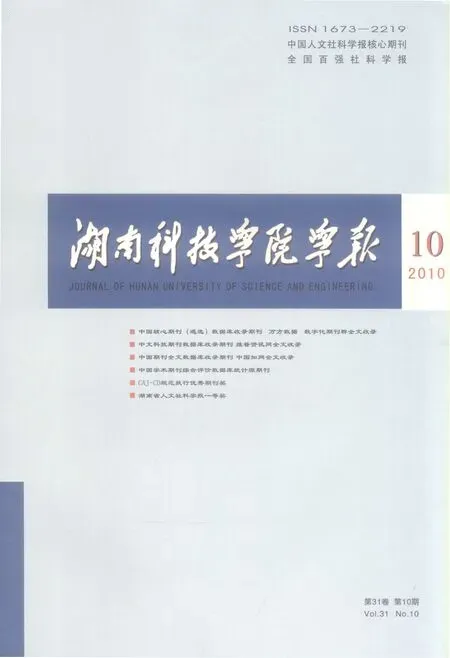論周敦頤的人生態度
徐儀明
(湖南師范大學 哲學系,湖南 長沙 410081)
論周敦頤的人生態度
徐儀明
(湖南師范大學 哲學系,湖南 長沙 410081)
周敦頤作為理學開山,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響,但其主導觀念則是儒家學說。這不僅表現在他的學術著作中,同樣也體現在他的人生態度上。那種認為他思想為儒,生活為道,或謂其生活非一圣賢型儒者之生活的說法是偏頗的。應還原他儒學宗師的真實形象。
;周敦頤;理學開山;人生態度
作為理學開山,周敦頤以倡言探尋“孔顏樂處”而聞名,二程、朱熹等理學名家莫不紛紛著文大加贊嘆。縱觀濂溪先生一生“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讀其書可以知其人,我們能夠看到周敦頤在對山水草木的觀賞中、在與事 事物物的接觸中以及在道德生活的砥礪中,都體現了儒家仁人君子高尚的人生態度,顯示了其獨特的人格魅力。下面,我們就對周敦頤的人生態度問題做一論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孔子有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周敦頤既仁且智,其對山水的熱愛體現了儒者追求自然和氣、渾然天成的人生境界,并顯示了掙脫世俗名韁利索羈絆的瀟灑和快樂,這其中包含了更多的極富啟發性思想內涵,使得后人反復琢磨、反復回味并深受啟迪。
周敦頤寄情山水的詩文雖然不是很多,但都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意味,表現出天然純樸的情趣。其云:“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喜同費長官游》)這是說只有舍棄了追名逐利之心,才能夠真正專心致志地去尋山尋水,所以感嘆高巖可上,伴侶難覓。濂溪在《同石守游山》一詩中進一步發揮了這種認識,詩曰:“朝市誰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云無語似相留。旁人莫笑憑欄久,為戀林居作退謀。”(在深山峽谷中漫游,他感到無比的舒暢,塵世間的煩惱都被拋到了腦后。幽靜的松杉林中正好可以短吟低唱,度水登山舒展著四肢,野鳥成了如影隨形的伴侶,白云默默在身邊徘徊表達了無限的眷戀。最后兩句體現了歸隱山林的情趣,旁人也許不能理解,然而這正是自己所謀慮的最終歸宿。在《書仙臺觀壁》中則說:“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躋攀聊足到官心。”在周子看來,尋勝與尋仙是密不可分的,盡管“官心”未泯,但仙境更樂,風物怡人。類似的詩篇還有一些,就不一一例舉了,大致上都流露出追高慕遠、高棲遐遁之意。在周敦頤的姻親蒲宗孟所寫的《濂溪先生墓碣銘》中有這樣的描述:“(濂溪)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筑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乘興結客,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躡雪岺,放肆于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籃輿而往,登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為逍遙社,但媿以病來耳!’”朱熹對蒲宗孟的這段描述頗不以為然,刪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顯然是認為有損周敦頤的“醇儒”的形象,理學宗師怎么可以“以仙翁隱者自許”,終日與高僧道人結伴而行呢?當然,蒲宗孟應該比朱熹更了解周敦頤的生平事跡,且不說其中有關僧道之類說法怎樣,僅就濂溪酷愛山水的高雅情趣,就有他自己的詩可以印證,決非蒲宗孟空口騰說。其實,樂山樂水并非僧道的專利,儒者向往山林水畔之樂也無可厚非,即使和那些高僧道人結伴而行也不必大驚小怪,更顯出周敦頤所具有“與眾樂樂”的胸襟。濂溪對大自然秀麗風光的酷愛,深深感染了他的弟子們,特別是后來成為理學重鎮的程顥。程顥也寫作了不少山水詩。比如:“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瞽朦。辜負終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白云道中》)“參差臺殿綠云中,四面筼筜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草堂詩》)“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與云膏洗俗腸。”(《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餐甚佳》)顯然受到濂溪詩作的感染,但比起乃師來,程顥不僅描述徜徉山水、志在林泉的雅趣,而且直接將慕神仙、讀真誥、餐冰片、乞云膏寫入詩中,流露出濃重的道教情結。然而,這并不影響程顥的大儒形象,似乎后儒也并未把程顥的這些詩放在心上。朱熹甚至說:“(明道)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朱子語類》卷九十三)為什么偏偏那樣計較蒲宗孟的《濂溪先生墓碣銘》中的這類文字呢?顯然,朱熹更重視周敦頤的理學開山的地位,更希望他是一位醇正的儒學大師,以承續先秦儒家以來的道統。毋庸諱言,在周敦頤思想中,三教合流的內容、儒道互補的觀點不能說沒有,然而,他仍是以先秦儒家學說作為母本的。他強調《中庸》的“誠體”、《易傳》的“乾元、乾道”之說,顯發了儒家形上智慧的思路。濂溪又引《尚書·洪范》“思為圣,睿作圣”之句,指出“思”為圣功之本,已經在強調理學的內圣功夫了。只是由于其說尚屬草創未能圓滿,故須后人繼續予以發展,這一點是我們能夠理解的。
至于具體說到周敦頤山水詩的影響,程顥有一段話頗具有代表性。其云:“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遺書》卷三)這里所謂“有吾與點也之意”典出《論語·先進》,是說孔子與“二三子”相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謂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即曾點)號稱是孔門的“狂者”,他和子路、冉有、公西華的志向大相徑庭。子路等人皆以命世之才自詡,獨曾皙希望能夠在暮春之時,與同學少年結伴而行,沐之春風,浴之沂水,舞于郊野,歌詠于歸途,可謂其樂融融,遁世無悶。而孔子深有感觸,喟然長嘆,產生共鳴。當然,對于這段話,后人的理解各不一樣,大部分人的意見是認為,孔子因其行道救世之志未遂,故有退隱待時之意,其與曾皙浴沂之說的契合點正在于此。并非孔子真的想要歸隱,不過是以退隱作為韜晦之計罷了。這類說法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卻都顯得太功利了,缺乏對這段話做出美學的理解。曾皙所描繪的是一幅美輪美奐的畫面,人們愉悅的心情與美麗的大自然融合在一起,非常富有詩情畫意。孔子顯然是陶醉在這種美的享受之中,才能發出由衷的謂嘆:吾與點也!由此看來,程顥是真正理解這段話的真諦。所以他說,自從拜周敦頤為師之后,就學會了吟風弄月,才有像孔子一樣的類似感喟,領會到了大自然所賜予心靈的快樂、陶醉、飄逸和自由。領會到孔子所說“詩可以興”的深刻含義,那就是清新雋永、意境深遠的詩篇能夠激起人們的美感,調動情感的積極因素,從而可以使人們能夠從詩歌的鑒賞中獲得美的享受。儒家詩教之本即本于性情,詩歌對人們情操的陶冶功能,在儒家心目中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如此看來,周敦頤的詩作所表現出來“樂”,是一種自然的流露,自有著清明和樂氣象,頗與濂溪一生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的心路歷程相吻合。至于后世有人恐怕這些詩作有損周敦頤的醇儒形象,明顯是過慮了。其實不管是道家還是佛家的東西只要能激起美感,都可以歌而詠之,而不要在心中橫亙這森嚴的壁壘。盡管朱熹很計較蒲宗孟的那段話,但他也說過:“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朱子語類》卷一二五)流露出對道家的一些好感。所以,我們說無論是作為理學開山的周敦頤,或是其高弟程顥,甚至朱熹,他們的詩歌創作的這種審美情趣還是應該加以肯定的。
二
關于周敦頤的生活態度或生活情調,勞思光教授有如下評論,其云:“濂溪所以并無后世儒者之危苦意味,即因濂溪在理論上雖有一屬于儒學之系統,但其生活非一圣賢型儒者之生活,而是一種名士或高士之生活。而此種生活情調,正道家人士或道教人士所具之情調。”(《新編中國哲學史》第109頁)勞氏舉出濂溪之詩作來作為此論的佐證,并認為濂溪之生活態度,與二程不同,更與朱熹大異。筆者認為勞先生之論恐怕也有不當之處。
首先,何謂“圣賢型儒者之生活”?如果以程頤“程門立雪”那種威嚴冷峻型為典范,則大部分儒者的生活態度似乎都不夠“圣賢型”之標準。孔子為儒學之開創者,尚有“吾與點也”之樂。而孟子所標榜的“三樂”則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認為君子的這三種快樂與德服天下并無關系,而是自己內心中的愿望與抱負,一是親情二是私德三是育人,顯得平實無華。就這樣宋儒尚認為孟子的氣象不夠“溫潤含蓄”,而不如顏回具有一團自然之和氣,淵深純粹。在宋代理學家之中,程顥的氣象最為人稱道和仰慕,并被視為楷模。如說:“視其顏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先生接物,,辨而不聞,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并概括為“心平氣和”。(程頤《明道先生行狀》)其實這些類似的贊美,也被用在周敦頤身上,如何仲平《贈周茂叔》詩云:“及物仁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因此后儒認為“濂溪清和”(朱熹語)。黃庭堅所說的“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也可以理解為“清和”“和樂”“中和”等意思。由此看來,“圣賢型儒者之生活”是偏于安靜、溫和、含蓄、超脫、圓融,可以說基本上是屬于陰柔性質的。當然,也并不是說這種陰柔性質就是唯一的圣賢生活態度或生活情調。應該說,“圣賢型”標準并沒有固定劃一的模式,既有我們這里已指出的周敦頤、程顥式的偏于陰柔的,同時也有其他諸如果敢、凜然、無畏、堅強等偏于陽剛性質,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所以,不能說偏于陰柔就是道家,偏于陽剛就是儒家,這樣的認識顯然是一偏之見。事實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修養、不同的氣度和不同的現實境遇,會造就出不同類型的圣賢,這個道理恐怕并不難理解。不能因為周敦頤“并無后世儒者之危苦意味”就斷定“其生活非一圣賢型儒者之生活”。
其次,周敦頤的生活態度或生活情調,并非勞先生在其書中所說的僅僅表現為對山水仙道的熱愛,濂溪具有儒家“泛愛眾”的廣闊胸懷。他的這一生活情調,受到后儒的仿效和追捧。《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附錄雜文》有著一些記述。現擇其要者錄之于下: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于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艮”字可了。
以上節錄的幾段話,是程顥在游學于周敦頤門下時所記,也夾雜了明道自己的一些體會。當然,這里的語句相當短,有的意思也頗費猜詳,顯然需要做一些分析與闡發。第一句,即人們較為熟悉的問題,即尋孔顏樂處。《論語·述而》:“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雍也》又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所講的顏回之樂,亦即是“貧賤之樂”。盡管貧賤本身并沒有什么可樂的,但是作為賢者的顏回,它具備了高尚的“仁德”,他就能感受到人生的快樂。程顥對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可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程氏遺書》卷十二)這個“深意”就是,“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應該說程顥(包括程頤)對孔顏樂處的理解是很深刻的,顯然對老師的這一教誨心領神會并有所發揮。其實,在筆者看來,周敦頤《愛蓮說》所闡發的核心思想就是“尋孔顏樂處”。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講的就是無論外在環境怎樣,要始終保持自己固有的本然狀態。這和身處陋巷、粗茶淡飯,而不改內心之樂的賢者風范是一脈相承的。蓮花是儒家的君子之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不可褻玩也”,象征一種特立獨行的生活態度,趨時守中的處事原則。這正是儒門的一貫心法,而周敦頤將之以形象的語言描繪出來,就顯得更加耐人尋味。第二句: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與第三句:觀天地生物氣象,應該合看。《易傳·系辭上》說:“生生之謂易”,孔穎達疏曰:“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后生次于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意思是生而又生,生生不已,是為變易。《系辭下》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疏:“以其常生萬物,故云大德。”是說天地恒常生出萬物,萬物生生不已,是乃天地的基本德性。周程諸人對“生”的高度重視,體現了對《周易》的深刻理解并強調了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體驗。在《二程遺書》卷三有著一些這樣的記載:“切脈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上述內容都體現了理學中人對天地生生不息精神的由衷贊嘆,對仁德的高度禮贊。陳榮捷先生說:“孔子以仁為全德,開新局面。孟子解為人心,亦即‘仁者人也’。仁的思想,于焉躍進一步。韓愈以漢儒說仁為愛之說,廣而博之,謂‘博愛之謂仁’,又進一步。及至二程,則臻乎高峰,即以仁為生理是也。”(陳榮捷《朱學論集》第77頁)當然,二程兄弟有如此認識,與周敦頤的言傳身教密不可分,“程顥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因茂叔(周敦頤)窗前草不除,有問顥。程子答云‘與自家思想一般’,即謂不肯斷絕生意。上引‘觀天地生物氣象’下有自注云‘周茂叔看’即指此也。”(同上書第77頁)第四句,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個“艮”字可了。《法華經》即《妙法蓮華經》,其強調出世(涅槃、佛性、圓滿)與入世(生死、煩惱、有漏)之間要保持一定的張力,認為只有這樣,人的精神狀態才能平靜、和諧和充實,像荷花出淤泥不染那樣不受煩惱等不良因素的侵襲。而《艮》卦作為《周易》第五十二卦,其主旨即為“靜止”,當為“山”之象征。《序卦傳》《雜卦傳》《象傳》皆有“艮”為“止”之說。《艮卦》上九爻辭曰:“敦艮,吉。”以多靜多止為吉利。而“主靜無欲”正是周子修養論的核心思想。《通書·圣學》說:“圣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就是說人首先要“靜”,這是成圣成賢的入手功夫,這也是“艮”字的奧義,正由于此“艮”字方能涵蓋一部《法華經》。顯然,周敦頤的人生態度與他的理論系統是一致的,都是對先秦儒學的的體認和發揮,勞先生所謂“而是一種名士或高士之生活。而此種生活情調,正道家人士或道教人士所具之情調”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總之,現實生活中的人都具有各種各樣的復雜性,表現出形形色色的生活樣態。但是,其中必然具有占主導地位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情調,這是應該首先應加以關注的。周敦頤是理學開山,是一位大儒,我們不能被一些枝節的現象所遮蔽,而將其視為一位道家或道教中人;或者將其兩分:思想為儒,生活為道。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濂溪先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生活中,都是以儒學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原則的,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1]周敦頤.周敦頤集[M].長沙:岳麓書社,2002.
[2]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5]陳榮捷.朱學論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6]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7]李方錄校.論語集解[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8]周敦頤.元公周先生濂溪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9]朱熹.朱熹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10]孟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1]徐儀明.理學家程顥及其詩[J].河南大學學報,1992,(5).
(責任編校:張京華)
B244.2
A
1673-2219(2010)10-0020-03
2010-06-27
徐儀明(1952-),男,江蘇蘇州人,哲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宋明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