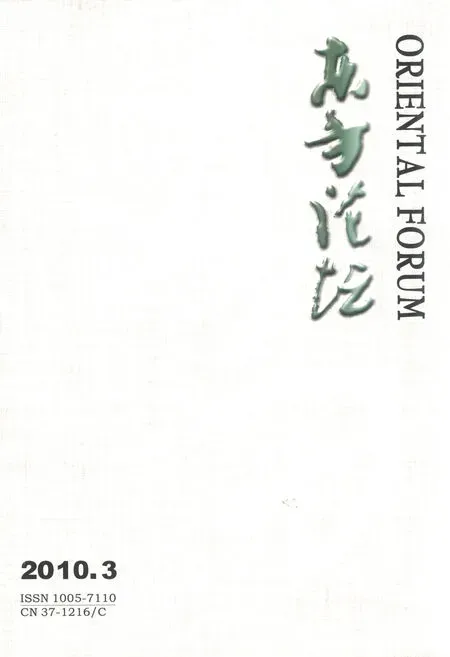論宗教與哲學的關系
單 純
(中國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70)
論宗教與哲學的關系
單 純
(中國政法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70)
宗教與哲學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兩種普遍表現形式。宗教的本質在于表達人類對于生命終極意義的追求,其方式多見于情感性的執著;哲學的本質在于表達人類對于世界的本原、思維的性質以及生活價值的探索,其方式多見于理性的反思。宗教信仰與哲學反思在方法論上的差異導致它們精神生活的客體表現出真實和虛幻的特征,但是它們在追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方法論上也相互影響。從中西方宗教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來看,哲學的思辨理性在宗教與哲學的相互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促使宗教傳統中人格神的意義向非人格神的人文主義觀念轉化,為世界多元性文明形態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奠定了客觀的思想基礎。
終極關懷;反思;天人合一;人文價值
一、宗教與哲學之異同
宗教通常被理解為“人與神的聯結”,神后來被解釋為“人格神”、“非人格神的靈性存在”或“終極實在”,而“聯結”歷史上曾被解釋為“信仰”,現在也可以理解為“體驗”,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理性論證”,如神正論者所做的那樣。但是在現代神學的層面,為適應各種經驗科學和理性思維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傳統宗教中的核心概念“神”不再被信仰成為“絕對外在的超越性”(或“絕對他在性”:the absolute otherness),①如幾個基本的“omni-”,這是來自拉丁文的一個前綴,意為“完全”,所表達的上帝特性有:omnipresence:無所不在;omniscience:無所不知;omnipotence: 無所不能;omnibenevolence:無所不善;后來有哲學家說上帝的這些“無限性質”都是緣于人的情感方面的“無限感知力”omnipercipience (羅德里克?費斯)。而是人主體性情感的最高表達,即蒂利希所定義的(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的表述”(the expression of the ultimate concern)。所謂“無限性”或“終極性”都是人類思維所賦予其對象的一種極限性的“形容特性”(attributes),反映了人類思維的理性邏輯和情感色彩。因此,在對于宗教的核心概念,無論從思維或情感的表述方面看,都與哲學的思維方法論和目的論相關聯。這就涉及到了哲學的問題。哲學在西方語境里是被當作“宇宙論或世界觀”、“知識論或方法論”及“目的論或人生觀”這“三論”的綜合,中國人也喜歡將此“三論”概括為“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學問”,因為將“世界觀”與“人生觀”表達成一種關聯性的“學問”,知識論自然也就包含在里面了。當然,用中國文化的傳統術語講“哲學”就是“尋根問底”和“安身立命”的合一。由于西方哲學出現了近代以來的“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哲學自然又被極為概括地總結為“對一切存在的反思”,這自然就包括對宗教的反思。這又從哲學方面涉及到了宗教的問題。因此,無論是討論宗教或哲學,都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宗教與哲學的關系問題。
宗教與哲學的關系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講:一是總括地講它們之間的異同;一是具體地講它們在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具體演變情況。
先講宗教與哲學之異。這種相異的一個最基本方面是其信仰或思考的對象的性質:宗教信仰的對象其性質多有信仰者所想象的成分或特質,甚至多半是幻象或扭曲的想象所致,其中滿足了信仰者的主體情感需要,如“義神”或“愛神”所具有的各種超越物理性質的“神跡”和表達倫理信息的“犧牲精神”。宗教所反映的世界基本上是經驗世界,只不過其在描述經驗世界時加進了許多缺乏或扭曲經驗世界真實性的成份,這即是宗教現象中常見到的“顛倒了的世界觀”或“幻象的反映”,即將經驗世界中的存在者幻想化或神圣化后再用以解釋經驗世界。這個反映的對象正與科學所反映的對象相等,但科學是真實地反映或實證經驗世界中的存在物,所以,宗教與科學在這方面的沖突要大于宗教與哲學之間的沖突。而哲學所反映的世界或其思維的客體是一種邏輯上的宇宙觀,即經驗世界加可能性世界,是中國古典哲學中的“至大無外”的存在者,是一種建構在思辨理性之上的邏輯本體,西哲亞里士多德名之以“反思的思想”,中國哲人則名之以“道”。作為一種思辨客體,與宗教的信仰客體一樣,它同樣也不同于“科學”的對象—作為實驗對象的存在者。“為道日損”和“為學日益”是中國人對哲學與科學之間在對象方面所做的區別,同樣也是哲學與宗教在對象上的區別。由于哲學的對象是邏輯的觀念,而不是經驗的事實,所以哲學與科學之間的沖突遠不像宗教與科學那樣明顯,甚至也可以說根本沒有沖突。中國儒家的經典《中庸》里有句話很好地解釋了哲學與科學并行不悖的觀點:“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這里的“大”是作為哲學對象的邏輯宇宙,即“要多大有多大”,“萬物”是科學的對象,“道”是哲學的對象,其不同的表現形式是“小德川流”和“大德敦化”,“德”是通假字“得”,表達“道”的具體表現形式,所謂“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管子?心術上》)因此在“道”的統領下,表現在萬物中的“德”和“大德”之“道”就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相比之下,在西哲柏拉圖的思想里,宇宙萬物的存在被分成“理世界”(world of ideas)和“經驗世界”(world of facts)兩個不同的部分,前者完美,后者拙劣,同樣亞里士多德也將科學與哲學分成“形而下學”(physics)和“形而上學”(metaphysics)之間的關系,它們也有邏輯上的前后、高低之分。之后西方基督教的教父哲學和經院哲學就延續了希臘哲人的這種二分理論,形象講就是“靈肉二分”,把“神靈”凌駕于“肉身”之上,自然也就把宗教凌駕于科學和哲學之上了。但實際上,哲學的宇宙觀是一種超驗的抽象概念,它并不直接否定宗教或科學的實在概念的價值,而是從一個永恒的方向引導和激發宗教觀念的演變和科學思想的創新。中國傳統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應該說很早就避免了類似的沖突或悖論,使中國思想史上沒有出現激烈的宗教神學與科學或哲學之間的尖銳對立和沖突。這是宗教與哲學是否能夠區別自己不同對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哲學這種與宗教和科學對象上的相異性可以在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中找到許多有趣的例證。當然,對于西方宗教核心的上帝概念的解釋——如“造物主”(creator)和“立法者”(law-giver),我們在西方思想發展的歷史中也可以發現其所受到的哲學的邏輯觀念的影響,如從“物理性質的犧牲”演變為“精神性質的祈禱”,從“先知的啟示”變成“因信稱義”,從“原罪的洗禮”變為“基督式的自我救贖”等等。
宗教與哲學另外一個相異性表現在其不同的方法論上。我們通常說“宗教在于信,哲學在于思”就是針對二者知識論或方法論的特性和意義方面說的。哲學注重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思辨;而宗教強調建立在體驗或幻想上的信仰,即哲學重“思辨”,宗教重“信仰”。這種方法論的差異也見于神學家們對宗教的獨特認識:即以信仰為主,以思辨為輔,其“‘以信仰為理解的基礎’(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精神,從亞力山大的克來蒙(Clement of Alexandria)提出,經過奧古斯丁(Augustine)闡釋而延續下來成為基督教知識分子的一種主要傳統,其意為:基督教知識分子所理解的往往是他們所信仰的東西,其特點是將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引入基督教的信仰傳統。到19世紀新加爾文運動興起之后,其基本精神已定型:即基督教知識分子的責任是以信仰主義的立場來探究知識問題,而不是離開信仰主義的神學傳統,即神性的簡單性原則或信仰主義的原則來思考一切學術、政治和社會問題。”[1](P122-123)但是,即便有哲學的理性因素,就方法論的意義講,以信仰為理解的基礎,則理解只能限于已經被信仰的客體,那當然就是加深對上帝的理解,其結果可能淪入“迷信”,即“信仰太甚必然窒息理解的主體性”。這是宗教信徒的精神生活中常見的危險。與之相比,哲學則是以“理解為本,以信仰為末”,是先理解了再信仰,其本質是強調人的理性主體意義,其結果可能完全排斥宗教式的信仰,即“理解太甚必然排斥信仰”。因此,從方法論講,哲學與宗教正好體現了它們之間的相異性,甚至是排斥性。這是西方文明中宗教與哲學關系所固有的特征,即權威教父哲學家德爾圖良(Tertullian)所謂的“雅典相異于耶路撒冷一如柏拉圖的學院相異于保羅的教堂”。但是,在中華文明體系里,宗教與哲學在方法論上并不是特別地相異,“天人合一”能夠將“尋根問底”與“安身立命”綜合成一個相融的命題,這與西方宗教“神人相分”和哲學“理世界與物世界相分”的特點確實不同。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在他的思想里,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前提就是理性,是獨立自主的思想,不過中國人認為理解源于“心”,所謂“心之官則思”,“心思”和“立命”即能將理解與信仰合成一個命題。西方人的哲學理性和宗教信仰在方法論上的區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完全可以是相容的命題,所以不少西方學者以及追隨他們的某些中國學者也都認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儒釋道三家既可以視為宗教亦可以視為哲學,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它們既非宗教亦非哲學。前者是看它們之間的相同之處,后者只看它們的相異之處。
二、“2H”與“天人合一”
如果說整個西方文明的傳統是一個“2H”統一的傳統,即“Hebrew religion”(希伯來人的宗教)和“Hellenistic philosophy”(希臘化時期的哲學),那么,它們的宇宙論都被基督教綜合成了一種設計論或機械論的宇宙觀。《圣經》開篇就講上帝“無中生有”地制造宇宙萬物,一如柏拉圖哲學將宇宙萬物解釋成絕對理念的“拙劣仿制品”(poor copies)和普羅提洛新柏拉圖主義中的“多”對于“一”的絕對依賴性,這樣,以上帝或者邏各斯所代表的“宇宙單元”或如萊布尼茲的“前定和諧”,就成了宇宙觀的核心和人生觀的價值追求,表達了哲學家所理解的生命的全部含義。照羅素的說法,“中世紀神學原是希臘才智的衍生物。《舊約》中的神是一位權能神,《新約》里的神也是個慈悲神;但是自亞里士多德,下至加爾文,神學家的神卻是有理智力量的神。”[2](P111-112)即偏于政治的“義神”、偏于倫理的“愛神”和偏于哲學的“理神”。可見,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對于“神”的理解表達的正是“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統一”,自然也表達出“2H”的統一。依我看來,從統一的立場講,猶太教時期的神可以稱為“義神”(以“上帝的選民”和“應許之地”所表達的哥們義氣的那種神,不夠真正宗教求善的涵義,所以斯賓諾莎稱其為“神學政治論”—這個新的哲學解釋給他自己惹來了殺生之禍),柏拉圖思想中的神就是“理念神”(the holy idea reflected universally in all poor copies,宇宙萬物皆神圣理念之拙劣衍生品),基督教的神是“愛神”(universal love:博愛成為三種民眾的必然選擇和精神追求:那些不為羅馬市民法—基督教形成之后才產生了萬民法—保護的千百倍于羅馬市民的帝國臣民,那些成千上萬的處于猶太教之外的“非上帝的選民”,那些屬于“一多關系”中的絕大多數在柏拉圖的宇宙論中以銅和鐵做成的農民和藝人),經院哲學的“理性論證之神”,斯賓諾莎的“宇宙萬物自然之神”,康德的“道德自由之神”以及佛洛伊德的“人類心理之神”,這些多元性質的“神”代表了多元和歷史發展的宇宙觀,同時也反映出相應的人生觀,即生命哲學。如果這個觀察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概括出神的三個基本特點就足以將“宇宙觀與人生觀統一”的哲學的奧義揭示出來。這三個特點分別是“造物的上帝”(creator)、“制定規律的上帝”(law-giver)和“救贖人類命運的上帝”(savior)。這三個特點在“二希”傳統中可以解釋哲學與宗教在思想上的相互補充關系,同時也很可以與中國哲學的特點相互借鑒和發明。中國學者傳統上都喜歡以司馬遷的人生哲學為自己學術使命的參照系,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報任安書》)如果按照范文瀾先生的說法,中國文化的傳統是一種“史官文化”,即“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漢書?藝文志》),則其哲學即為“春秋大義”,這是中國人生理想成為“義人”的標準,所以,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上》)作為中國“義人”或人生哲學典范的“圣人”的標準和前提都是宇宙論的—天,但它卻是與人生哲學和諧交融的,所以用不著特別地標志其為“絕對他在”或“超越性的理念”,中國人的宇宙論化生出萬物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生命情感,不是靠神跡和客觀規律。所以它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統一就被順理成章地解釋成為“天人合一”,人的生命的終極意義就自然地包含在宇宙論里,是“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周敦頤《通書?志學》)。
但是,我們從柏拉圖的“理世界”或基督教的“creator”、“law-giver”和“savior”里面很難找到類似中國天人和諧那種類型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統一性。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代表人的主體性的生命哲學往往要經過革命性的反叛才能被揭示出來,如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和克爾愷郭爾的“存在主義”,它們必須要將傳統世界觀中“絕對他在性”的神圣權威解構之后,才能確立人的主體性生命意義。由于西方傳統的宇宙論的超越性、客體性和絕對他在性,生命的主體性意義總是被抑制或蔑視的,這就使得強調主體性的思想特別受到推崇,如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康德的“自由意志”以及克爾愷郭爾的“真理就是人的主體性”(truth is subjectivity),不過,可悲的是,像克氏這樣具有開風氣之先的存在主義大師仍然不敢說這是自己的獨立見解,而是將它追溯到拿生命去喚醒人們主體自覺的蘇格拉底:“對于克爾凱郭爾而言,‘外在地在那兒’的只是‘一個客觀的不確定性。’無論他對柏拉圖的批評是什么,他的確從蘇格拉底對無知的斷言中找到了這種真理概念的一個好例子。因此,他說:‘因而蘇格拉底的無知正是這一原則的表達,即永恒真理是與存在著的個體相關的,而蘇格拉底始終以他個人經驗的全部熱情持有這一信念。’”①Socrates to Sartre:A History of Philosophy, Samuel Enoch Stumpf, printed by McGraw-Hill, Inc.1993, P.486.在西方這種機械論和設計論的宇宙觀下面,宗教徒的生命意義是信仰上帝,愛上帝,最終等待上帝的救贖,而哲學家的意義則是認識上帝所制定的規律,按照認識到的客觀規律而理性與自由的生活。這兩者形式上確實有些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都在“神人對立”或“客主對立”關系中來確立主體的人的有限意義。這一特點,即便我們拿“近代哲學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philosophy)笛卡爾的箴言“我思,故我在”來分析也是這樣。從表面上看,“我思”是在確立主體的人的獨立思想地位,但是實際上,他只是在拿“思考客觀真理”與“感官經驗的客觀真理”作比較,以見理性的思想比感性的直覺更容易獲得客觀真理,而我的思想的對象本身仍然是一個以外在的上帝為代表的絕對客觀真理:“我們理解為至上完滿的、我們不能領會其中有任何包含著什么缺點或對完滿性有限制的東西的那種實體就叫做上帝(Dieu)”,[3](P162)因此“在上帝的觀念里,不僅包含著可能的存在性,而且還包含著絕對必然的存在性。因為,僅僅從這一點,他們絕對用不著推理就可以認識到上帝存在。”[3](P164)既然上帝已經作為一個無限完滿的客觀真理而存在,“我思”的結果無論如何是不能超越它的,充其量只能無限地接近它,因為它是“我思”的最高標準和思考者的最終人生目標。正因為如此,西方人所能給予笛卡爾的最高贊譽也只是說他是一個“二元論”者,上帝的那一元是絕對不能動搖的,而笛卡爾這一元只是史無前例地肯定了“我思”的主體性地位,但其存在仍然以不削弱上帝作為絕對真理和思考的終極的標準那一元為前提。
三、宗教與哲學的人文價值
無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如何相異,宗教與哲學都有人生論的共同議題。大體上說,宗教方面所體現的人生論的議題是“天國”的外在救贖,即上帝的末日審判;而哲學的人生論的議題則是人的主體意識的充分實現,即人的全面自由。這類議題正好反映出了宗教與哲學各具特色的人文價值。
大體上講,哲學從一個永恒的角度來看待一切存在物的發展、演變,這是由它的“反思的思想”所具有的無限靈活性所決定的;而宗教也似乎是從一個“永恒”的角度看待“一切存在物”的演變,但它所謂的“永恒”和“一切存在物”都是在對經驗世界中的存在物作幻想的類比而形成的,如以“天國”折射“人世”,以“永生”折射“長壽”,以“地獄”折射“苦難”等。而在哲學的最高概念中只有超驗的“理念”、“物自體”或“絕對精神”等。但是,在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領域里,我們又可以看到宗教與哲學相同的一面,即兩者都十分關注諸如生與死的意義、善與惡、美與丑、秩序與自由等。對于這些共同的方面,盡管哲學對它們的解釋有思與信的差別,但它們對人類所提供的“安身立命”的功用卻是相同的。
馮友蘭先生在美國大學講《中國哲學簡史》開篇的第一句話就說:“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歷來可以與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4](P1)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他又給哲學下定義說:“我所說的哲學,就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4](P4)“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于實際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現在引用它,只是要標明,中國哲學傳統里有為學、為道的區別。為學的目的就是我所說的增加積極的知識,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說的提高心靈的境界。哲學屬于為道的范疇”[4](P8)他在這里是參照西方思想所做的解釋,西方的宗教本來的功能是“為道”的,即所謂“哲學(科學)求真,宗教求善,藝術求美”中給宗教所確定的功能,現代美元上的標記“我們信賴上帝”(In God We Trust)就是將宗教信仰視為其社會生活的價值基礎:“關于美國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在美國人自己的概念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他們和許多非基督徒都認為,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猶太-基督教道德”,“從某種意義上說,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①《交流》,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編譯2000年第1期第29頁。僅從宗教的倫理功能來看,它應該與日益的、積極知識的科學傳統不相干,而是與日損的、提高精神境界的哲學相互關聯。可是,在西方的中世紀,宗教則沒有恪守好自己的職責,經常犯規,侵襲哲學和科學的領地,甚至凌駕于它們之上,將科學和哲學視為自己的“婢女”和“仆人”。啟蒙運動之后,這種“思想犯規”的情況已經得到很大糾正,當時激發西方人糾正宗教思想“犯規”的重要啟示就是來自于中國的思想傳統,即天和人不是主人和奴仆,絕對他在和受造存在,神圣客體與世俗主體之間的對立關系,而是合一的相容關系。這一點給了西方的啟蒙運動新的“人本主義”啟發:中國人的心可以是知識的本體,也可以是信仰的本體,理性與情感,理解與信仰可以由人的心得到統一;中國儒家所提倡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給了西方近代哲人深刻的啟示,使他們從“道成肉身”和“因信稱義”的宗教觀念中轉化出新的人文信息,這些信息很多都被運于解釋主體性的自我救贖和世俗性的天賦人權。
因此,根據中西思想的同異比較,我們大體上還是可以說:宗教與哲學的異同關系可以總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它們涉及的領域有“大小”之別;一是它們進入自己領域的思想方法有“思”與“信”之異。宗教的領域一般不超出人類的經驗世界,而哲學的領域往往在經驗世界之外還有可能性世界,在經驗世界之內,古今中外一切的宗教現象也是哲學思考的領域之一部分,而哲學的可能性世界則不在宗教建立信仰的領域里。在思想方法上,宗教要求其信徒對最高的神圣存在者,無論是人格性的上帝還是絕對靈性存在,都呈獻不假思索的虔誠。而哲學對宗教所謂最高存在者一定要訴諸理性之思考:最高存在的證據何在?如何證明此證據的可信性?最高存在的本質定義與經驗事實有無邏輯矛盾,如神之全善與人世之惡當作何解釋?這些出自思想的問題都是哲學反思的對象,哲學家們視其為生活的樂趣。這是它們從宇宙觀與知識論的關聯中所轉化出來的人生價值觀或人文價值取向。
在東方的文化傳統中,宗教與哲學的關系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其特點是兩者之間的若即若離,界限模糊。
我們知道,作為印度婆羅門教最早的經典之一的《奧義書》(Upanishads)既可以看成是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教義基礎也可以看成是它們在哲學方面的基礎。它是印度最古老的《吠陀》(Veda,形成于公元前2000-1000年之間)經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所宣傳的“梵我同一”和“輪回解脫”等概念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而其對于物質存在的原素論的解釋和對社會倫理的樂生論的解釋,又是具有哲學方面的人文主義意蘊的。因此,《奧義書》既是古印度的宗教經典又是其哲學經典。特別是在公元前后,在《奧義書》的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印度教正統的哲學流派“吠檀多派”(Vedanta)。
佛教的傳統也可以分成哲學和宗教兩個相互交融的層面:作為宗教的佛教和作為哲學的佛學。佛教的創始人悉達多?喬答摩(Siddhartha Gautama)或稱釋迦牟尼(Sakyamuni)本人展現出來的乃是其哲學思想,倒是后人把他的思想和探索人生意義的行為改造成了宗教中的教義和奇跡故事。此后,作為宗教傳統的佛教在南亞、東南亞、中國西藏、中國內陸、朝鮮、日本等地得到傳播,其特點是強調修煉、戒律、出家及廟堂等形式,也是其宗教傳統中人文價值的表現形式。而作為哲學傳統的佛學也在印度、中國、日本等地得到傳播并在歷史上形成了大乘佛學(Mahayana),龍樹(Nagarjuna)創立的中觀派(Madhyamika),在中國、日本和美國西海岸的禪宗等,這些新宗派在創新方法論的同時也揭示出了獨特的人生論的意義。
中國儒家的傳統也是這樣。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本來也是繼承中華民族古老的文化傳統其中包括宗教中的神話傳說、巫術思想等而形成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既有屬于他自己創新的、具有哲學意味的仁義道德思想,也有古老的文化傳統中沿襲下來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命鬼神思想。在這個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體系里,《中庸》中的天賦人性論、孟子的“養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宋明理學家致良知的修養功夫②研究中國宗教思想的學者認為,宋明儒家在修煉方式上具有濃烈的宗教色彩。所謂“理學家的修養工夫,無論主誠主敬主靜主寡欲主返觀內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禱面目。因此,我們認為這也是一種宗教思想的表現。”見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康有為的“孔教”運動、錢穆用火珠林法卜“國運”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敬天祭祖”的傳統,都是在表達儒家思想在宗教層面的人文含義了,所謂“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當然,儒家傳統也有明顯的哲學層面的意蘊,如孔子強調人世倫理的“仁”、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朱熹以“理氣”關系解釋事物的存在、馮友蘭以“理、氣、大全、道體”建構“新理學”的思想等。這些都與西方傳統的哲學具有相同的理性思辨旨趣。不同的是,儒家的傳統強調“天人合一”,總是將這個傳統的宗教性和哲學性意蘊融合在一起,沒有造成明顯的互相沖突和緊張關系,而是在哲學的思辨理性中貫徹了人生論的意義。我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中國哲學具有西方宗教所強調的“終極關懷”或中國語境下的“安身立命”的功能。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以“人生境界論”為其主要特征,就是中國哲學傳統在當代轉化的一個顯例。
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更強調宗教與哲學之間的界限與沖突;宗教的啟示性不斷受到哲學的思辨性挑戰,在思想方法上來自希臘哲學的思辨特征主導著整個宗教神學思想的發展方向。其結果是導致宗教的“外在啟示性”向“內在體驗性”轉化,這種轉化不僅表現為宗教自身的演變,也反映出了其中不斷被強化的人文價值取向,所謂“道德宗教”,“人道宗教”,“解放神學”和“上帝之死派”等等,都可以視為人文價值觀對傳統宗教救贖論的深刻影響力。
我們知道,西方宗教傳統從其源頭開始,就突出信仰的啟示特色,以與哲學從其源頭開始的思辨特色相區別。在形成于公元前7-6世紀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圣書《阿維斯塔》(Avesta)、猶太教(Judaism)的律法書《托拉》(Torah)、基督教(Christianity)的“上帝之道”(Word of God)以及伊斯蘭教(Islam)的《古蘭經》(Qur’an)中,充滿大量神的啟示的信息。可以說,在西方宗教的古典時期,其主要思想特色是啟示性的。但到了中世紀以后,希臘哲學的思辨性特色開始影響這一宗教傳統,基督教神學的思想中心轉向了思辨方面,其人文主義特色在希臘哲學的刺激之下逐漸顯露出來,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時形成高潮。
雖然基督教在最初的時期仍帶有希伯來(the Hebrew)人的宗教在啟示方面留給它的影響,但很快就轉向了希臘哲學的理性思辨傳統。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神學在奧古斯丁時代形成一個高潮,而其特點是柏拉圖式的思辨性。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全盛時期,基督教神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則轉向亞里士多德并以其思辨方法建構自己的神學體系。自近代以降,基督教新教神學家施萊爾馬赫(F.D.E. Schleiermacher)和基督教加爾文派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又明顯表現出康德(Immanuel Kant)哲學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接下來卻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神學家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過程哲學對過程神學運動的影響。從基督教的發展方向看,哲學的思辨性在對宗教信仰的“理解”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其結果是培育出了宗教自身的人文主義精神,所以蒂利希才可能在當代的思想環境下給宗教下一個具有人文主義價值取向的宗教定義—“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的表述”。
在伊斯蘭教的發展方面,自穆罕默德之后有兩個趨向:一是受柏拉圖影響的蘇非派(Sufis);一是受亞里士多德影響的伊本?路西德派(ibn Rushd)。然而,這兩派都是深受古典希臘哲學思想影響而形成的,其中的人文價值取向經過拜占庭帝國崩潰后傳播到西歐社會,對那里的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盡管西方的宗教特別是其神學思想傳統一直在接受哲學方面的思辨性影響,但其哲學傳統卻很少受到宗教啟示性特征的影響。中世紀神學在哲學思辨性傳統的影響下居于西方思想傳統的主流地位,以致于哲學本身淡出思想領域,成了神學的婢女。可是,自從笛卡爾(RenéDescartes)建立近代哲學以來,哲學則完全又恢復了古希臘哲學的思想活力并脫離了宗教神學的束縛,更加迅猛地發展出枝繁葉茂的諸多新流派。特別是經過康德和黑格爾(G.W.F. Hegel)的洗禮,20世紀的哲學開始全面清算宗教神學在西方傳統中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形成于對希臘哲學傳統的曲解和篡改。在這期間,誕生了排斥宗教傳統的、無神論的邏輯實證主義和否定上帝絕對存在的以人為核心的存在主義,最精彩的是薩特(Jean-Paul Sartre)對上帝的宣判:“我給大家講一個天大的笑話:上帝根本不存在!”[5](P141)存在主義發展了自啟蒙運動以來哲學對神學的否定傳統,薩特則在承認人的存在高于一切、提倡人的獨立意識和與生俱來的絕對自由的前提下,把宗教傳統中那個外在而超越的上帝完全否定了。自那以后,在西方宗教與哲學的關系中,根本的問題不是哲學在面臨新問題時回到宗教思想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宗教若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維系其信眾對神或終極實在的信仰,不得不借鑒哲學的方法并協調自己與哲學在發展方向上的關系。也就是說,西方文化傳統在啟蒙運動之后所呈現的宗教發展趨勢是哲學化的、人道化的。總體上講,人文主義最終形成了近代西方宗教和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個主流性議題。
[1] 單純.當代西方宗教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M].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 (法)笛長爾.第一哲學沉思集[M].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4]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5] 薩特.魔鬼與慈善的上帝(英文版)[M].紐約:蘭登出版公司,1960.
責任編輯:郭泮溪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SHAN Chun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70, China)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re two universal expressions of hum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Religion in its essence is to express the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uman life while philosophy in its essence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rigin, the nature of thinking and the value of life. The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n seeking answers to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so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erms of methodologies. As far as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s are concerned, the speculative reason of philosophy hold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ultimate care; reflecti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umanistic value
B91
A
1005-7110(2010)03-0001-06
2010-05-10
單純(1956-),男,浙江紹興人,哲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