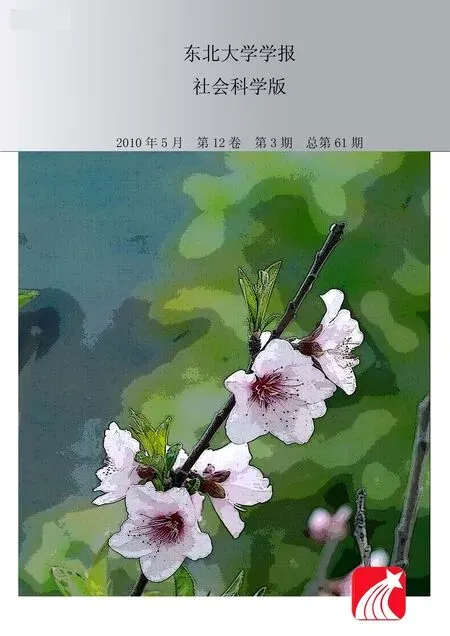試論言語社區的層次性
李現樂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 210093)
作為社會語言學的重要概念之一,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近幾年來受到語言學界的較多關注。言語社區是語言學的首要研究對象和語言調查的基本單位[1]。同時,言語社區也是言語行為的存在場,人類活動的必需空間,正如錢冠連先生所說:“人活在語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語言中”[2]。言語社區對人類社會生活如此重要,關于言語社區及其相關問題的討論和紛爭自然不足為奇。
一、 言語社區及其構成要素
關于言語社區的概念,語言學界存在很多爭議。自20世紀30年代布龍菲爾德開始,諸多語言學者對“言語社區”進行了多角度的界定。例如,布龍菲爾德認為,一個言語社區就是“依靠言語相互交往的一群人”[3]45。萊昂斯認為,言語社區是“使用某一特定語言(或方言)的全體人員”[4]579。霍凱特認為,言語社區是“通過共同的語言能直接和間接地彼此進行交往的一整群人”[5]。甘柏茲認為,言語社區(言語共同體)是“憑借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進行經常的有規則的交流,并依據語言運用上有實義的分歧而區別于同類集團的人類集合體”[6]36。拉波夫認為,對不同語言行為的共同評價及由此形成的共同規范是言語社區必不可少的部分:“言語社區并不是根據語言因素使用過程中任何明顯的一致性,而是根據一套共有規范來界定的”[7]。海姆斯認為,言語社區“把所要描述的單元假定為一個社會的而非語言的實體。首先將它看做一個社會群體,然后考慮到存在于這個群體內的一整套語言手段”[8]47;“一個言語社區成員不僅知道某種語言,而且還知道如何使用這種語言”[8]123。
對于言語社區概念界定的復雜性,郝德森認為,“有可能,言語社區除了作為人們心理內部的原型之外,實際不存在于社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對‘言語社區’‘真正’定義的探求,只不過是一件徒勞之舉”[9]。沃德華也認為像定義語言、方言一樣,定義言語社區也是困難的[10]146。關于言語社區的概念之爭,不是本文討論的主旨,本文不作過多闡釋。付義榮對此有較為詳細的綜述[11]。
徐大明總結言語社區理論時指出:“總結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確定,社區是第一位的,語言是第二位的。語言產生于社區之中。一個言語社區不一定就對應著一種語言;但是頻繁的言語互動的結果往往是產生和保持一種語言變體的基本條件。因此,歷史悠久的言語社區一般都擁有一個標志性的語言。與此同時,穩定的雙語社區也普遍存在。”[1]言語社區具有人口、地域、互動、認同、設施五個要素[1]。總體上看,我們比較贊同這一觀點。
除了對言語社區概念的討論之外,關于言語社區的構成要素的討論,近來也受到語言學界的關注。例如,楊曉黎認為,確定一個言語社區,須要具備三個基本元素:可以大體圈定的區域、相對穩定而適量的人群、由區域群體成員共同認可并使用的語言變體[12]。周明強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地域、人口、設施、互動和認同五要素,這五要素既與社區有聯系,又與語言有聯系,表現出極強的復雜性,具有一定的辯證關系[13]。夏歷以在京農民工言語社區為例,指出“言語社區的范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地域層面,可將精神層面的言語社區納入到言語社區研究的范疇里”[14];王玲以合肥科學島社區為例,指出“言語社區五要素在社區中所處的作用雖然不同,但缺一不可,認同是五要素中最重要的一個鑒定要素,它是言語社區最終形成的重要標志”[15]。
本文在有關言語社區概念及其構成要素的討論基礎上,透過言語社區的內部層次性特征來嘗試探討言語社區的內部結構系統,同時就言語社區基本構成要素問題略陳管見。
二、 言語社區層次性的已有相關論述
言語社區是多層次的社區。語言學界學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多有提及。早在20世紀30年代,布龍菲爾德在《語言論》中對此就有所論述。盡管布氏“以語定區”,但也注意到言語社團的大小有懸殊,言語社團內部存在差異。他認為:
在一個言語社團中,交際密度的差別不止是個人和個體的差別,而且一個社團還分成各式各樣的小社團體系,小社團里的人彼此交談的次數,大大地超過了跟小社團以外的人交談的次數[3]51。
而言語社團內部的差異,“有地方性的----僅僅由于地理上的分隔----也有非地方性的,或者像我們通常所說,社會性的”[3]51。關于復雜言語社團里的主要言語類型,布龍菲爾德認為,大致可以分以下幾種:書面標準語、口頭標準語、地方標準語、次標準語和地方方言。此外,他還指出:
我們對言語社團內部的差別所做的綜合觀察告訴我們,一個言語社團的成員可能說話非常相似,誰都聽得懂誰的話,也可能差別很大,住得略遠的人就彼此聽不懂[3]57。
關于聽懂和聽不懂,布龍菲爾德認為:
在這兩種情況之間我們的確劃不出一條界線,因為在聽得懂和聽不懂之間是有許多過渡階段的。美國人和約克郡人彼此能否聽得懂,可能決定于兩人智力的高低,或者有無接觸別的方言或語言的經驗,或者愿不愿意細聽對方的話,或者當時的環境是否很容易使對方了解語義,如此等等。此外,在地區言語和標準言語之間的差別,還有無數等級;兩個人或其中的一個都可能作某些讓步,以便雙方了解,這些讓步一般是向標準語靠攏。[3]57
從上述布氏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布龍菲爾德存在“以語定區”的問題,但是他關于言語社區內部的差異性的論述以及交際密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言語社區的層次性問題,只是沒有作明確的概念闡釋而已。布氏所論述的由于交際密度的不同,一個大的言語社區內產生了一些小的言語社區,正是言語社區層次性的重要表現之一。布氏關于一個言語社區內部成員有聽不懂和聽得懂的不同情況的論述,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11]。而布氏所論的言語社區內部成員有聽不懂和聽得懂的不同情況,并非是影響交際的核心因素。這正如上文所述,聽得懂和聽不懂之間是“有許多過渡階段的”(這也體現了布氏所說的交際密度問題),更何況聽不懂的原因并非完全是語言本身問題,而更多的是外在因素。因而,聽不懂和聽得懂在整體上并不影響一個大的言語社區的存在。
甘柏茲在《言語共同體》一文中也就言語社區(即 “言語共同體”)的層次性作過一定程度的闡釋。他說:
在同一言語共同體里,并非所有成員均等地掌握全套流行的超方言變體,個人所掌握的交際手段明顯地隨著他在這個社會內的地位而變。活動范圍越狹窄,他所處的社會環境里語言越單一,他所需要的語言表達能力就越小。因此,家庭婦女、農夫、勞工這些很少同外界接觸的人,只要掌握有限的語體就可湊合,而演員、演說家、商人掌握的語體最多。這種個人間的差別無論在多語社會里或單語社會里均存在。[6]42
布氏看到了言語社區內部的差異性,認為交際密度的不同造成了小的社區體系的存在,但是未能就內部層次性作進一步的明確闡釋。而甘柏茲注意到了超方言變體的掌握與個人在言語社區中的地位有關聯。活動范圍的寬與窄,正是在大的言語社區下的不同亞社區里的活動與交際,這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言語社區的層次性。
言語社區的層次性并非表現為一個大言語社區下的在同一平面上的一些小社區的簡單排列。其層次性更體現在內部不同層級的亞社區或小社區存在著的嵌套或包含關系。這一觀點在安娜和帕拉迪等人的言語社區的四個區域模型的論述中得到了較為明確的闡釋。他們在研究墨西哥巴霍地區言語社區的基礎上提出了嵌入性言語社區模型的概念。根據被人瞧不起的語言變量、特定地區語言變量和標準語言變量,他們將言語社區分為四個層次,即言語場、言語鄰近地區、言語區和全國言語社區。言語場成員不能區分被人瞧不起的語言變量的等級;言語鄰近地區的成員用被人瞧不起的語言變量來評價言語,但是沒有意識到言語變量的地區模式;言語區的成員意識到地區言語變體,他們沒有意識到標準語言變體,在語言使用中使用更為寬泛的語言變體形式;全國言語社區的成員意識到語言標準變體,在語言使用上不愿意使用地方語言變體。[16]
從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語社區結構的表述中我們看到了言語社區的較為明顯的層次性特征,其中由最里層區域到最外層言語社區區域,是一個層級性、漸變性的結構。相對于先前的關于言語社區層次性的論述,安娜和帕拉迪等人的言語社區理論較為明確地論述了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點,這是言語社區層次性研究的一大進步。而較為系統地從言語社區理論角度闡述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點則是出現在近期的言語社區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中。
三、 從構成要素看言語社區的層次性
從上述關于言語社區的概念、構成要素及層次性的論述中,我們也得到一些啟發。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點也可以從言語社區的基本構成要素中窺見。言語社區理論的系統闡述者徐大明先生認為,人口、地域、互動、認同、設施是言語社區的基本構成要素[1]。根據“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1],言語社區的基本構成要素可以分為兩大方面,即社會性要素和語言性要素。社會性要素主要體現在人口和地域方面;語言性要素則更多地體現在認同、互動和設施方面。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征。
作為言語社區的主體,人口是構成言語社區的基礎性要素。言語社區與社會學的社區都需要有聚集在一起的人口。沒有聚集在一個地區的人口就不能構成言語社區[13]。人口所具有的流動性特點決定了以人口為基礎的言語社區必然處在多層次上。因為人口的流動帶來了交際范圍的不斷擴大,這正是從一個小的、低層次的言語社區逐步走向大的、高層次的言語社區的過程。這里的交際范圍的擴大,一定程度上是以語言為載體的交際范圍的擴大。另一方面,人口素質的層級性差異也為言語社區的層次性分布創造了可能。如不同文化層次、家庭背景、社會經歷的人口,形成不同的言語社區。夏歷對農民工言語社區的調查表明,從進城務工前后語言能力的對比上看,農民工在使用普通話的交流能力、發音和運用情況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農民工因進京務工其語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普通話水平整體有了提升,語言使用也和從前大不相同,已完全不同于務工之前在家鄉時以地域為界所歸屬的言語社區,有形成一個新言語社區的潛質”[17]。當然,這是一個對變化的、歷時的言語社區的考察。但由此可推知的是,共時層面上的不同語言能力、文化背景的人口等也同樣具有形成不同層次言語社區的可能。
伴隨人口要素的是地域要素。作為社會性特征的地域,是人類包括語言交際在內的各種活動的場所,其本身的地域性、層次性分布也為言語社區的層次性提供了可能。如政治上的區域劃分、地理上的區域分布,為大小不等的言語社區在地域上的層次性分布提供了條件。當然,這也給同一層面上的不同言語社區的排列提供了條件。如葛燕紅對南京“小姐”稱呼語的使用調查,與其他地區的調查作了比較:
唐師瑤(2005)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東北人并不常用“小姐”這個稱呼語;盧驕杰等(2005)的調查中發現,在山西太原,很少有人稱年輕女性為“小姐”;在山西忻州,幾乎沒有人隨便稱年輕女性為“小姐”。章建華(2001)指出,在閩粵地區,“小姐”和“小妹”這兩個稱呼語涇渭分明,在歌廳等場合若稱“小妹”為“小姐”,被稱呼的女性會認為是一種污蔑,至少是一種誤會。[18]
而南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葛燕紅的調查結果是:
有92.4%的調查對象都會使用“小姐”來稱呼陌生的年輕女性,只有7.6%的人不使用“小姐”這一稱呼語。而且,“小姐”稱呼語在南京市的各種不同場合都有人使用,在商場、酒店、餐館、歌舞廳和問路等場合下,“小姐”都是人們稱呼女性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稱呼語。這和我們第一階段觀察的結果也基本一致。所以,總體來看,“小姐”是目前南京市民對陌生年輕女性這類交際對象的最主要稱呼語。[18]
通過對比發現,不同言語社區中稱呼語“小姐”的使用差異,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地域上的差異。由此可知,地域的不同及其層次性分布是言語社區的層次性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大明的研究也很好地證明了地域層次性與言語社區層次性問題[19]。通過對比包頭昆都侖區1987年和2003—2004年的兩次調查數據,以及與北京1981年鼻韻尾調查數據的對比,徐文指出,言語社區內部理想的一致性和同質性很難實現,現實中具有的是表現在統計結果上的相對一致性,而相對一致性表現出很強的有序性;一致性的等級是按照“同一時間地點”—“不同時間同一地點”—“不同地點”有序排列的;徐文認為,“這些現象顯示的是北方話鼻韻尾變異的擴散機制和擴散軌跡,也體現了言語社區的層級性”[19]。其層級性依次是:“昆都侖本地出生人口構成的社區”—“包括移民人口的昆都侖社區”—“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一個時間段的昆都侖社區”—“包括該時間段的不同地點的北方話大言語社區”。隨著層次的升高,變異模式的一致性逐漸降低,但高層次上仍有其一致性,即在高層次上仍為一個言語社區。“時間和空間的差距往往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但是這只不過說明了言語社區的多層嵌套的結構。”[19]
言語社區的語言性基本構成要素,即互動、認同和設施,同樣體現出了一定的層級性特點,這為言語社區層級性的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類似于布龍菲爾德 “交際密度”的概念,互動是言語社區的核心構成要素之一,它主要是指言語的交際互動。言語社區是言語互動的場所[1]。離開互動,言語社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布氏的交際密度存在疏密問題,互動自然也有其程度的問題,即存在層次性。而互動和認同緊密相聯,互動的強弱直接影響到認同的程度。孫德平對南京大學小百合虛擬社區的調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在“小百合”這個虛擬社區,影響成員對網絡語言認同的因素是網齡和每周在小百合上發/回帖的次數。“小百合成員”網齡越長、每周發/回帖次數越多,就越認同網絡語言;反之,就越認同規范的現代漢語。網齡長短,反映出網民在虛擬社區生活時間的長短: 網齡越長,說明其在虛擬社區生活的時間越長,相應地,其在虛擬社區中互動也就會越多。而發/回帖正是成員在虛擬社區中的互動表現: 發/回帖次數越多,說明成員在虛擬社區互動越頻繁;互動越頻繁,也就說明其越認同網絡語言。由此,我們進一步得出結論:社區成員的互動度是影響其語言認同的重要因素。[20]
可見,不同的參與程度是不同互動的表現,由此形成了在該社區里的不同的語言態度和語言行為,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認同。(這里主要是對網絡語言的認同,而身份的認同也在孫德平的調查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如在調查小百合成員使用網絡語言的原因時,作者發現,占33.77%的成員認為使用網絡語言“能得到認同、易被接納”;而另有16.88%的成員認為“不會讓人覺得是菜鳥”。)盡管孫德平的調查不是專門針對本文所談論的認同和互動的層次性對言語社區層次性的影響問題,但我們完全可以推知,由于互動的程度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語言態度和語言行為,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語言認同和身份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形成不同級次的言語社區。
關于認同在言語社區中的作用,沃德華援引了布朗和列文森對“群體”相對性的論述:“生活在劍橋的人,當與紐馬克特對比時,在地域上將認同于劍橋;與蘭開夏郡相比,認同于劍橋郡;與蘇格蘭對比時,認同于英格蘭;與德國對比時,則認同英國,以此類推”。沃德華認為,“群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言語社區”也必定是相對的[10]152。沃德華指出:
在特定場合下,當X和Y在同一層面有鮮明對比時,你認同X而不是認同Y,因此你就是某個言語社區的成員。這種觀點暗示有英語社區(是因為有法語和德語社區)、得克薩斯言語社區(因為有倫敦社區和波士頓社區)、哈佛言語社區(因為有牛津社區和伯克利社區),有奇卡諾言語社區(因為有英語和西班牙語社區)等等。因此,個人可以同時屬于不同的言語社區,但是在特定場合只能認同于其中的一種,特定的認同取決于環境中什么是最重要或對比性最強的。[10]152
可見,認同具有一定的層次性,言語社區也具有一定的層次性;在不同層次上的認同對于不同層次的言語社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為言語社區的另一語言性基本構成要素,設施不僅包括語言這一社區所共有的財產,還包括有關的語言權威機構,語言的典籍、成文的標準、輿論的壓力等[1]。自然,語言的各個不同層次上的變體與變異形式都應是言語社區共有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這些不同層次上的變體與變異形式的運用,也正是構成不同形式、不同級別和層次的言語社區的重要因素。這類似于上文中的安娜和帕拉迪的言語社區的四個區域模型。但是我們也不能僅以類似于被人瞧不起的語言變量、特定地區語言變量和標準語言變量的標準來劃分不同級次的言語社區,否則有以語定區之嫌。語言及語言變體的使用是劃定言語社區的重要因素,但非首要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言語社區特別是高層次的言語社區未必是單語或單方言的社區。另一方面,語言規范、成文標準等方面的層次性也是確切存在的。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言語社區一般有各自規模,適合各自需要的規范、標準等,只不過有些規范標準不是顯現的而已。
關于言語社區語言變體和言語社區的層次性問題,仍可以徐大明對包頭鼻韻尾變異研究為例[19]。在對北方話鼻韻尾變異的對比分析基礎上,文章指出,言語社區內部的一致性是相對的和多層次的,一致性是言語社區的存在條件,在某些方面的不一致性恰恰是言語社區層次性的體現[19]。而這些“體現了言語社區的層級性”的正是不同層次上的鼻韻尾變異。
四、 結 語
根據言語社區理論“社區第一,語言第二”原則,言語社區是相對的概念[11],其內部結構,既有嵌套式的,也有同一層級上的排列形式。言語社區的層次性主要表現在社區中人口、地域的范圍、規模、交際的密度、互動的程度及語言變體、設施規范等方面的層次性。從層次上看,言語社區未必是單語的,雙語的社區可能是更高層次的言語社區。不同層次上的言語社區,其語言及語言變體的使用是不同的。通過對言語社區層次性的分析,我們更加明確了構成言語社區的五個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同時,我們對言語社區的層次性有了更為清晰的把握。對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征的進一步認識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把握言語社區的內部結構系統。
以上簡要回顧了關于言語社區層次性的論述,并從言語社區的五個基本構成要素方面分析了言語社區的層次性特征。言語社區理論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理論。言語社區是實證語言學的一個核心概念[4]573。然而,目前關于言語社區層次性的研究還不充分,學界尚未展開針對言語社區層次性問題的實證性研究。言語社區理論須要在更充分、更系統、更深入的實證性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
參考文獻:
[1]徐大明. 言語社區理論[J].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4(1):18-28.
[2]錢冠連. 語言:人類最后的家園[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23.
[3]布龍菲爾德. 語言論[M]. 袁家驊,趙世開,甘世福, 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4]Patrick P L. The Speech Community[M]∥Chambers J K,Trudgill P, Schilling-Estes 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5]霍凱特. 現代語言學教程[M]. 葉蜚聲,索振羽, 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8.
[6]甘柏茲. 言語共同體[M]∥祝畹瑾. 社會語言學譯文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7]徐大明. 語言變異與變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42.
[8]Hymes D H.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9]郝德森. 社會語言學[M].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35.
[10]沃德華. 社會語言學引論[M]. 雷紅波,譯. 5版.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11]付義榮. 試論言語社區的界定[J].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6(2):150-163.
[12]楊曉黎. 關于“言語社區”構成基本要素的思考[J]. 學術界, 2006(5):82-86.
[13]周明強. 言語社區構成要素的特點與辯證關系[J]. 浙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7(5):59-64.
[14]夏歷. “言語社區”理論的新思考----以在京農民工言語社區共同體為例[J].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9(5):86-90.
[15]王玲. 言語社區基本要素的關系和作用----以合肥科學島社區為例[J].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9(5):80-85.
[16]張紅艷,張邁曾. 言語社區理論綜述[J].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5(1):1-8.
[17]夏歷. 農民工言語社區探索研究[J]. 語言文字應用, 2007(1):94-101.
[18]葛燕紅. 南京市“小姐”稱呼語的調查分析[J].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5(2):196-207.
[19]徐大明. 語言的變異性與言語社區的一致性[J].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8(5):78-86.
[20]孫德平. 虛擬社區成員對網絡語言的態度:南京大學BBS個案研究[J]. 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6(2):125-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