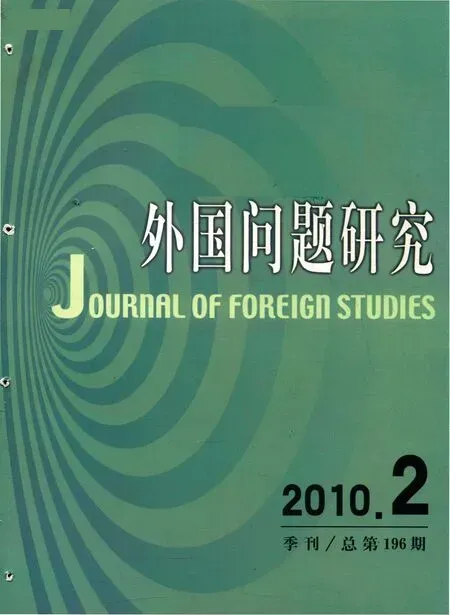神秘介質(zhì)與吉本芭娜娜的小說風(fēng)格
劉旸
(東北師范大學(xué)日本研究所,吉林長(zhǎng)春130024)
一
《月影》、《哀愁的預(yù)感》、《甘露》分別代表著吉本對(duì)神秘的三種不同的詮釋方法。《月影》貼近古代神話傳說,人物設(shè)置、情節(jié)架設(shè)都可以輕易地找到相應(yīng)的古典神話故事原型。《哀愁的預(yù)感》重在營(yíng)造神秘氛圍、制造懸念,引人入勝。《甘露》則是超能力者的集中展現(xiàn),擁有超能力的人物接連登場(chǎng),是一場(chǎng)神秘世界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較量。
神話傳說總是與神秘有著不解之緣,遠(yuǎn)古時(shí)代的先人以這種離奇曲折的方式對(duì)人類起源、各種自然現(xiàn)象做出解釋。“如果說巫術(shù)是對(duì)在自然中一種巨大而微妙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常常以令人恐懼的形式出現(xiàn))的安撫的話,神話則是人們?cè)诳謶种鲗?duì)世界何以如此的一種探索與解釋。”[1]神話傳說作為后世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形式的母胎,其許多方面的藝術(shù)價(jià)值是無限的,吉本芭娜娜的《月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古代流傳的神話傳說的影子。
《月影》是吉本芭娜娜在日本大學(xué)的畢業(yè)作品,也是吉本初登文壇的處女作。處女作反應(yīng)的是作家最初創(chuàng)作時(shí)期的精神狀態(tài)、寫作能力、藝術(shù)追求,這些作品也許不夠成熟、不夠深刻、不夠完整,但它非常重要,它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原點(diǎn),對(duì)于吉本《月影》正是這樣的作品。《月影》中包含了日后吉本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大多數(shù)主題。
早月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戀人阿等,在同一場(chǎng)事故中,阿等的弟弟柊也失去了女朋友惠理子,早月與柊兩個(gè)人彼此支持從悲傷中重新站立起來。某日清晨當(dāng)早月靠在橋邊正準(zhǔn)備喝茶時(shí),突然出現(xiàn)一位神秘女子。年齡不詳,三月的早晨卻“似乎沒有絲毫寒意”,“白色外套”等一系列描寫淡化了這個(gè)神秘女子的真實(shí)存在感,仿佛來自另一個(gè)虛無縹緲的世界。浦羅是引領(lǐng)早月走出困境的重要人物,在浦羅的神情中,早月看到了在其他人臉上從未見到過的沉重的神色,這種內(nèi)在的悲傷與早月產(chǎn)生了共鳴,也得到了早月的信任。幾天以后,早月按照約定的日子來到橋邊,與浦羅一起見證了“七夕現(xiàn)象”這一神奇的時(shí)刻。在日本古代傳說中,橋更多地被用來在人與鬼、生與死之間建立聯(lián)系或形成過渡與中介,在以橋?yàn)橹黝}的故事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橋姬的傳說,在《古今和歌集》、《平家物語》中均有記載。橋姬是指守護(hù)橋的女神,在眾多版本的橋姬傳說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宇治橋的橋姬,相傳是被丈夫拋棄的女子跳入宇治川化身的女鬼。在早月眼中,仿佛無意中幻化成人形的鬼魂、沒有存在感的浦羅猶如橋姬的化身,是與異界交流的媒介,也具有統(tǒng)御異界的能力。
阿等的弟弟阿柊也與早月共有著同樣的悲傷,柊是一個(gè)古怪的人,“就像是生長(zhǎng)在異度空間”,小說中第一次登場(chǎng)穿著水兵服。水兵服是由美子的遺物,自從由美子死后,阿柊一直穿著這身水兵服上學(xué)。一方面,阿柊的女裝中和了他男性的這一性別,與早月之間建立了一種超越性別的精神關(guān)系,另一方面,阿柊的水兵服也是他的“羽衣”。在日本各地都流傳著關(guān)于羽衣的傳說,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竹取物語》輝夜姬披上羽衣,告別塵世、飛天而去的故事。失去由美子以后,阿柊借由這身水兵服變身,似乎變成另外一個(gè)存在,仿佛到一個(gè)可以與由美子溝通的世界,小說最后由美子取走這身衣服,阿柊最終告別了過去,告別了由美子,重新做回原來的自己。
《月影》講述的是一個(gè)失去以后,如何繼續(xù)的故事,記錄了主人公走出悲傷的心理過程。吉本芭娜娜將古代傳說中的主題元素插入字里行間,以魔幻的方式治療著這些年輕人的傷痛。這些古代的發(fā)想并沒有脫離日常生活,被主人公自然地接受,看似不經(jīng)意,其實(shí)蘊(yùn)含著無限的暖意。
二
吉本隆明認(rèn)為:“這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由始至終所散發(fā)出來的不安定的氣息[2]157”。吉本芭娜娜自己也說,這篇小說很“與眾不同”[2]150。的確,以解謎為故事主線的小說結(jié)構(gòu),與《廚房》、《泡沫/圣域》等作品直接明了的故事情節(jié)大為不同。
《哀愁的預(yù)感》是一部深沉神秘,中間摻雜著溫馨與甜蜜的小說。故事從一座老房子開始,孤零零佇立在粗獷森林中的老式宅院里,爬山虎覆滿墻壁,地板上積滿灰塵,斷了絲的燈光從未換過,儼然就是恐怖片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鬼屋”。少女彌生的阿姨雪野一個(gè)人獨(dú)自居住在這座古老的房子里,她像沉睡了似地悄悄地生活著,這里仿佛是一個(gè)不存在時(shí)間的世界。彌生和這個(gè)阿姨沒有太深的交往,卻對(duì)她頗有好感,雨夜離家出走,會(huì)將目標(biāo)鎖定在阿姨家,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小學(xué)時(shí)曾經(jīng)和阿姨共度過的片刻時(shí)光,對(duì)彌生來說總有一種“神神秘秘的感覺”。這位離群索居的阿姨特立獨(dú)行,習(xí)慣躲避人們的關(guān)注,在彌生眼里她生活得很“古怪”,她的生活、她的過去像謎一樣神秘,沒有人了解。作家不僅沒有在這里交代彌生失去的記憶是什么,為什么會(huì)失去,以表面的這種空缺制造迷霧,而且隨著故事的發(fā)展,又設(shè)置了一個(gè)更大的懸念。
彌生是一個(gè)預(yù)感很強(qiáng)的女孩,憑介頭腦里依稀閃現(xiàn)的幻影,她直覺“別的地方還有和我血脈相連的親人”,這句話的出現(xiàn),使小說的情節(jié)變得更加不可思議。彌生決定出門去尋找自己遺忘的過去,逐漸發(fā)現(xiàn)阿姨原來就是自己的親姐姐,彌生印證了自己的“預(yù)感”,雪野也供認(rèn)不諱。但就在第二天,雪野卻憑空消失了。接下來的敘述中謎團(tuán)更是一個(gè)接一個(gè)的出現(xiàn),姐姐不斷地設(shè)謎,妹妹不停地去解開謎題、尋找答案。每解開一個(gè),姐姐就會(huì)給妹妹一些“獎(jiǎng)勵(lì)”與新的啟示。彌生揣測(cè)著姐姐的心思,找到當(dāng)年一家人住過的親戚家的別墅,果然發(fā)現(xiàn)姐姐的蹤跡。在那里,她得到了意外的驚喜——她遇上了姐姐的情人,并從他口中獲悉姐姐的感情生活。
在兩人的交流中,舊日生活中的種種不和諧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彌生也逐漸體會(huì)到姐姐心底的焦慮和沉重。同時(shí),她還開啟了自己的愛情之門。一切之后,彌生和雪野分別回到當(dāng)年父母發(fā)生意外的地點(diǎn),兩人再次相遇,相視一笑,發(fā)現(xiàn)原來當(dāng)初父母選擇的旅行地點(diǎn)也是如此荒涼怪異,完全是一片不可思議的景象,她們和曾經(jīng)的自己、曾經(jīng)的生活重新接連起關(guān)系,人生在新的愛、新的生活中繼續(xù)下去。
三
吉本芭娜娜自己曾經(jīng)這樣談?wù)撨^《甘露》的主題:“我想描寫另一個(gè)世界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想描寫神秘精神與新生代精神在現(xiàn)實(shí)中的挫敗,想描寫破裂家庭的重組,還想描寫手足之情。想描寫像三島由紀(jì)夫的《美麗的星星》那樣嚴(yán)肅瘋狂的家庭。這些全部包含在里面了。”[3]35作者解釋了小說中多重的主題,不難看出神秘、新時(shí)代的挫敗是《甘露》中突顯的中心,在意識(shí)水平上,作者肯定了超越自然的神秘存在,對(duì)脫離生活的超現(xiàn)實(shí)世界也并非全盤否定。
故事主人公朔美在一次意外中從樓梯滾落下來,因頭部受重創(chuàng)而失去部分記憶。失去記憶的朔美對(duì)自己和周圍的人與事都產(chǎn)生了疏離的感覺,曾經(jīng)熟悉的一切變得陌生。她的思想游離于現(xiàn)實(shí)之外,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她存在意識(shí)模糊,她是“死了一半”的人,這種狀態(tài)將她帶到現(xiàn)實(shí)世界與神秘世界之間的邊緣位置。朔美的弟弟由男,是一個(gè)擁有特殊能力的小學(xué)生,他能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能預(yù)感到很多事情的發(fā)生,他還可以生靈游走到朔美的夢(mèng)里,由男帶領(lǐng)朔美向神秘世界一步一步靠近,也正是由于自己身邊有這樣一位親人,朔美才得以窺見神秘世界的種種現(xiàn)象。由男年齡很小,他并沒有因?yàn)樘熨x異稟而感到快樂興奮,這種能力一直折磨著他幼小的心靈,超常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使他迷茫、不知所措,而且隨著超能力的日漸發(fā)展他愈發(fā)苦惱煩悶,與朔美在一起體會(huì)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樂趣,使由男放棄發(fā)揮超能力的念頭更加強(qiáng)烈,他決定努力回歸到平凡而踏實(shí)的生活。
朔美為梳理心情、找回記憶,與戀人龍一郎去塞班島旅行,塞班島是一個(gè)神秘的靈異世界,這里留下了無數(shù)在二戰(zhàn)中陣亡的戰(zhàn)士靈魂。在塞班島朔美結(jié)識(shí)了兩位奇異人物——花娘和古清,更多地體驗(yàn)了種種超自然的神秘現(xiàn)象。古清是一個(gè)白化病人,與由男一樣能夠聽到神秘的聲音,具有預(yù)知未來的異能;花娘是古清的妻子,也有一種特殊力量——她能夠與亡靈交流。這對(duì)夫妻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都有過噩夢(mèng)般的悲慘體驗(yàn),迫使他們逃避現(xiàn)實(shí),并最終筑成超越現(xiàn)實(shí)的精神世界,他們是超現(xiàn)實(shí)的存在,而聚集了無數(shù)靈魂的塞班島就是“神秘世界”的象征。他們擁有的超能力并不能改變?cè)谌毡镜默F(xiàn)實(shí)生活,于是帶著沉重的失敗感離開日本,正如吉本芭娜娜自己所說,這是“神秘精神與新生代精神在現(xiàn)實(shí)中的失敗”。
塞班島回來,朔美因?yàn)槟硞€(gè)契機(jī)開始恢復(fù)失去的記憶,在“新舊”兩個(gè)朔美融合的過程中,她又一次遇到了兩位特殊人物——寬面條和梅麥斯,又是一對(duì)超能力者,寬面條能夠消除人的痛感、透視箱里子里的東西,甚至可以根據(jù)失蹤者或死者的東西,找出各種相關(guān)信息,幫助警察破案。梅麥斯的特長(zhǎng)是催眠術(shù),在朔美即將找回自己重返現(xiàn)實(shí)生活時(shí),來自神秘世界的信息又一次向朔美襲來,朔美再度面臨著超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誘惑。《甘露》想要表達(dá)的是人們對(duì)于自我難以掌控的超能力、神秘現(xiàn)象的態(tài)度[4]。也正如木股知史對(duì)“甘露”這一題目的解釋那樣:“在這篇小說中,甘露并不是高貴、神秘、特別的圣水,而是咕嘟咕嘟地喝水這種日復(fù)一日地平凡生活的象征。神秘的力量并不是存在于遙不可及的靈異世界,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5]
四
神秘文化從某一側(cè)面反映了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對(duì)自然界的認(rèn)知程度。遠(yuǎn)古的祖先認(rèn)為風(fēng)雨雷電神秘可怕,今天的我們?cè)缫阎溃L(fēng)不過是空氣流動(dòng)的結(jié)果,雨也只是海水蒸發(fā)遇到冷空氣凝結(jié)的產(chǎn)物,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自然現(xiàn)象。隨著科學(xué)的發(fā)展,曾經(jīng)的不解之謎、離奇現(xiàn)象逐一揭開神秘的面紗,人們已學(xué)會(huì)用理性的思考、科學(xué)的方法去認(rèn)識(shí)、把握那些不可思議的現(xiàn)象。當(dāng)然,面對(duì)浩瀚的宇宙,人類是渺小的,作為宇宙中極其有限的生物,在思考、探索宇宙時(shí)依然面臨巨大的困難,宇宙以它的無限性依舊保持著其一貫的神秘感。實(shí)際上,在當(dāng)代社會(huì),神秘主義的存在已經(jīng)成為人們內(nèi)心的需求與心靈的寄托,神秘是人們出自感情的、對(duì)世界的詩意想象,展現(xiàn)出人類心靈的豐富、溫柔和深刻。
解讀吉本芭娜娜的小說,“神秘”是一個(gè)關(guān)鍵詞。她在創(chuàng)作中結(jié)合了后現(xiàn)代小說虛構(gòu)亦真實(shí)的特點(diǎn),也借助了后現(xiàn)代小說家經(jīng)常使用的病態(tài)人物形象,以女性特有的詩化感受注入大量的神秘元素,在表現(xiàn)超現(xiàn)實(shí)的同時(shí)也展示了人們可能面臨的種種精神障礙和肉體缺陷。她筆下的超現(xiàn)實(shí)、超自然,從不會(huì)獨(dú)立于現(xiàn)實(shí)之外,也絕不是作為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對(duì)立面而存在,她的神秘世界總是與現(xiàn)實(shí)交織在一起,隱藏著現(xiàn)實(shí)的因素。
吉本芭娜娜小說中流露出的神秘氣息、頻繁出現(xiàn)的神秘現(xiàn)象,與她本人對(duì)神秘世界的濃厚興趣有極大關(guān)聯(lián)。吉本在她的個(gè)人自選集《神秘》集的后記中曾經(jīng)提到過:“我從兒時(shí)起就整天莫名其妙地想象這個(gè)世界的神秘,其中也包括對(duì)各種神秘現(xiàn)象的思考。”[6]而且,在一次訪談中,被問及如果殺人會(huì)采取什么方式時(shí),吉本的回答是:“詛咒或棍棒。”[3]26可見,在吉本的意識(shí)中,詛咒與棍棒具有同等的傷害能力。吉本芭娜娜這種對(duì)神秘世界的關(guān)注,是在個(gè)人經(jīng)歷、傳統(tǒng)文化、當(dāng)代社會(huì)的變化等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
吉本幼兒時(shí)幻有單眼弱視,為了鍛煉病眼,父親吉本隆明經(jīng)常讓她用眼帶故意蒙住正常的另一只眼睛,治病的過程,大半的時(shí)間都在黑暗中度過,然而視覺的障礙卻刺激了其他感官的發(fā)展,這種與眾不同的經(jīng)歷培養(yǎng)了吉本豐富的想象力和異常敏銳的五官感覺。幼年時(shí)代的特殊經(jīng)歷,逐漸培養(yǎng)起吉本芭娜娜對(duì)神秘領(lǐng)域的興趣,這種興趣一直影響著吉本對(duì)其他事物的好惡選擇。吉本十分熱愛恐怖小說和電影,這也許與恐怖情節(jié)的神秘詭異以及其中經(jīng)常有幽靈和鬼魂出沒有關(guān)。吉本芭娜娜喜歡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說,鐘愛意大利導(dǎo)演達(dá)里歐阿基多(Dario Argento)的懸疑電影,兩位大師作品中對(duì)世界的感覺與吉本芭娜娜不謀而合,迎合了吉本對(duì)超現(xiàn)實(shí)的興趣,也為吉本的神秘寫作增添了色彩。
“如今的日本在精神方面正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在經(jīng)濟(jì)上雖已成為經(jīng)濟(jì)大國,但在精神上就如同一個(gè)內(nèi)容空虛的稻草人。”[7]精神的空虛,使人們?cè)谏鐣?huì)現(xiàn)實(shí)面前無能為力,把希望寄托于虛無,關(guān)注起超自然、超人類的東西,于是,七十年代開始掀起了一場(chǎng)神秘主義文化的熱潮。與神秘主義思潮相對(duì)應(yīng),則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率從過去的遞減轉(zhuǎn)為增勢(shì)。許多人崇尚命運(yùn),把前途和未來歸結(jié)于神秘力量的必然驅(qū)使,求助所謂預(yù)測(cè)未來命運(yùn)的載體。神秘主義的回潮成為新新宗教生長(zhǎng)的土壤,新新宗教“以肯定人的靈性存在作為教義的主體,以開發(fā)提升人的靈能作為教法的力點(diǎn),非理性的靈術(shù)側(cè)面突出。幾乎所有教主都利用人們崇尚權(quán)威的心理來神化自己,自稱具有神賜能力的資質(zhì);重視產(chǎn)生神秘體驗(yàn)和奇跡的靈術(shù),實(shí)施以教主和靈能者為媒介的靈能救濟(jì),靈修學(xué)已成為新新宗教研習(xí)的一個(gè)重點(diǎn),盛行在恍惚朦朧狀態(tài)下開發(fā)靈能與神通力的神秘行為。”[8]新新宗教的崛起并不是一種孤立現(xiàn)象,同時(shí)包括巫術(shù)內(nèi)容的增多以及更加個(gè)人主義的新靈性運(yùn)動(dòng),新新宗教反映了日本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個(gè)人化與個(gè)人主義化傾向,對(duì)靈性和神秘感的探究,往往成為一些日本現(xiàn)代青年追求自我的蹊徑。
[1]毛峰.神秘主義詩學(xu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57—58.
[2][日]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M].東京:株式會(huì)社ロッキング·オン,1997.
[3][日]吉本ばなな.B級(jí)BANANA[M].東京:角川書店,1995.
[4][日]近藤裕子.満ち欠ける時(shí)間[J].國文學(xué)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4(3):128-132.
[5][日]木股知史.吉本ばななイエローページ[M].東京:荒地出版社,1999:181.
[6][日]吉本ばなな.吉本ばなな自選選集(1)Occultオカルト[M].東京:新潮社,2000.641-642.
[7][日]源了圓著.郭連友,漆紅譯.日本文化與日本人性格的形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198.
[8]張大柘.論日本新興宗教及其在社會(huì)變遷中的應(yīng)對(duì)[J].日本學(xué)刊,2002(5):8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