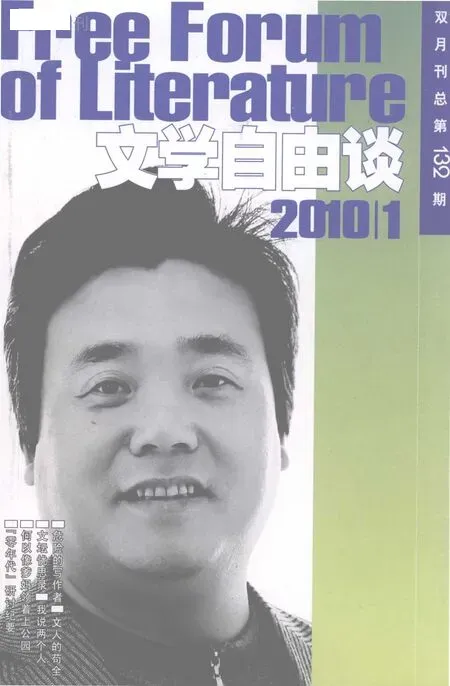分類法發凡
●文 陳 沖
三年前給《文學自由談》寫過一篇小稿,題目叫《把貓頭鷹和夜鶯分開》。近三年來,那篇小稿里的看法,一再受到現實生活的嚴懲,那感覺,直如一記又一記巴掌,火辣辣扇在我的臉上,然后是有人提著我的耳朵教訓道:貓頭鷹和夜鶯都在天上飛,都在樹上停,都可能感染H5N1病毒,它們都是鳥,所以它們是同一種東西!
我確實因此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軟弱和無能為力。我受到的傳統教育太少,而洋化的教育又太多。那么我應該怎么辦呢?七十三歲了,改造思想,再來一次“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實事求是地說,真是來不及了。所以,想來想去,還是就用這花崗巖腦袋,再發一次很對不起祖宗的狂話吧——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所造就的中國式思維,有一個很不好的特點,就是非常喜歡分等,卻很不擅長分類。
沒辦法,從小受的就是這種教育。我不知道現在中學里的課程是怎樣設置的,我上初中的時候,一年級講“動物”課,二年級講“植物”課。12歲的我,坐在初一教室里,聽頭一堂動物課,講的是貓。對貓的第一個理解,是這種動物屬于“脊椎動物門、哺乳綱、食肉目、貓科”。然后,老師沒有直接講貓,卻講了分類——為什么貓科里包括老虎,卻不包括狗;為什么犬科里包括狼,卻不包括貓。“先入為主”吧,這種思維從12歲一直伴隨我、主宰我到現在,雖然我明明知道貓和狗都是家養動物,都能在寵物市場買到而都不能在動物園的籠子里看到,老虎和狼都是野生動物,都不能在寵物市場買到而都能在動物園的籠子里看到,但我仍然認為貓和虎同屬貓科動物,而狗和狼同屬犬科動物。
為什么要這樣分?老師說,動物學的分類,是按動物的“解剖學特征”分類。
好吧,我也給自己找一塊堅實的地方,讓自己能站得更穩當些。這樣一種分類的原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里是有根據可循的;那根據是一個很堅硬的概念,叫“質的規定性”。哲學的任務是認識世界,這個任務只能由人來完成,所以就有了一個很“彎彎繞”的說法,叫“自然界通過人類來認識自己”。說這話的人沒想到的是,人跟人不一樣,所以認識的途徑和結果也不一樣。同樣是認識世界,道家講“大象無形”,易家靠八八六十四卦,“百家講壇”喜歡講這個,講來講去,世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混沌,能聽明白的,是幾個人一起走路,要讓領導走在中間之類。不過,遇到“矛盾”,就要對立統一,向對立面轉化,比如發生了火災,就要改為“讓領導先走”了。這種根據需要可以方便地做出變通的思維方式,天然地排斥“質的規定性”,因為它太剛性。所以,幾千年來,中國世世代代的聰明人,都在前仆后繼地與這個招人討厭的東西做斗爭。舉例來說,幾千年來,中國的天文學都是和“預測學”混在一起的,因為兩者都要“觀天象”。歷史在記述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時,為了彰顯他在天文學方面的高深學養,說在他死去多年之后,他的墓被盜掘,縣官接到報案前來勘察案發現場,只見那墓里有一隨葬木牌,上刻六個字:“盜墓者李準也。”把李準抓來一審,果然供認不諱。端的“料事如神”,死后多年誰來盜他的墓,他都能預先知道,那么他親眼所見的種種天象,你盡管放心相信。這樣一種既悠久又優秀的傳統,直到元朝才被郭守敬一度打破,但也只是“一度”而已。他死后不久,他領銜創制的新歷法“授時歷”被廢止,他創制的天文觀測儀器被毀壞,他的觀測資料和研究成果被封存,他自己雖然還算長壽,卻史稱“后世不可考”。“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他連自己的兒子都沒保住。相比之下,那位告訴我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孔丘先生,卻恩澤綿延以迄于今,某某是他的第七十四代孫,某某是他的第七十六代后人,包括某某、某某目前正在美國發展等等,仍不時見諸報端也。
向馬克思敬個禮很容易,接受“質的規定性”很難。
“服務”和“管理”,原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各有各的目的、對象、方法、評價標準,兩者各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相互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對立關系,而我們的有些人偏要先把它們對立起來,然后再引入“對立統一”,讓它們各自向對立面轉化,于是就出現了“管理式的服務”,和“服務式的管理”,于是乎“大象無形”,讓人如墜五里霧中,橫豎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從后果倒推它的動機,似乎又很簡單,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經常會遇到“管理式的服務”,而大款們則時而就能享受到“服務式的管理”。把分類加以混淆,就為分等的操作打開了方便之門。
現在我們要說到文學了。“文學”作為一個概念,有它確定的內涵和外延,也就是“質的規定性”。這和“文學”作為一個詞語不“同一”。“文學”作為一個詞語,可以、實際上也經常被加上各種各樣的副詞,而加了副詞以后的“××文學”,是否還是原來意義上的那個文學,或是它的一部分,那就要看它是否還具有原來那個“質的規定性”。通常所說的“報告文學”、“軍事文學”之類,都是“文學”的一部分,而廣告文學、暴力文學就跟“文學”毫不搭界。“社會主義文學”是對文學的一種政治分類,或者說是按政治分類的幾種文學中的一種,不是說“資本主義文學”就不是文學了。同樣道理,“小說”作為一個文學概念,也有它確定的內涵和外延,有它的“質的規定性”,這其中就包括著它的精神價值取向和審美態度,并不是只要有人物有故事就是小說——當然是指作為“文學”項下按樣式分類中幾種樣式之一的小說。而當小說作為一個詞語被使用時,它也經常被加上各種各樣的副詞,而加了副詞以后的“××小說”,是否還是原來意義上的小說,或者說是否還是“文學”的一部分,同樣要看那個“質的規定性”。早先有一種“春宮小說”,即便你給那個副詞換上一個更具裝飾性的說法,它與文學也搭不上界。又或者,即便你會玩一套文字雜耍,加一個具有等級性、排他性的副詞,把你那個玩意叫作“最小說”,如果里面只是一些精神價值取向市儈化的人物和故事,那它根本就不是小說,只是某種小市民讀物。
然而,我不能不承認,現實生活的走向與我的理念大相徑庭。實證之一,就是所謂的“文學三大塊”的理論,正在或已經成為某種半官方的理念,正在或已經成為制訂工作計劃的依據,甚至已在實施。“半官方”也者,是因為以我的理解,作家協會無論名義上還是實際上,確實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官方機構。至于他們為什么偏要去做他們做不好的事,去管他們管不了也管不著的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在我的理念中,文學就是文學這一塊,沒有別的“塊”。作家協會存在的六十年里,除了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出現過向左的偏斜,在對文學的質的規定性的認知上,并沒有出現過大的岐議。有段時間,它確實“引入”了一些偽文學,但是當我們對那個時期的文學進行歷史梳理時,這種偽文學的存在仍然可以而且應該被視為文學現象的一部分,有它的特定的文學史意義,正如我上次說到偽歷史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或許真是這世界變化快,忽然之間,文學就有了“三大塊”,給人的感覺,似乎是部隊在裁軍,文學卻在擴軍,大路兩廂豎起了招軍旗,愿來吃糧領餉的,按個手印,當場就能領到兩個饅頭一碗糨粥。我真是不明白,這是在干什么?
被擴招進來的那兩大塊,究竟應該怎樣表述,我也真是說不好。有一陣,我確實想當然地以為,其中是把通常所說的“通俗文學”包括在內的。在我看來,這還真是個問題,至少,對于是否應該把通俗文學也算作文學的一種,我自己就長時間猶豫不決,迄今仍無定見。我想,當年中國的評論家們紛紛把赫爾曼·沃克的《戰爭風云》稱譽為“史詩式的作品”,直至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并論,那只是表明這部分中國文學評論家在分類方面的低能,無損于沃克先生是一位有特點、有功力的美國通俗小說作家。我們為沃克未能順利獲準加入美國筆會而抱打不平,則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美國筆會的性質,誤以為它就是美國的作家協會。無論如何,在通俗小說這個巨大的金字塔的頂部,確有一些作品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沒有人能把日本的社會推理小說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筆抹煞。舉例來說,《人性的證明》所達到的人性深度,肯定超過了我們目前某些以“挖掘人性”為標榜、實則只是在把玩某些淺薄欲望的小說。可話說回來,這些又畢竟只是金字塔的塔尖。這種數量上的低比例,在質的規定性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但我很快發現,本次擴招與此無關。所謂“三大塊”里的第二大塊,按我的分類法,是那種連通俗文學中低層次作品都趕不上的、只能叫“通俗讀物”出版物。這里所說的“趕不上”,是從文學價值上來說的,有點兒拿量杯量西瓜的意思,而西瓜本來是應該論斤秤的。論斤秤的時候,它們自會有各自的重量,并且由此決定了它們存在的理由和價值。當然,若要確切,還得加上一條,就是當它們被上秤秤時,是連包裝一塊兒秤的。如果某個西瓜的外面裹了一層厚厚的鉛箔,鉛箔外面再涂上花花綠綠的礦物顏料,完全有可能賣個比普通西瓜高一萬倍的好價錢。所以我就替作家協會犯開了愁:當作家協會的小賣部里也開始出售這種西瓜時,您確定您準能給這種西瓜合理地定價嗎?
而且,這一大塊的現狀,似乎也并不像三大塊論者所說的那么欣欣向榮或生機勃勃。那里的空氣正在和已經被普遍泛濫的抄襲、剽竊所毒化。聽一位對此做過具體調查的女評論家介紹,抄襲、剽竊已經成了那里的常態,而給我的印象,似乎那些寫手們的電腦根本就不配置鍵盤,他們的操作僅限于用鼠標反復點擊“復制”和“粘貼”。所以我又犯開了愁:當這些鼠標操作手們紛紛成為作協會員之后,“文學”將自立于何地?
還有另一大塊,那個所謂的網絡文學。網絡文學不能用量杯量,也不能論斤秤,它的計量單位是點擊率,且在實際操作中用的又不是“率”而是“次”。網絡上那些被稱為“網絡文學”的文字,從數量上說,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自娛自樂的文字,但“網絡作家”卻是個職業化程度遠遠高于“專業作家”的人群。他們憑“點擊率”掙錢,有些人收入頗豐,但卻很不穩定,很沒有保障。那是個非常喜新厭舊的領域,除極少數例外(兩岸四地加起來也屈指可數),多數“網絡作家”的鼎盛期都不長,有的甚至超不過一兩年,一旦點擊率降到“門檻”以下,就等于失業,而且領不到失業救濟。我聽說過有些作家協會正在鄭重其事地吸收“網絡作家”入會,但沒聽說過在這些會員失業了、改行了以后,協會準備怎么辦。這個作家走紅,那個作家被冷落,連他們自己的“圈內人士”都說不清原因何在。同一個網絡作家,從躥紅到過氣,點擊率從幾十萬陡降到幾千,相距僅僅咫尺之遙、轉眼之間,若是看他的作品質量,即使以他們的標準衡量,也沒有任何明顯的變化。一句話,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游戲規則,并且正按、也只按他們的規則游戲。我真是想象不上來,他們怎么能跟文學玩得到一塊兒?
但是,這種荒誕的“合并”,確實掩蓋了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正是由于文學刊物方面的原因,使一些有志于文學的青年作者,不得不以網絡作為他們邁進文學門檻的通道。雖然那是一條很繞遠的羊腸小道,成功的機會也并不多,但畢竟是一種機會。如果真關心他們,那么要做的首先是檢討我們自己為什么要這樣地把守著金光大道,而把他們擠到羊腸小道上去。然而我聽到的卻是“招安”,是敦促他們“向主流文學轉型”。好一個“向主流轉型”!正是在這一塊揭去了麒麟皮的地方,無意間露出了馬腳——所有以混淆分類開始的鬧劇,總是以最終的分等告終。
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有其自身的“質的規定性”。其中之一,就是它高貴的品格。不是穿什么牌子的西裝、拿什么牌子的手袋那種高貴。是靈魂與精神價值取向的高貴。是不是真高貴是一回事,要不要高貴是另一回事。至少,我們不能因為有人批評某些作家的故作高貴(這其實原是正確的批評),就放棄對高貴的追求。如果一個人連精神的高貴和靈魂的卑賤都區分不開,卻要來侈談文學,我愿意建議他免開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