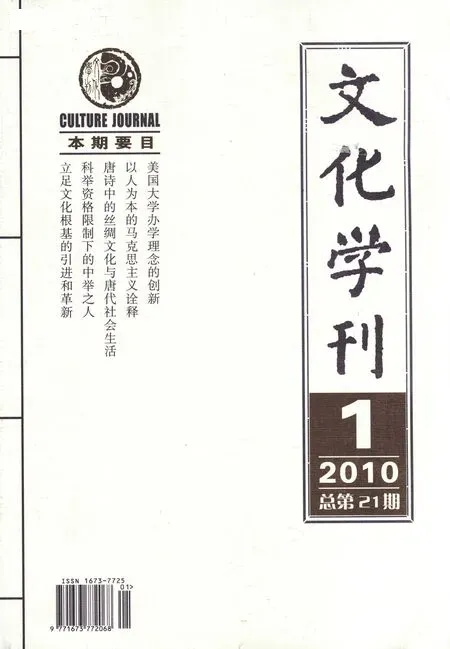唐詩中的絲綢文化與唐代社會生活
劉佳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 100871)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文化的鼎盛時期,尤其是以絢麗的絲綢織造為代表的紡織業的高度發展,極大地豐富了唐代人的社會文化生活。透過唐詩這種具有極高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文學形式,今人可以復見當年的繁盛景象。唐代詩人筆下的絲織品,多側面地反映出了絲綢文化的發達和紡織業的發展對唐代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影響。
一、唐詩中的唐代桑蠶紡織業的發展與唐代經濟社會生活
唐代歷經“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兩大盛世,手工業在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其中,絲綢織造方面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取得了空前進步。唐代紡織業除了設有以少府監下的織染署為代表的官營機構外,也有大量民間從事絲綢生產的手工作坊和個體農婦,另外還有一種官府控制、散點生產的織造戶。在關心社會現狀和人民生活的唐代詩人眼中,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同時反映了底層婦女遭遇的廣大織婦,以及有著超群技藝卻遭受不公待遇的紡織精英——織造戶,這二者成為了關注的焦點。唐詩中的大量織婦詩與織錦詩都反映了絲綢紡織業的進步和絢爛的成果背后從事紡織業的人民的疾苦。
唐代詩歌從多個角度描繪了織婦們創造出的光輝業績,也從側面上反映出了唐代紡織技術的進步。首先是繅織機具——繅車的發明和普及。唐代以前不見有繅車的名稱,而在唐詩中卻多次出現相關記載,如王建《田家行》:“五月雖熱麥風清,檐頭索索繅車鳴”,陸龜蒙《奉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次韻》:“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繅車”,從中可見,以輪子轉動繅絲的手搖繅車業已發明,這一唐代人的首創使唐代的繅絲技術大大提高。而從李白《贈清漳明府侄聿》:“繅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之中可以看到,這一新工藝自發明后由北向南迅速普及,成為普遍運用的生產工具,為唐代絲織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礎。[1]
唐代絲織業的技術進步,還體現在絲織品種類的豐富和紋飾的創新上。緯線表里換層顯花技術的出現,織出了比經錦花紋更繁復、更寬幅的織品。唐詩中有很多描繪織錦花紋富麗繁華的詩句,如“花攢騏驥櫪,錦絢鳳凰窠”“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等。而“自盤金線繡真容”“銀泥衫穩越娃裁”等詩句中所反映的金線織繡和金銀泥畫花,體現了唐代織物加金技術的提高。
織婦們的辛勤勞作,為唐代絲綢紡織業的繁盛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唐詩中“魚鹽滿市井,布帛如云煙”“繒帛如山積,絲絮如云屯”等詩句描繪了府庫、市場中絹帛堆積如山、浩如煙云的景象。然而這樣繁盛的物質經濟背后,是廣大織婦被繁重的賦稅和官府強令所逼,出賣青春和勞力,夜以繼日拋梭不輟的艱辛生活。唐詩中的織婦詩詞,對這些底層的勞動婦女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也譴責了苛酷不公的社會制度。孟郊《織婦辭》:“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樹。”描繪了農家個體織婦辛勞紡織,卻身無完衣的貧苦景象,指出了官府征稅之苛正是造成這一現象的社會原因。而作為因有特殊技藝而受官府嚴格控制的織造戶,不僅勞動成果,甚至人身自由也被剝奪。王建《織錦曲》:“合衣臥時參沒后,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里怪。”元稹《織婦詞》:“繅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反映了這些絲織業的精英們被統治階級所壓迫,不僅凝結了心血和創意的織品不能自由拿去兌換應得的酬付,更要付出青春和自由的代價。唐詩中巧思精技的織婦們悲慘的遭遇,與所描繪的精美織物相襯相對,反映了唐代社會不同階層間物質財富分配的巨大差異,對專制的封建社會制度之不公作出了有力的控訴。[2]
二、絲織品在唐詩中的反映
(一)豐富的品種
唐代的絲綢文化之發達,從唐詩中描繪的豐富的絲織品種類中可見一斑。杜甫《后出塞五首》:“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軀。”《憶昔二首》:“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白絲行》:“越羅蜀錦金粟尺。”從中可見,齊紈、魯縞、越羅、楚練、蜀錦的并稱,體現出山東、浙江、湖南、四川等地各種繼承了地方傳統與特色的絲織品在唐代社會生活中產生了跨地域的影響。而在唐詩中獨具特色而備受青睞的絲織品,這里取羅紗、綾和錦為代表加以詳敘。
羅和紗都是質地輕薄、繅絲精細、質感飄柔的半透明絲織品,單絲羅和輕容紗是其中的代表。王建《織錦曲》:“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宮詞》:“縑羅不著索輕容,對面教人染退紅。”可見這兩種極致輕薄的絲織品都曾是上流社會宮廷女性中的流行。而“酒法眾傳吳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最宜全幅碧鮫綃,自襞春羅等舞腰”“舞時紅袖舉,纖影透龍綃”等詩句,也流露出唐代人對羅紗的偏好和贊美。[3]
綾是單色提花的斜紋織物,在唐代頗受推崇,也是絲綢中的珍品。“厭裁魚子深紅纈,泥覓蜻蜓淺碧綾”“五色鶴綾花上敕,九霄龍尾道邊臣”等詩句中可以看到各色綾的盛行,而其中獨具代表性的繚綾,更是地方貢奉的佳品,在白居易《繚綾》中有著生動的描繪:“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臺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從中可見繚綾之花紋形制的獨具一格。而元稹《陰山道》“:越繚綾織一端,十匹素縑功未到。”則更為量化地說明了繚綾織造的費時費工,突出了這種織物的精美和貴重。
錦歷來是絲綢中的名貴品種,更以豐富多彩的紋飾花樣而聞名。溫庭筠《織錦詞》:“簇簌金梭萬縷紅,鴛鴦艷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蕊亂云盤相間深。”盧綸《宴趙氏昆季書院因與會文并率爾投贈》:“花攢騏驥櫪,錦絢鳳凰窠。”都可見錦的色彩花紋之絢麗。王建《織錦曲》:“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秦韜玉《織錦婦》:“合蟬巧間雙盤帶,聯雁斜銜小折枝。豪貴大堆酬曲徹,可憐辛苦一絲絲。”不僅描繪了錦紋艷麗,更點出其織成不易。[4]
(二)多彩的紋飾。
唐代的絲綢藝術之繁盛,從唐詩中所描寫的各類絲綢紋樣中得到了繽紛生動的體現。紋飾主要集中在鳥獸紋、花草紋和幾何紋三大類。白居易《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杜牧《偶呈鄭先輩》:“不語亭亭儼薄妝,畫裙雙鳳郁金香。”張祜《感王將軍柘枝妓歿》:“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施肩吾《雜谷詞五首》:“夜裁鴛鴦綺,朝織葡萄綾。”這些詩句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花鳥瑞獸等吉祥圖案在各類絲織品中的反映。而唐代發展到新高度的印染工藝,也為織物新增了豐富多彩的花色,李賀《惱公》:“醉纈拋紅網,單羅掛綠蒙。”白居易《玩半開花贈皇甫郎中》:“紫蠟黏為蒂,紅蘇點作蕤。成都新夾纈,梁漢碎胭脂。”詩中所描寫的就是唐時民間常見的印染法絞纈和夾纈制造出的朦朧抽象、層次豐富的暈染效果。“戴花紅石竹,帔暈紫檳榔”“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瑤琴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等詩句,則多方面地表現了暈染、織繡、金泥畫花等多種制造絲織品紋飾的方法,在唐代人生活中的應用和推廣。[5]
而說到唐代著名的紋樣形式,就不能不提唐代人獨創的“陵陽公樣”。陵陽公樣是唐初封陵陽公的益州行臺竇師綸為蜀地綾錦所創設的新的絲綢紋樣,內容主要是以連珠團窠為形式,以成對的瑞獸鳳鳥為題材,在團窠當中的飾以對雉、斗羊、翔鳳、游麟等動物圖案,創造出一種勻齊均衡的對稱美。“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從奴斜抱敕賜錦,雙雙蹙出金麒麟”等詩句中所提及的祥鳥瑞獸紋,以及“花攢騏驥櫪,錦絢鳳凰窠”“空把金針獨坐,鴛鴦愁繡雙窠”“風遞殘香出繡簾,團窠金鳳舞,落花微雨恨相兼”等詩句中描繪的團窠對稱動物紋,應該就是對這種獨特紋樣的描繪。從詩中也可以看出,陵陽公樣多被用于瑞錦、宮綾,在上流社會中備受歡迎,同時因其中國式的高貴、穩重和寓意吉祥,直到中唐后百余年仍在流行,對唐和唐以后的織錦圖案影響十分深遠。[6]
三、唐詩中所反映的絲織品在唐代社會生活中的功能與地位
(一)反映審美情趣的變遷
絲織品在唐代社會文化生活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絲綢藝術的發展變化也成為唐代人審美情趣變遷的一個向標。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唐代,絲織品的形制和花樣不僅成為人們對服飾審美的一大要求,更成為一種生活時尚。劉禹錫《酬樂天衫酒見寄》:“酒法眾傳吳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與白居易《劉蘇州寄釀酒糯米李浙東寄楊柳枝舞衫偶因嘗酒……寄謝之》:“金屑醅濃吳米釀,銀泥衫穩越娃裁”相映成趣,都贊美了越地出產的絲織品,其質地和花式均為時人眼中的衣料上品。段成式《柔卿解籍戲呈飛卿三首》:“最宜全幅碧鮫綃,自襞春羅等舞腰。未有長錢求鄴錦,且令裁取一團嬌。”則反映出對衣料的藝術價值的高下判斷。若說“時世高梳髻,風流澹作妝。戴花紅石竹,帔暈紫檳榔”表現了盛唐時貴族女子的著裝時尚,那么“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則體現了織戶們為迎合不停翻新的時尚而必須面對的巨大的生產壓力。
另外,從紋飾藝術審美的角度,從詩歌中常可以看到唐代人對“新樣”的追求。王建詩:“遙索彩箱新樣錦,內人舁出馬前頭。”“不看匣里釵頭古,猶戀機中錦樣新。”可見時人對新樣錦的關注。張籍《酬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越地繒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便令裁制為時服,頓覺光榮上病身。”則體現出絲織品紋飾與唐代人生活情趣的密切相關。不斷追求新事物也是開放的唐代一大社會風氣,絲織品紋樣的日新月異正體現了唐代人以新汰舊、不斷發展的審美觀。鄭谷《錦二首》:“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流離桑柘殘。”元稹《陰山道》:“挑紋變倍費力,棄舊從新人所好。”都體現著這種社會審美觀的變遷,以及它與不斷發展的絲綢紡織業之間相輔相成關系。
(二)作為價值判斷的體現
唐代紡織業的高度發達,令絲織品的經濟屬性得到了極大限度的發揮。在唐代社會生活中,絲綢作為一種高級的手工業產品,往往體現出唐人的價值判斷。在唐代詩歌中,常可見到描寫絲綢作為價值尺度、充當賦稅和貢奉、用于賞賜和饋贈這幾個方面的功能。
陸龜蒙《顧道士亡弟子奉束帛乞銘于襲美因賦戲贈》:“比于黃絹詞尤妙,酬以霜縑價未當”和白居易《賣炭翁》:“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之中都是直接用絲綢來充當價值尺度,體現了其貨幣職能。白居易《秦中吟十首·重賦》:“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云屯。”皮日休《正樂府十篇·賤貢士》:“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如何賢與俊,為貢賤如此。”不僅體現了絲織品作為賦稅和貢奉的功能,同時揭露了貪贓枉法的官吏利用苛捐雜稅將人民壓榨殆盡的丑惡行徑,以及選才入仕的過程中以貢奉之便行賄賂之實的官場黑暗。
另外,絲織品還常常用于賞賜和饋贈。翁承贊《御命歸鄉蒙賜錦衣》:“九重宣旨下丹墀,面對天顏賜錦衣。……德音耳聆君恩重,金印腰懸己力微。”李頎《緩歌行》:“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侯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僚揖者稀。”反映的是織錦作為君于臣的賞賜,既是君恩浩蕩,也是為臣莫大的榮耀。李詢《贈織錦人》:“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竟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里尤嫌花樣疏。”則體現出絲綢錦緞作為給宮媛舞女的賞賜,它的織造者和受益者天差地別的命運。而用于私交饋贈的絲織品,既可作情人間的定情之禮,如杜牧《張好好詩》:“主人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疏。”也可傳達朋友間的關懷,如白居易《寄生衣與微之》:“淺色衫輕似霧,紡花紗薄于云。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詩歌中對用于賞賜和饋贈的絲綢織物的描寫,都體現了唐人對絲綢的價值認識,并進一步將其用以交換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滿足。
唐代詩歌中所描繪的綾羅錦緞,從各個方面展現了唐代絲綢紡織業的發展進步,絲織品的織造和使用對唐代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詩人們所記錄和描繪的唐代絲綢文化對唐代人的審美觀與價值觀的反映,以及在唐代人的社會文化風氣中的浸染,在唐代以后千百年的歷史文化發展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1]于年湖.從唐詩看唐代的手工業和商業狀況[J].商場現代化,2007(9).
[2]盧華語.全唐詩經濟資料輯釋與研究[M].重慶出版社,2006.
[3]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舞蹈史研究組.全唐詩中的樂舞資料[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
[4]趙豐.中國絲綢藝術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5]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飾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繆良云.中國歷代絲綢紋樣[M].紡織工業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