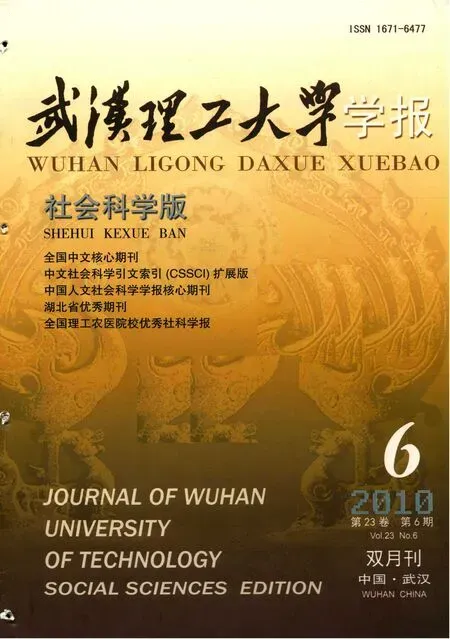王陽明致良知學(xué)說及其實(shí)踐論內(nèi)涵
黃百成,趙 晶
(武漢理工大學(xué) 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63)
王陽明致良知學(xué)說及其實(shí)踐論內(nèi)涵
黃百成,趙 晶
(武漢理工大學(xué) 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湖北 武漢430063)
從實(shí)踐論的角度,對致良知學(xué)說進(jìn)行深層次的解讀。王陽明的心學(xué)理論,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與致良知。王陽明到晚年才提出致良知說,被他的門人奉為晚年的親切教訓(xùn),致良知的提出標(biāo)明陽明心學(xué)已完全成熟,臻于化境。
王陽明;致良知;實(shí)踐
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在立德、立功、立言幾方面都達(dá)到高度成就的哲學(xué)家,他的思想學(xué)說的完成形式,即致良知論,概括了他一生各個階段的其他重要命題。
所謂實(shí)踐,以西方哲學(xué)大師康德的理解,就是泛指與吾人內(nèi)心立意或行為決定有關(guān)事務(wù)的總稱。這樣的實(shí)踐在王陽明的學(xué)問上是頭等要務(wù)。
王陽明在其38歲的時候提出了“知行合一”說。知行合一命題涵義豐富,可作為為教的方法,從提出之日起,它就不斷地受到人們的質(zhì)疑與批評,其中不僅有宗朱學(xué)者,甚至連王陽明的高徒與世友,也都為之困惑。因此,王陽明提倡身心上體履,用靜坐的方式補(bǔ)充“知行合一”為教的不足。但王陽明發(fā)現(xiàn)許多學(xué)者在靜坐時會產(chǎn)生思慮紛雜,不能強(qiáng)制禁絕的弊病。于是,王陽明在正德十五年(公元1521年,時年50歲)居住于贛州時提出了致良知命題,目的是解決為教時的動靜問題。
一、致良知中的致與良知的涵義
王陽明致良知說的提出,有一個發(fā)展過程。龍場之悟可以看作他的“良知”學(xué)說確立的開端。他的“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路,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心上做”[1]。實(shí)際上已為良知之學(xué)規(guī)定了方向:格物不是向外窮理,而是向內(nèi)正念頭。但此時良知所包含的內(nèi)容遠(yuǎn)不如正式提出致良知作為學(xué)問宗旨時那樣廣大。因此王陽明在去世前就一直說:“吾平生講學(xué),只是‘致良知’三字。”[2]
王陽明是以至、極、盡之義來解釋“致”字,也就是說,“致良知”就是擴(kuò)充推行自己先天稟賦的,發(fā)見于日用之中的良知,使良知全體充拓得盡,得以充塞流行,無有虧缺障蔽。王陽明的學(xué)生黃綰對此有一精辟的解釋:“予昔年與海內(nèi)一二君子講習(xí),有以致知為至極其良知……致者,至也,至極其良知,使無虧缺障蔽”[3]。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意義是至極其良知,就是拓展自己的良知,將自己的良知擴(kuò)充到底,把良知推廣到人倫日用當(dāng)中去。這是致良知的至極義,也就是孟子所言的盡性,在《大學(xué)》里叫做致知,在這個意義上說,“致良知”的至極義就是從良知本體向良知發(fā)用的展開。
王陽明將“致”字工夫視為用力之最難處,他批評有些學(xué)生時說:“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于此實(shí)用功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得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4]
良知從本然之知走向明覺之知是以“致”字工夫(即行)為中介的,先天良知在“致”的工夫中不斷地達(dá)到明覺的狀態(tài)(即為主體自覺把握),而主體的“致”字工夫不斷地消解良知的先天性,使其獲得現(xiàn)實(shí)性,從而使自己能夠自覺地把握良知,使良知成為實(shí)存諸己的德性。
致良知中的良知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天賦道德意識。即王陽明在《年譜》中有“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的論述,其良知的此義得自孟子。二是在實(shí)事中鍛煉成的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就是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善知惡是說,發(fā)一念是善還是惡,自己的良知自會知得。在這里,良知是對意念進(jìn)行監(jiān)察的深層價(jià)值判斷系統(tǒng),是意念、欲望、情感等感性我之外的價(jià)值我。要使對意念的監(jiān)察有效,良知自己首先得有一個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這個標(biāo)準(zhǔn)就是好善惡惡。三是良知的意義是能思維的主體,即思想和知識的承擔(dān)者,這個意義的良知又叫心之虛靈明覺。也就是說,良知的活動與代表宇宙萬象的易同其廣大,對良知的開掘拓展無止境。四是良知是宇宙的具體而微的表現(xiàn),這就是王陽明說的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個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這個是王陽明達(dá)到上述第三個方面的含義的基礎(chǔ)上,以良知為全部精神活動的主體之后而有的新的升華。他認(rèn)為,人是天地的心,而人又以心為主宰,所以人的心,人的精神活動是宇宙的最高表現(xiàn)。
以上是從致良知的充拓義來看良知的具體意義,正如王陽明所言:“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diǎn)此二字不出。”[5]致良知是其一生思想的系統(tǒng)總結(jié)和升華。這個學(xué)說一方面是指人應(yīng)擴(kuò)充自己的良知,擴(kuò)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實(shí)在地付諸行為中去,從內(nèi)外兩方面加強(qiáng)為善去惡的道德實(shí)踐。
二、致良知說的實(shí)踐論內(nèi)涵
王陽明是個文武全才,他不把自己限制在當(dāng)時大多數(shù)由科舉出身的官吏慣常采取的道路上,而是進(jìn)行了多方面的實(shí)踐活動。王陽明的致良知說所包含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他倡導(dǎo)在實(shí)踐中,于內(nèi)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養(yǎng),于外以建立經(jīng)世濟(jì)民的功業(yè)。王陽明的學(xué)說可以說是實(shí)踐的良知學(xué)或良知的智慧學(xué)。
(一)先天良知與后天經(jīng)驗(yàn)的道德實(shí)踐
王陽明對良知的本然狀態(tài)與明覺狀態(tài)作了區(qū)分,前者帶有自在的性質(zhì),后者則是對良知的自覺意識。當(dāng)良知對主體來說還處于本然狀態(tài)時,主體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自在的存在,從本然走向明覺,以致為其中介。良知作為內(nèi)在的道德意識與理性原則,具有先天的性質(zhì),這種先天性首先是就其起源而言:良知的形成先于一切經(jīng)驗(yàn)活動。
王陽明認(rèn)為良知是內(nèi)在的德性真實(shí)和本然的至善,是先驗(yàn)的道德潛能或道德理性。人心本有道德價(jià)值和倫理素質(zhì),此道德價(jià)值和倫理素質(zhì)不學(xué)而能,不慮而知,但又可隨時呈現(xiàn),當(dāng)下切己體驗(yàn)。良知的先天性固然擔(dān)保了良知的普遍有效性,但卻無法擔(dān)保主體對良知的自覺意識。先天與明覺的這種區(qū)分,無疑有其理論上的意義。從邏輯上看,先天的完成往往意味著對主體作用的某種限制:作為天之所賦,良知的形成并非出于主體的學(xué)習(xí)與思考。
后天的工夫的作用只是以旁助的方法,促使先天的良知自然地顯發(fā)或活潑地敞開,所謂豁然有見便是實(shí)存生命契入良知本體,本體與工夫長期相互作用,而最終獲得了時機(jī)化的綻放與彰顯。這一豁然有見的過程本質(zhì)上即是人性固有之至善由先驗(yàn)變經(jīng)驗(yàn)、先天變后天的過程,即天賦良知觸發(fā)于人的道德實(shí)踐活動而自動呈現(xiàn)的過程。
(二)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在實(shí)踐中的理論互涵
致良知學(xué)說和知行合一說是相互聯(lián)系的,從心學(xué)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看,知行學(xué)說可以看作致良知學(xué)說的邏輯展開。王陽明認(rèn)為致知的目標(biāo)首先指向內(nèi)在的良知,這一點(diǎn)同樣體現(xiàn)于知行的工夫:“君子之學(xué),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于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6]52
知行合一之說是王陽明謫居貴州龍場時首先提出來的,后來又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來,此新的方式就是致良知,王陽明認(rèn)為致良知與知行合一意義相同,只是以更直接的方式表達(dá)而已。王陽明“知行合一”之“知”即是“知”是心之本體之“知”,即是“致”知之“知”,也是“良知”之“知”。王陽明將脫離良知明覺的盲目行動排除于行的概念之外。
首先,王陽明賦予“行”字的意涵又比通常的理解要更寬泛。在王陽明的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行”本身已具有道德的意義,可以承擔(dān)道德責(zé)任。因此,王陽明才要求我們“發(fā)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7]。
其次,良知的“知”是與事親、治民、讀書、聽訟等道德活動相聯(lián)系而言的,這些行為不能脫離良知之明覺感應(yīng),而良知本身就含有實(shí)現(xiàn)這些活動的力量。
致良知的目標(biāo)在于從本然走向明覺,而要實(shí)現(xiàn)這種轉(zhuǎn)換,便不能離開知與行的互動。以關(guān)于孝之知而言,“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jié),則必實(shí)致其奉養(yǎng)之力,而后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yǎng)之宜,則必實(shí)致其奉養(yǎng)之力,而后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8]。因此,王陽明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行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6]50
王陽明要求通過日用事為間的體究踐履而成就德性,無疑更自覺地注意到了道德實(shí)踐在德性培養(yǎng)中的作用。知行互動與成就德性構(gòu)成了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王陽明對此做了概括:“區(qū)區(qū)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著實(shí)去致良知,便是誠意。”[9]格物而致其知,是對先天良知的自覺,誠意則指向德性的完善。這種思想體現(xiàn)了陽明注意到了理性的自覺、德性的升華與后天的實(shí)際踐履是一個統(tǒng)一的過程。
(三)致良知中道德理性與知識理性實(shí)踐合一
致良知包含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的結(jié)合。這就是要以道德理性為統(tǒng)領(lǐng),以知識理性為輔翼,在實(shí)踐中實(shí)現(xiàn)兩者的同步發(fā)展。
在致良知學(xué)說提出后,王陽明就把每一次的致良知看成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的綜合作用,這時道德理性與知識理性的結(jié)合不是一種總的方法和綱領(lǐng),而是步步皆實(shí),時時皆有的具體步驟。致良知的“致”字也由初時的“擴(kuò)充、積累”義變?yōu)橄蛲馔浦隆?shí)行義。從推致良知于實(shí)踐這個方面看,致良知中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的結(jié)合這一精義可歸納為以下幾點(diǎn):
第一,格物須在實(shí)事上格。王陽明把《大學(xué)》中最重要的功夫“格物致知”代之以“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把良知所知之天理推行到具體的做事上。
第二,道德理性對于知識理性有驅(qū)迫力。致良知最主要的,即以善良意志包括善的動機(jī),也包括完成此事的決心與求知的驅(qū)迫力。良知有做好某一件的知識固然好,即使對做此事缺乏知識,道德理性這一主宰也會激勵或驅(qū)迫知識理性去獲得關(guān)于此事的知識。
第三,在致良知過程中,知識理性會根據(jù)道德理性給予的原則,使各個不同的事物各如其理,各極其則。在致良知的具體活動中遇到相應(yīng)的刺激便當(dāng)機(jī)而發(fā),這種當(dāng)機(jī)而發(fā)采取了直覺的、不假思索的形式。這種當(dāng)下出之不假思索而自然天成的形式省去思量考校簡擇的過程,使人覺得它是天賦的,心中固有的。
王陽明晚年,其實(shí)踐的良知學(xué)已達(dá)到相當(dāng)高的造詣,黃宗羲在《明儒學(xué)案》里甚至把這樣的造詣形容為“如赤日當(dāng)空而萬象畢照”[10]。
三、致良知說的當(dāng)代實(shí)踐論意義
致良知活動涵蓋了人類歷史文化的全體進(jìn)程,但違背良知也成為人類歷史文化進(jìn)程中經(jīng)常遭遇的事實(shí)。人類之所以要依據(jù)良知不斷地建構(gòu)、充實(shí)和豐富意義世界,恰好便是緣于歷史文化中始終存在著違背良知并消解了意義世界的具體事實(shí)。因此,王陽明在工夫上倡導(dǎo)致良知,把致良知看成是與本體不二的實(shí)踐論工夫,是治療各種人的氣質(zhì)之性的疾病和道德流弊的良藥,能夠把人從各種沉淪狀況中喚醒并返回真實(shí)本然的自我,同時也是成圣之學(xué)最根本的教法,足以成為生命和學(xué)問的人生指南:致良知是學(xué)問大頭腦,是圣人教人第一義。
(一)當(dāng)代的學(xué)術(shù)困惑——讀書解經(jīng)與德性實(shí)踐的本末倒置
我們現(xiàn)在也遇到了與王陽明時代相似的困惑。現(xiàn)時代是一個以知識過度膨脹而淹沒了價(jià)值理性的時代。盡管當(dāng)今東西方文化格局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西方人越來越多地把眼光轉(zhuǎn)向東方,企圖重新理解先前他們用純知識的眼光看作神秘甚至荒謬的東西,但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優(yōu)越論及植根于希臘哲學(xué)中的理性傳統(tǒng),現(xiàn)在仍是支配西方思想界的主要觀念。中國古代教育沿襲演變至今,忽視人的全面發(fā)展逐漸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社會問題。
儒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是實(shí)踐理性,尤其是經(jīng)孟子發(fā)展和闡釋的儒學(xué),其根本目的就是使人的道德修養(yǎng)漸趨完備,因此能否落實(shí)到踐履層面是衡量一個學(xué)人水平的標(biāo)準(zhǔn)。儒家的各種經(jīng)典的目的在于教育、指導(dǎo)、說服人去這樣做,所以,也可以這樣去理解:經(jīng)典、言說是手段,修德、實(shí)踐是目的。王學(xué)的立足點(diǎn)與出發(fā)點(diǎn),就是王陽明終身痛切批判的徒騰口說的學(xué)風(fēng)。陽明學(xué)最大的動機(jī)就是要糾正這種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實(shí)踐的學(xué)風(fēng)。
(二)致良知學(xué)說的當(dāng)代實(shí)踐論意義——注重為學(xué)的道德踐履
王陽明指出了道德踐履的重要性,學(xué)孝必須真正以己身去躬行孝道,只是空口耳去講去聽孝,不能稱作真正的學(xué)孝。德,不能僅停留于對善觀念的認(rèn)知,知以行為功,善的認(rèn)知和動機(jī)必須借助于行動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意向的善只有落實(shí)到實(shí)際行動中,才是真正的善。
當(dāng)代學(xué)校的德育也在試圖開展注重踐履的德育,但課堂道德知識灌輸仍是主渠道,主陣地,這種德育途徑傾向于認(rèn)為只要讓學(xué)生盡可能地學(xué)習(xí)有關(guān)道德的知識,學(xué)生自然會形成道德認(rèn)知、道德意志、道德信念,最后,在實(shí)際行動中實(shí)踐道德。現(xiàn)代德育旨在培養(yǎng)出具備相對穩(wěn)定心理特點(diǎn)、思想傾向和行為習(xí)慣的人,基于此,我們應(yīng)該對以往的德育中某些單調(diào)的、干癟的方法進(jìn)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構(gòu)建新的,適合時代精神的德育教育模式。而陽明學(xué)的目的就在于解決道德實(shí)踐的問題,強(qiáng)調(diào)付諸實(shí)踐的重要性,否則,各種認(rèn)識即不成為真正的認(rèn)識。為了強(qiáng)調(diào)道德踐履的純粹,將道德評價(jià)深入到思想深處,讓一點(diǎn)雜念也同樣承擔(dān)道德行為的責(zé)任。
王陽明的學(xué)說對現(xiàn)代人仍具有啟示作用。
[1]王陽明.與黃宗賢[M]∥王陽明全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9.
[2]王陽明.書正憲男手墨二卷[M]∥王陽明全集:卷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90.
[3]黃 綰.明道編:卷1[M].北京:中華書局,1959:10.
[4]王陽明.與陳惟睿[M]∥王陽明全集: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22.
[5]王陽明.傳習(xí)錄拾遺[M]∥王陽明全集: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70.
[6]王陽明.傳習(xí)錄中[M]∥王陽明全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王陽明.傳習(xí)錄下[M]∥王陽明全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6.
[8]王陽明.書朱守諧卷[M]∥王陽明全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77-278.
[9]王陽明.傳習(xí)錄中[M]∥王陽明全集: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3.
[10]黃宗羲.姚江學(xué)案[M]∥明儒學(xué)案: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85:181.
Wang Yangming's Consciousness and Its Connotation of Practice
HUANG Bai-cheng,ZHAO 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H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s Consciousness from the angl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His psychological theory can be shortened as intuitive knowledge and realizing intuitive knowledge.Put forward in his late years,the theory of realizing intuitive knowledge was looked upon as a kind lesson by his apprentice,and also the sign of the maturity of his psychology.
Wang Yangming;realizing intuitive knowledge;practice
B248.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0
2010-08-25
黃百成(1953-),男,湖北省天門市人,武漢理工大學(xué)教授,主要從事哲學(xué)與科技文化研究;趙 晶(1983-),女,浙江省余姚市人,武漢理工大學(xué)政治行政學(xué)院科技哲學(xué)碩士生,主要從事科技哲學(xué)與科技文化研究。
(責(zé)任編輯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