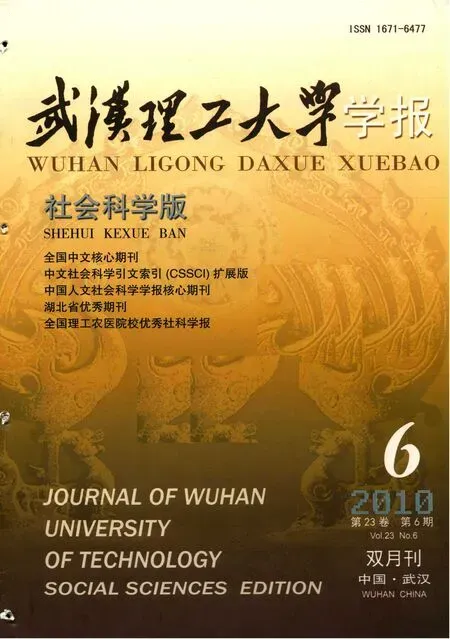中國互聯網政治功能研究述評*
溫瓊娟,陳先紅
(1.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4;2.武漢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81)
中國互聯網政治功能研究述評*
溫瓊娟1,2,陳先紅1
(1.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4;2.武漢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81)
互聯網作為新的大眾傳播媒介,同傳統的大眾傳媒一樣,承擔著社會系統的政治功能。從政治參與、權力監督、政治溝通和建構公共領域四個方面對國內互聯網政治功能的研究情況進行了述評。
互聯網;政治參與;政治溝通;輿論監督;公共領域
關于傳統的大眾媒介的政治功能,美國的經驗學派和歐洲的批判學派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經驗學派側重從體制內去探討,而批判學派則側重從體制外去探討。
傳播學的奠基人及政治學家拉斯韋爾于1948年在其專著《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媒介具有監視環境、聯系社會和傳遞遺產的功能,而施拉姆則在《傳播學概論》中將這幾點重新整理以后,確定了大眾媒介具有監視(收集情報)、協調(解釋情報,制訂、傳播和執行政策)、社會遺產、法律和習俗的傳遞等幾項政治功能[1],概括了大眾媒介與政治系統的互動過程。而在現代民主社會,大眾媒介體制內的政治功能具體體現為:其一是政治參與功能;其二是權力監督功能;其三是政治溝通功能;其四是政治控制功能;其五是議程設置功能[2]。議程設置是實現傳播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成為功能,同時,在民主社會,政府或政黨就是通過政治溝通實現政治控制的,因此,政治溝通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實際上具有相同的內涵。
然而,歐洲批判學派的學者則傾向于從體制外去思考媒介的政治功能,從而把大眾媒介看成是公共領域的代表。公共領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該應有相等的自由表達機會,并且能夠自主地組成公共團體,其討論的主題應以批評公共事務為主[3]。
在政治體制允許的范圍之內,公民通過政治參與和權力監督影響政治系統的運行,而政府(政黨或政治利益集團)通過政治溝通干預政治系統。前者的主體是公民,后者的主體是政府(政黨或政治利益集團),兩者在話語博弈的過程中形成了張力,由此構成了政治“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體制之外的客觀存在,但是它對整個社會政治系統的進化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傳統的大眾媒介的政治功能包括四個方面: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權力監督與政治溝通,體制外的建構公共領域。這四個方面的政治功能的總結,采用了政治學的視角和傳播學的方法,體現出兩個學科在該研究領域的交叉融合。
而作為新媒介形態的互聯網,在中國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成長為新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它在政治系統中承擔著和傳統大眾媒介同樣的政治功能。但是,由于互聯網的特性,使得它在承擔政治功能的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征。這一點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通過搜索中國目前有影響的幾家網絡中文學術數據庫,將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內所發表的關于互聯網政治功能研究的主要論文匯總篩選和分類歸納,并進行了述評,以期為這一方面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基礎。
一、政治參與功能
政治參與指的是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通過和實施的過程。通過政治參與,公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愿,爭取自己所得的權益,并維護自身的基本權利。而在現代社會,政治參與往往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來實現的。互聯網作為新興的大眾媒介,它是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在提高政治參與程度和推進民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與傳統的政治參與相比,網絡政治參與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具有平等的參與主體;自由的參與空間;低成本的參與手段;虛擬的參與身份等[4]。互聯網對政治參與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互聯網為提高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政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平臺;其次,互聯網的應用有利于促進利益表達和利益聚集;再次,互聯網豐富了政治參與的渠道[5]。尤其有意義的是,網絡政治參與的平等與自由,能夠促進協商民主的發展[6],從而解決了大規模政治體系中的協商民主問題,推進了“草根”民主的發展[7]。
互聯網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民通過網絡直接向政府機關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參與重大事項討論;表達一定的政治感情;監督政府機關的運行;進行政治投票[8]。而政治參與使用的具體的網絡工具包括:BBS留言板、評論、博客、論壇等諸多方式。
然而,互聯網的政治參與并不必然地催進民主的發展。我們首先所面對的現實是,盡管我國已經有近3億人口使用互聯網,總量雖多,但相對人口總數來說,仍舊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在使用程度上也有明顯的差異。由于互聯網的接入和使用的差異所造成的人們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上的差異這種“數字鴻溝”必然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9],使得政治參與依然是小部分公民的參與,并且亦有可能成為社會分化和斷裂的催化劑。
此外,還存在敵意參與、無序參與以及非理性參與等問題[10]。這些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網絡政治參與不僅不能推進民主,而且還會威脅國家政治安全,貽害無窮。因為,網絡政治參與既可能緩解政治沖突,促進政治穩定;也可能激發政治沖突,解構政治秩序。網絡時代和諧與穩定政治的實現途徑關鍵是政府和公民能否利用好網絡媒介,能否形成良性互動關系[11]。
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從互聯網本身著手,培養網民的公民意識和主體精神,倡導理性有序的網絡政治參與文化。但是,網絡政治參與的社會現實性決定了民主不能僅從發展網絡去建構,推動民主更需要網絡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主體的成熟,網絡政治參與環境的改善[12]。這些都需要政府的積極推進。而政府要實現這種積極作用的前提是將傳統的管理模式改變為服務型的管理理念,扁平化的管理組織,人性化的管理方式[13]。在此前提下,政府必須從加快電子政務建設,促進網絡技術發展,規范網絡秩序,加速國家信息化進程等多個層面入手,以推動網絡時代政治參與的深化[14],并且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使網絡政治參與制度化和規范化。
網絡政治群體的不斷壯大,網絡民意的理性聚集,網絡與傳統媒體的共鳴及政府開明的制度供給,這些都是網絡政治參與有效性的基本保障[15],而這些,只有在解決了以上問題以后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二、權力監督功能
作為民主政治的產物,權力監督是公民依法對國家機關、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和個人活動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了解和評論的過程,是實現公民權利的重要手段。
而公民有效地實現權力的監督,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權力執行過程的透明化,或是對濫用權力行為有揭露之自由;二是公民具有對以上兩種情況發表言論的空間,從而形成輿論,通過輿論監督權力。因此,互聯網作為權力監督的工具,其作用也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作為信息來源,保證公民的知情權;二是通過網絡輿論監督,實現公民的表達權。
(一)網絡知情權
網絡還民眾知情權的成就感,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傳統壟斷媒體在互聯網時代不得不拱手相讓的。官方壟斷媒體往往被禁止采訪報道而集體失語。而互聯網的技術特點造就了自由、平等、兼容、共享的技術準則和網絡精神,促成了小眾話語、個體話語對壟斷傳媒話語的技術消解,進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官方金字塔式權力控制模式[16]。
然而,通過網絡爭取知情權所反應的事實是,在現實生活中,公民的知情權受阻,而網絡提供了信息交換的平臺,網民們通過信息“拼圖”的方式,力圖拼湊出事實的真相。從最近幾年發生的眾多“網絡事件”來看,網絡知情權并非具有制度化的保障,而更多是網民的自發行為,以及政府的被動行為。
于是,有學者認為,網絡知情權不是具有現實性的政治權利,只不過是一種充滿了崇高幻覺的虛擬權利。用網絡知情權的方式代替真正社會權利的實現,這一點正是網絡時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值得警惕的地方[17]。
在民主社會里,知情權是一項基本權利,公眾應當知曉政府在做什么,為什么要這樣做。這里隱含著一個假定,那就是政府行為必須透明公開[18]。政府、立法及司法機構是公共決策的主體,因此,必須將決策及決策的依據告知公眾,以說服公眾,或者接受公眾的監督。作為目前效率最高的大眾傳播媒介,網絡可以用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推進民主社會的進程,亦可以淪落為散布流言的幫兇,損害政治穩定。
(二)網絡輿論監督
輿論是公眾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長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19]。因此,它必然對決策機構形成強大的壓力,使得決策機構的行為展現在公眾的關注之下,從而實現了對權力的監督。
因此,權力監督的第一步是公眾知情,第二步就是公眾形成輿論。而網絡輿論則指相對于傳統大眾媒介而言,網絡是輿論得以形成并傳播的主要渠道。
傳統大眾媒介反映出來的輿論主要體現的是媒體組織的意見,而互聯網使公眾有了直接表達各種意見的渠道,其傳播特性加速了輿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公眾輿論在網上聚集放大,使公眾輿論力量的體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形成了獨特的輿論形態[20]。傳統大眾媒介輿論監督的側重點在于宏觀、宏大的事件上,而網絡輿論監督則很典型地體現出“草根性”,小處見大,通過普通網民發現的小問題,往往折射出重大的社會問題。比如“天價煙局長”、“釘子戶”,等。這是由于在網絡中,由于傳播與溝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人們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關注數量眾多但分散、弱小、獨立、細微的信息,網民“草根”聲音通過聚合形成強大的話語場和傳播效力因而形成了網絡輿論的長尾效應[21]。這正好彌補了傳統大眾媒介輿論監督范圍和力度的不足問題。
網絡輿論的形成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社會事件的發生或熱點、敏感話題的出現;各種意見通過論壇、博客、即時通訊等平臺進行交流融會形成傾向意見;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共振”形成輿論的立體傳播[22]。網絡輿論通過權力監督,推動公共政策議程,拓寬政策方案的選擇空間,使政策制定更科學,并且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質量[23]。
然而,同時,網絡輿論亦存在以下明顯的問題:一是產生網絡暴力;二是易于干預司法;三是制造虛假民意。
(三)網絡暴力
不可否認,人性、道德和正義是網絡暴力乃至人肉搜索的驅動力,然而,公民社會的前提是,所有的行為都必須在理性、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而網絡暴力形成的“土壤”是網絡表達中的非理性,網絡暴力與網絡中的“群體”直接相關,網絡暴力還表現為自我糾結的道德困境,網絡暴力體現了網民社會參與的不成熟性[24]。網絡平臺塑造了“非實體性”的輿論主體,網民以群內同質化、群際異質化的特點聚集,志同道合的網民群體易于出現嚴重的群體極化傾向[25]。非理性和群體極化很容易導致網絡暴力的產生,從而扭曲網絡輿論的真正內涵。
(四)干預司法
司法是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要領域,網絡輿論影響司法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網絡傳播具有強化“議程設置”和弱化“沉默的螺旋”效果。“議程設置功能”在司法實踐中表現為個體可以很方便地將一個日常的案件通過網絡傳播來讓大眾知曉,從而成為社會性案件,并通過設置某一討論主題來表達網絡上的“民意”,以網絡輿論來影響司法;“沉默的螺旋”弱化對司法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促進了司法的民主化[26]。
輿論與司法存在兩種互動狀態,網絡輿論與司法的良性互動以及網絡輿論對司法的異化。良性互動促進司法公正,而輿論對司法的異化則會導致“媒介審判”,影響司法公正[27]。
(五)虛假民意
所謂民意,至少要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然而,網絡輿論是否能夠真的代表民意呢?而網絡輿論的事實是,情緒化輿論往往形成一邊倒之勢,構成了社會民意的假象,誤導公眾,不利于公眾的理性思考[20]。最為嚴重的是,被俗稱為“網絡黑社會”的勢力,潛伏在各大門戶網站的論壇上,操控不明真相、缺乏理性思考的廣大網民,從而制造虛假網絡民意,為少數利益集團謀取利益[28]。虛假的網絡輿論傳遞出欺騙性的民意信息,甚至會誤導政府的決策。
面對網絡輿論存在的以上問題,我們有必要找出良好的應對之策。首先,建立健全監管網絡輿論的法律法規,加強對網絡從業人員和網民的責任意識、自律意識和道德觀教育,重視“意見領袖”的作用,黨報也應在引導網絡輿論中發揮自己的作用[29];其次,促進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之間的互動,倡導協商型司法正義,為網絡輿論設置邊界,防止“網絡媒體審判”,適度限制網絡“公權力”,適當寬容網絡輿論,加強司法公開和民主[26];最后,除了加大技術上的控制和立法的強度以外,政府加強網絡輿論引導,根據不同輿論主體群落的不同特點,增強輿論引導的針對性;針對網民易受權威左右的特點,加強引導者的權威性[25]。
三、政治溝通功能
“政治溝通”作為從美國引進的概念,對應的英語是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美國,political communication研究始于20世紀50—60年代,這個概念自誕生以來,一直爭議不斷,流派眾多,從未有過清析的界定。而這個概念在中國則更為復雜,由于對communication這個單詞理解上的差異,存在“政治傳播”和“政治溝通”兩種不同的譯解。實際上,廣義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應當被理解為政治傳播,指的是大眾傳播與政治系統之間的互動[30];而狹義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則應當被理解為政治溝通,是指掌握一定政治資源的政治主體如政府或政黨,通過一定的媒介輸送、獲得和處理政治信息的行為或過程[31]。因此,政治溝通應當包含在政治傳播的范疇之內,是政治傳播的一個方面,是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和傳播學經驗學派共同研究對象。除此之外,傳播學的批判學派及政治經濟學派,致力于對媒介、權力和資本的共生關系進行批判性的政治傳播研究。因此,也可以認為政治溝通是狹義的政治傳播。
由于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導致國內學者對政治溝通研究投入不足。本文認為,站在政府或政黨的角度,探討政治信息傳播的技巧、方法和效果的論文,均屬于政治溝通類論文,而不管論文中是否稱這種形式為“政治溝通”。
在傳統的大眾媒介環境下,政府掌握了媒介的近用權和消息來源,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挑戰了高度集中控制的媒體管控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政府與公眾在媒介近用權和消息來源方面的關系狀態,呈現出政府近用新媒體能力的低下,壟斷消息來源地位被瓦解,民眾近用新媒體權力擴大,消息來源角色增強的二元博弈格局[32]。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信源的多樣化及信息傳播的即時性,使得“把關人”角色缺失,“議程設置”草根化,因此,很容易引發公共危機,從而損害政府公信力和聲譽。而在突發性的公共危機狀態下,由于危機態勢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性,良好的政府聲譽就成為社會公眾預測和解釋其未來行為的一個及其重要的因素[33]。因此,在政治溝通中,政府聲譽是一個關鍵因素。
而在公共危機傳播過程中,通過互聯網作為傳播渠道,官方的政治溝通和民間輿論構成了雙重話語空間[34]。官方模式主要有封閉控制模式、單向宣教模式和雙向溝通模式,與之相對,非官方模式主要有揭露模式、抵觸模式和肯定補充模式,二者一一對應形成雙重話語空間的三種互動模式:控制封閉VS揭露模式;單向宣教模式VS抵觸模式;雙向溝通模式VS肯定補充模式。這三種互動模式分別呈現出積極或者消極的傳播效果[34]。這幾種模式為公共危機中的政治溝通提供了參考。
總之,政治溝通暢通,不僅可以使黨和政府的決策合理化和民主化,維護和鞏固政治秩序,而且還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促進公民相關政治權利的實現[31]。
四、建構公共領域功能
“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公眾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政治學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35]。
展江認為,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演進的論述,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為線索,但這并不意味“公共領域”對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意義。在我國大力發展民主與法制,推進市場經濟的情境下,“公共領域”的存在非常必要。他亦提出,傳媒與高新技術和新經濟的關系以及新技術對傳媒和社會的影響有待深入研究,那么,新的傳媒技術對公共領域的建構有何種影響呢?這正是思考互聯網對公共領域建構的切入點[36]。
有研究者認為互聯網對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具有積極意義[37],虛擬現實技術是在信息意義上對實體屬性的實現,為現實公共領域提供了虛擬論域平臺,人們利用虛擬現實技術而充分進行的自由和交流性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為公共領域的重建帶來契機[38]。
有研究者認為,通過對互聯網上言論最豐富的BBS和博客進行研究,網絡虛擬社群具有拓展網絡公共領域的意義[39];網絡公共領域內的參與主體已經初步具備了哈貝馬斯定義下的私人屬性[40];中國大陸的“兩會”博客是目前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制[41];“強國論壇”已經具有現實的公共領域的特征,可監督國家權力并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是一個公共權力的批判領域[42]。
然而,公共領域的形成首先需要外部制度化空間,還需要內部要素包括參與者、媒介和共識。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網絡傳播目前只能提供公眾參與的意見平臺,尚不能被看作公共領域勃興的契機[43]。此外,由于進入網絡空間受經濟、知識等門檻限制,以及網絡空間語言霸權、數字鴻溝等造成的不平等,仍制約著網絡空間成為公共領域的可能[44]。因此,“強國論壇”可以稱作是一種公共話語空間,而不是一種理想的公共領域[45];盡管“華南虎”事件體現出了公眾的平等參與及理性批判等能力,但是,公眾輿論的意見集合與權力機關決策過程之間還存在斷裂,此外媒體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還不能給公共領域提供全面發展的空間[46]。
當然,也不排除未來民主社會出現具有公共領域性質的第二條媒體通道,即在保留傳統媒體的功能的第一條媒體通道之外,出現脫離第一通道控制,純粹表達不同的個體或團體公眾參與的意見和異見平臺[43]。如果這條通道有存在的可能性,那互聯網無疑是最理想的平臺。還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論證在網絡輿論中,官方話語、民間話語之間存在著52%的意見中立者,這52%的中立者,大多數通過引導可以轉化為公共領域的參與者[47]。
五、結 語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對互聯網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學領域與傳播學領域,處于兩個學科的交集點。由于互聯網具有迥異于傳統大眾媒介的特性,因此,它從擴大政治參與,加強權力監督,促進政治溝通和建構公共領域四個方面承擔著社會系統的政治功能。但同時,互聯網亦有可能導致無序的政治參與,民意的被操控及司法的扭曲,它并不能決定其自身是否能夠在社會系統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必然地推進民主。因此,要實現互聯網的積極的政治功能,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公民意識的覺醒,只有實現這一點,才能保證是理性的主體在使用互聯網;二是法律制度的完備,民主需要規則,沒有規則的民主只會走到民主的反面。
到目前為止,盡管就互聯網政治功能的四個方面的研究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進一步推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于網絡知情權的研究非常有限,目前僅有一篇論文以此為主題,其他論文中僅有少量內容涉及,而知情權在政治系統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其次,由于對“政治溝通”概念的理解難以達成共識,從而導致了這個方面研究的嚴重缺失。再次,雖然有關互聯網政治功能的研究的廣度蔚然可觀,但欠缺深度。大部分研究僅停留在描述現象,總結問題,提出建議層面,并沒有更深入的研究,而且,結論和建議少有創新。最后,科學細致的實證研究缺乏。僅有少量研究使用了調查法、內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絕大部分研究停留于描述層面。同時,研究者們提出了大量假設,卻鮮見有對假設的驗證。這些不足有待我們今后的研究者著力改進和推進。
[1] 施拉姆,波特.傳播學概論[M].陳 亮,周立方,李啟,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2] 張 昆.大眾媒介的政治屬性與政治功能[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1):96-100.
[3] 張錦華.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M].臺北:正中書局,1997.
[4] 李尚旗.網絡化政治參與的特點、雙面效應及其應對[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14-18.
[5] 杜 潔.互聯網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及政府應對[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3(1):70-74.
[6] 趙春麗.網絡政治參與:協商民主的新形式[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09-22(B07).
[7] 陳剩勇,杜 潔.互聯網公共論壇:政治參與和協商民主的興起[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3):5-12.
[8] 徐黎明,姜艷艷.論網絡時代的公民政治參與的意義[J].理論探討,2008(4):20-22.
[9] 韋 路,張明新.數字鴻溝、知識溝和政治參與[J].新聞與傳播評論,2007(Z1):143-155.
[10] 安云初.芻論網絡政治參與對執政安全的負面影響[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7(4):19-23.
[11] 郭小安.網絡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新型關系及其影響[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72-76.
[12] 王有加.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民主再思考[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08(6):122-124.
[13] 張恩韶,文軍.論政治參與和政府管理在網絡空間的良性互動[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72-75.
[14] 劉 文.網絡時代政治參與的難題及對策[J].中州學刊,2003(6):14-18.
[15] 陶建鐘.網絡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7(6):100-107.
[16] 賴俊文.互聯網絡助推中國式民主進程[J].現代傳播,2009(2):139-140.
[17] 周志強.“網絡知情權”,一場虛幻的狂歡?[J].人民論壇,2009(5):40-43.
[18] 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權和公共話語——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J].環球法律評論,2002(3):263-273.
[19] 陳力丹.輿論學[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
[20] 劉正榮.從非理性網絡輿論看網民群體心理[J].現代傳播,2007(3):167-168.
[21] 周云倩,吳詩祺.網絡輿論監督的長尾效應[J].新聞愛好者,2009(18):112-113.
[22] 樊金山.網絡輿論視域下的執政創新[J].新東方,2009(3):42-45.
[23] 李雪芳.網絡輿論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J].法制與社會,2009(29):184-185.
[24] 彭 蘭.如何認識網絡輿論中的暴力現象[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08-25(06).
[25] 郭光華.論網絡輿論主體的“群體極化”傾向[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6):110-113.
[26] 楊 治.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的沖突與協調——以司法個案的分析為視角[J].法律適用,2009(1):41-45.
[27] 王 軍,李王穎.互聯網信息時代的輿論監督與司法——以“杭州飆車肇事案”為例[J].現代傳播,2009(4):42-44.
[28] 柴會群.網絡輿論操控食物鏈[N].南方周末報,2009-03-26(A06).
[29] 田群蘭.論網絡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新聞知識,2009(5):60-62.
[30] 李元書.政治傳播學的產生和發展[J].政治學研究,2001(3):68-77.
[31] 淦家輝.中國網絡政治溝通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9.
[32] 陳先紅.媒介近用權:消息來源對政府調控新媒體的影響——以汶川大地震為例[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20-25.
[33] 陳先紅.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聲譽指數測量[J].現代廣告,2007(6):24-28.
[34] 陳先紅.雙重話語空間:公共危機傳播中的中國官方與非官方話語互動模式研究[C]∥第二屆公關與廣告國際學術論壇主題發言論文,香港,2008.
[35]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
[36] 展 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與傳媒[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2(2):123-125.
[37] 蘇晉京.網絡革命與中國公共領域的發育[J].重慶社會科學,2002(3):54-56.
[38] 張如良.虛擬現實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67-70.
[39] 唐大勇,施 喆.虛擬社群抑或公共領域[C]∥鄧炘炘,李興國.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0] 鄭達威.信源擴張與網絡公共領域現狀[J].當代傳播.2005(3):52-54.
[41] 蔣艷芳.兩會博客與公共領域的建構[J].青年記者,2006(10):63-64.
[42] 王君平.虛擬的網絡社區現實的公共領域——淺談強國論壇對公共領域的重構或轉型[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6):68-74.
[43] 陳 鋼.公共領域型變的傳播學觀照[C]∥中國傳媒大學第一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研討會文,2007.
[44] 劉丹鶴.網絡空間與公共領域實踐[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71-74.
[45] 彭 蘭.強國論壇的多重啟示.關注中國[M]∥官建文.縱論天下:強國論壇這五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46] 胡忠青,鄒華華.公共領域視角下的“華南虎事件”[J].新聞界,2008(1):56-58.
[47] 陳先紅.中立的多數:雙重話語空間的第三方立場和公關責任[C]∥第三屆公關與廣告國際學術論壇主題發言論文,澳門,2009.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Functions of Internet in China
WEN Qiong-juan1,2,CHEN Xian-hong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2.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81,Hubei,China)
Internet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kind of new mass medium,which can undertak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social system just like traditional mass media.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internet political functions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power supervi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Internet;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public sphere
G206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06
2010-09-10
溫瓊娟(1979-),女,湖北省南漳縣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武漢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公共關系與廣告研究;陳先紅(1967-),女,湖北省武漢市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傳播學及公共關系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課題(08BXW026)
(責任編輯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