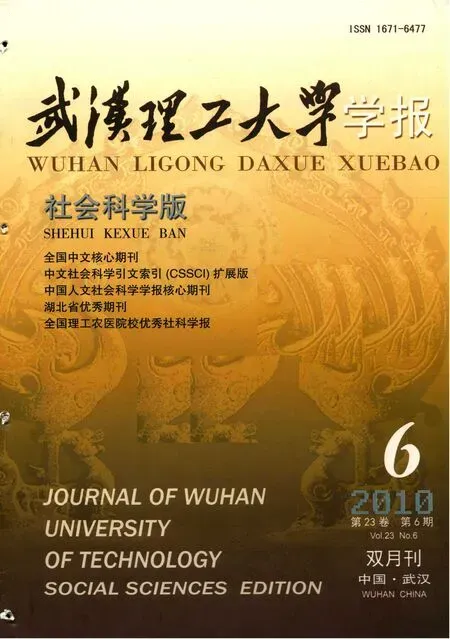論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內(nèi)在生成*
毛明芳
(中共湖南省委黨校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湖南長沙410006)
論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內(nèi)在生成*
毛明芳
(中共湖南省委黨校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湖南長沙410006)
在現(xiàn)代風險社會語境下,技術(shù)產(chǎn)生風險的機制與水平與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相比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是一種客觀風險與主觀風險的集合體。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形成既有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原因,又有社會制度、文化以及個人心理等外在原因。但毫無疑問,科技自身發(fā)展的不足是引發(fā)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根本原因。科學(xué)的不確定性是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內(nèi)在根源;現(xiàn)代科技的“逆邏輯性”是技術(shù)風險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復(fù)雜性是技術(shù)風險產(chǎn)生的時代誘因。
技術(shù)風險;風險社會;不確定性;復(fù)雜性
1986年,德國社會學(xué)家烏爾里希·貝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描述了當今日益擴大的風險社會現(xiàn)實,初步構(gòu)建了風險社會理論框架。貝克、吉登斯等風險社會理論學(xué)者認為,技術(shù)風險(以及因技術(shù)進步而引發(fā)的工業(yè)風險)是現(xiàn)代風險社會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它社會風險的重要成因。吉登斯就曾指出,“風險社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兩項根本轉(zhuǎn)變。兩者都與科學(xué)和技術(shù)不斷增強的影響力有關(guān),盡管它們并非完全為技術(shù)影響所決定。第一項轉(zhuǎn)變可稱為自然界的終結(jié);第二項,傳統(tǒng)的終結(jié)”[1]。
正如風險社會有別于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風險社會中的技術(shù)風險也不同于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中的技術(shù)風險。本文將當代風險社會語境中的技術(shù)風險稱為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理解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需要從“客觀實體派”與“主觀建構(gòu)派”相結(jié)合的視角進行分析[2]。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是指在風險社會語境下,技術(shù)發(fā)展對社會公眾及其所生活的環(huán)境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性以及人們對這種可能性的認知,包括客觀風險與主觀風險兩部分。研究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形成機制,既需要從技術(shù)、經(jīng)濟等“客觀實體”的視角進行分析;也需要從文化、心理、哲學(xué)等“主觀建構(gòu)”的視角進行探討。但無疑科學(xué)技術(shù)自身的不足是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生成的根本原因。
一、科學(xué)的不確定性是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內(nèi)在根源
技術(shù)是科學(xué)的應(yīng)用,科學(xué)的確定性程度影響技術(shù)的風險屬性。傳統(tǒng)科學(xué)觀認為,科學(xué)是確定的,科學(xué)承諾給我們的也是一個確定的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由科學(xué)所塑造的確定性世界中。因此,按照科學(xué)規(guī)律辦事是正確的,遵循科學(xué)規(guī)律,將科學(xué)知識應(yīng)用于技術(shù)實踐是沒有風險的。這種確定性的科學(xué)觀以拉普拉斯理論的誕生而達到極致。拉普拉斯決定論認為,只要知道了世界的初始條件,我們就可以依據(jù)既定的邏輯規(guī)則,推演出今天的發(fā)展現(xiàn)狀以及世界的未來發(fā)展。科學(xué)發(fā)展的未來圖景是明朗的,科學(xué)能夠提供給我們一個確定性的世界。
這種確定性的科學(xué)觀和世界觀在上世紀初因量子力學(xué)和測不準關(guān)系等理論的出現(xiàn)而受到挑戰(zhàn),普里戈金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的誕生表明了西方確定性科學(xué)理論的終結(jié)。按照普里高津的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西方確定性科學(xué)理論是建立在以犧牲“時間之矢”為代價的基礎(chǔ)上的。“從經(jīng)典觀點——包括量子力學(xué)和相對論——來看,自然法則表達確定性,即只要給定了適當?shù)某跏紬l件,我們就能夠用確定性來預(yù)言未來,或‘溯言’過去”[3]3。從今天來看,他們的這一科學(xué)理論既不符合現(xiàn)實,也經(jīng)不起理論的推敲。常識告訴我們,從搖籃到墳?zāi)梗瑥陌滋斓胶谝梗瑫r間一往直前,是不可逆的;現(xiàn)代科學(xué)理論告訴我們,科學(xué)研究不能忽視時間之矢的存在,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是不能等價的,因此,科學(xué)規(guī)律作為對過去科學(xué)事實的總結(jié)與提煉,在今天只有概率意義上的真理性或確定性,科學(xué)理論對于未來的預(yù)言更是令人疑惑的。科學(xué)規(guī)律在本質(zhì)上具有不確定性。
因此,這正如普里戈金所指出的,“人類正處于一個轉(zhuǎn)折點上,正處于一種新理性的開端。在這種新理性中,科學(xué)不再等同于確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無知”[3]5。有學(xué)者將科學(xué)不確定性的來源分為以下五個方面:科學(xué)認識對象的復(fù)雜性和認識主體的局限性;科學(xué)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特征;科學(xué)的范式;科學(xué)的文化和體制特征以及科學(xué)與社會聯(lián)系的加強[4]。
首先是科學(xué)認識對象的復(fù)雜性與認識主體的局限性的矛盾。一方面,整個世界是無限的,人類的認識和實踐能力始終是有限的,人類所認識到的只是整個世界體系當中的很小部分,以對世界小部分的理解和認知,去總結(jié)整個世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預(yù)測整個世界的發(fā)展圖景,是存在顯而易見的邏輯缺失和站不住腳的。因為我們不可能確切地知道世界初始條件的全備信息,更不可能確切知道事物演化發(fā)展的確切路徑,無法去推測世界的未來發(fā)展。人類的科學(xué)知識是建立在不完備的初始條件基礎(chǔ)上的,科學(xué)知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另一方面,整個世界是一個由各個部分共同組成并相互聯(lián)系、相互作用的系統(tǒng),并且,世界是不斷運動、變化、發(fā)展的,世界變化發(fā)展中包含著大量偶然性和隨機性因素。可是,傳統(tǒng)科學(xué)視野中的世界卻是一個“被肢解了的世界”,造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認識缺陷。比如,肥料科學(xué)只研究如何提供作物生長所必須的養(yǎng)料,以提高作物產(chǎn)量,而沒有注意到肥料也可以與土壤發(fā)生相互作用,導(dǎo)致土壤板結(jié),降低土壤肥力;農(nóng)藥化學(xué)只研究怎么樣有效地殺死害蟲,而沒有注意它把益蟲同時也殺死了,更不可能注意到農(nóng)藥在生物體內(nèi)的慢性聚集可以導(dǎo)致人體免疫功能的降低,患病甚至死亡。因此,作為科學(xué)認識對象的客觀世界的復(fù)雜性和變化性,是科學(xué)的不確定性的最基礎(chǔ)的來源;而科學(xué)認識主體的局限性則加劇了科學(xué)不確定性的產(chǎn)生。科學(xué)認識主體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人的感官功能的有限性和知識結(jié)構(gòu)“缺省配置”。人的感官功能的有限性使個人所認識的只是客觀世界或客觀世界作用機制的很小部分;知識結(jié)構(gòu)“缺省配置”使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學(xué)科背景和主觀色彩。概率論、量子力學(xué)、測不準原理和復(fù)雜性科學(xué)都表明了事物固有的以及主客觀互動必然帶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可以說,世界是不確定的,時間是不確定的,建立在此基礎(chǔ)上的科學(xué)知識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其次是科學(xué)的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簡化、受控的實驗方法,模型方法與歸納方法等,一度是科學(xué)突飛猛進的重要“法寶”,但這些方法在邏輯上也不是完備的。就簡化、受控的實驗方法而言,在簡化的、受控制的實驗室條件下產(chǎn)出的知識,在說明和運用于復(fù)雜的現(xiàn)實條件時,就可能出現(xiàn)未預(yù)見到的狀況,產(chǎn)生不確定性,社會變成了一個大實驗室。模型是科學(xué)研究的常用手段,但由現(xiàn)實向模型“翻譯”的過程中,省卻了許多復(fù)雜的條件,所建構(gòu)的模型可能只是一種“虛擬的現(xiàn)實”,與現(xiàn)實狀況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包含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科學(xué)的推理中也包含著不確定性。歸納法“從個別到一般”的邏輯不完整性是顯而易見的。醫(yī)學(xué)研究中的動物實驗的可靠性也是令人質(zhì)疑的。人與其它動物是存在差異的。在醫(yī)學(xué)研究中,由于法律、倫理等多方面的原因,毒性實驗與遺傳實驗只能以動物取代人體,但從動物實驗向人類推廣卻存在著邏輯上的缺環(huán)或缺陷,這種“無視”人與動物區(qū)別的做法肯定是有風險的。
再次是科學(xué)的范式。科學(xué)家對客觀世界的把握,對科學(xué)事實的選擇、觀察,對科學(xué)定律的總結(jié)以及對科學(xué)體系的建構(gòu),都要受到科學(xué)范式的篩選、影響與制約。科學(xué)范式是科學(xué)家無法擺脫的“精神枷鎖”。不管科學(xué)家是否注意到,科學(xué)范式都在潛移默化地發(fā)揮作用。正如有學(xué)者所指出的,“常規(guī)科學(xué)家并不直接研究自然界,而研究由范式所定義的自然現(xiàn)象,也就是由他們的儀器、方法、信念呈現(xiàn)給他們的‘現(xiàn)象場域’”;并且,“作為科學(xué)訓(xùn)練和對范式的信奉的結(jié)果,科學(xué)家感到他們所處理的是‘客觀的’現(xiàn)象”[4]。這種經(jīng)過科學(xué)范式篩選和過濾的“客觀世界”是一種帶有科學(xué)家學(xué)科背景、興趣朝向和價值取向的客觀世界,是科學(xué)家“有色眼鏡”視野中的客觀世界。這種“客觀現(xiàn)象”的客觀性是令人質(zhì)疑的,其中的主觀成分是顯而易見的。
還有是科學(xué)的文化和體制特征。科學(xué)的人文化是科學(xué)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普里戈金在為《確定性的終結(jié)》中文版作序時再次強調(diào)科學(xué)與文化的聯(lián)系是他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科學(xué)不確定性的一個基本方面和重要原因。他認為,現(xiàn)代科學(xué)的科學(xué)化特征日益淡薄,文化特征日益明顯,與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關(guān)系正在拉近,科學(xué)的整體性特征日益增強。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認識到了科學(xué)的價值和文化特征。惠特利認為,科學(xué)活動可分為研究實踐(觀念、規(guī)范、準則)、程序和技術(shù)、說明模型、一般關(guān)注和興趣、價值和信念等五種組分。在他們看來,價值和信念已成為現(xiàn)代科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4]。
最后是科學(xué)與社會聯(lián)系的增強。在當代社會,隨著科技成果應(yīng)用轉(zhuǎn)化周期的日益縮短,科技與社會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科技對社會的支撐和影響作用日益增強。科技的建制化特征日益明顯,科學(xué)技術(shù)正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建制。在社會建構(gòu)論者的視野中,科技與社會是一體的,科技的社會運行是科技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的社會屬性是內(nèi)在于科技自身的。照此觀點,科技社會運行的風險也是科技自身的內(nèi)在風險之一。
非確定性科學(xué)觀告訴我們,科學(xué)知識的不確定性內(nèi)在于科學(xué)規(guī)律之中,科學(xué)知識所描繪的是一幅概率性的圖景,科學(xué)規(guī)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概率性的,按科學(xué)規(guī)律辦事也存在一定的風險。因此,如果無視這種危險性,視科學(xué)知識為完備無缺、拯救人類的“圣經(jīng)”,就會從主觀上降低我們的技術(shù)風險意識,從客觀上減少應(yīng)對風險災(zāi)難的防范與規(guī)避措施,從而加重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可能對我們造成的實際損害。因此,我們既要認識到科學(xué)的不確定性,增強科技發(fā)展的風險意識;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面對科學(xué)的不確定性和技術(shù)風險,我們并非束手無策。“如果我們把不確定性作為我們知識系統(tǒng)的基本建筑材料,我們或許還能構(gòu)建對現(xiàn)實的理解。這種理解雖然本質(zhì)上是近似的,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仍然有助于啟發(fā)我們關(guān)注我們現(xiàn)在——我們大家都生活在現(xiàn)在——所具有的歷史性選擇”[5]。
二、現(xiàn)代科技的“逆邏輯性”是技術(shù)風險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
現(xiàn)代技術(shù)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科學(xué)化的技術(shù)”。這正如有文章指出的,“就技術(shù)風險,或那些源于科學(xué)技術(shù)的社會風險來說,盡管作為日常經(jīng)驗常規(guī)化的傳統(tǒng)技術(shù)也有其潛在的風險,但當技術(shù)獲得了科學(xué)的特性以后,其產(chǎn)生社會風險的機制和水平就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現(xiàn)代社會中的技術(shù)風險主要是指那些由科學(xué)化的技術(shù)或技術(shù)的科學(xué)化而引起的潛在社會威脅”[6]。
首先,“科學(xué)化的技術(shù)”存在明顯的邏輯缺失。科學(xué)技術(shù)一體化是當代科技發(fā)展的重要特征。正如美國技術(shù)哲學(xué)家卡爾·米切姆所指出的,“在知識領(lǐng)域中,正如技術(shù)是應(yīng)用科學(xué)那樣,現(xiàn)在的科學(xué)也是應(yīng)用技術(shù)。粒子加速器、計算機、空間探索等使當代科學(xué)具有獨特的形式”[7]。技術(shù)發(fā)展獲得科學(xué)的特性后產(chǎn)生風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xué)實驗與技術(shù)開發(fā)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通道。在科學(xué)實驗中總結(jié)的知識或證明了的結(jié)果,并不意味著必然可運用于技術(shù)開發(fā)。這是因為實驗室知識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實驗室知識的可控性。實驗室知識都是在實驗室可控制的條件下得出來的,但社會條件是不可控的,將可控條件下的知識運用于不可控的社會,出現(xiàn)不可預(yù)料的情況理所當然。二是實驗室知識的簡化性。在實驗狀態(tài)下,我們通常選取復(fù)雜社會條件中的某些條件進行實驗,而對其它的實驗條件忽略不計。這種簡化對于檢驗?zāi)切╇[藏在現(xiàn)實社會復(fù)雜結(jié)構(gòu)中的因果關(guān)系是必要的,但這種簡化造成了實驗室結(jié)果與實驗室外表現(xiàn)的不可通約性,使之對實驗室外部的現(xiàn)實世界的說明準確性下降。三是實驗室知識的相對穩(wěn)定性。模擬現(xiàn)實世界得出的實驗室知識,它所指向的是實驗發(fā)生時的外部世界,將這種知識運用于社會時,外部世界條件發(fā)生了變化,“不可預(yù)見到的因素”和“新出現(xiàn)的因素”就可能以意外的方式發(fā)揮作用,從而使現(xiàn)實狀況與原有結(jié)果不符,產(chǎn)生技術(shù)風險。四是實驗室知識的相對不完整性。我們在實驗室看到的結(jié)果可能只是某一完整自然變化過程的一部分,或者是某一自然變化過程的一個階段。正如科勞恩所指出的:“研究設(shè)計是當前的,在一些實例中,如臭氧空洞,它們是清晰的以及為公眾所知的;但在另外一些實例中,實驗結(jié)果要等到事故發(fā)生以后才會出現(xiàn);在其它一些實驗中,如放射性實驗,要想得到實驗結(jié)果,細致的調(diào)查必不可少。”[8]因此,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從實驗條件下總結(jié)出來的科學(xué)知識并不是完備的科學(xué)知識,還需經(jīng)受完整的自然和社會條件的檢驗,并可能出現(xiàn)意想不到的情況。如果忽略這一環(huán)節(jié),將實驗室知識直接應(yīng)用于技術(shù)開發(fā),則可能將本應(yīng)該在實驗階段予以規(guī)避和治理的技術(shù)風險演化為社會風險。
其次,科學(xué)研究違背科研邏輯加劇技術(shù)風險的發(fā)生。從前面可以看出,即使將科學(xué)實驗結(jié)果應(yīng)用于技術(shù)開發(fā)和社會發(fā)展,也存在一定的風險。但現(xiàn)代科學(xué)的這種“實驗外移”特征(將科研實驗室移到了人類社會,讓某一地區(qū)甚至全人類承受實驗的結(jié)果)加劇了風險。貝克認為,傳統(tǒng)科學(xué)研究遵循“先試驗后應(yīng)用”、“先研究后生產(chǎn)”的科研邏輯,這樣可以將科學(xué)實驗中的風險局限于實驗室之內(nèi),避免了實驗室風險演化為技術(shù)風險。但現(xiàn)代科學(xué)實驗完全違背了這一科研邏輯,代之以“先應(yīng)用后試驗”、“先生產(chǎn)后研究”的科研邏輯。
烏爾里希·貝克指出:“當今時代科學(xué)研究之邏輯規(guī)律在很多領(lǐng)域已經(jīng)完全顛倒過來了,不再是首先將所研究的對象放在實驗室里進行實驗,實驗成功后再生產(chǎn)出來投入應(yīng)用,而是先投入應(yīng)用,然后再開始觀察、實驗、總結(jié);也不再是先進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投入生產(chǎn),而是先制造出來,然后再進行研究。”[9]這種對科研邏輯規(guī)律的背離與顛倒造成這樣一個事實,即本應(yīng)該局限在實驗室中發(fā)生的風險事件,卻在社會領(lǐng)域中發(fā)生了,造成了不必要的風險影響和損害的擴大化。這不但釀成實際損失,更為嚴重的是,可能會產(chǎn)生技術(shù)風險的放大效應(yīng),給公眾心理造成陰影與恐慌,導(dǎo)致技術(shù)憂慮與技術(shù)恐懼癥狀的發(fā)生。
著名科學(xué)社會學(xué)家科勞恩指出,當今社會正在向一個“試驗社會”邁進。“試驗社會”的現(xiàn)實將現(xiàn)代技術(shù)的風險擴展為社會風險。科勞恩在《將社會作為實驗室:實驗研究的社會風險》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在現(xiàn)代科學(xué)中,有一種越來越明顯地將研究過程及其相應(yīng)風險從實驗室或相關(guān)機構(gòu)直接延伸到社會的趨勢”。“在許多的研究領(lǐng)域,科學(xué)知識生產(chǎn)在實驗室之外進行。這是因為復(fù)雜技術(shù)的操作模式,特別是它們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模式,通常不能在實驗室里面進行。以與環(huán)境發(fā)生相互作用為發(fā)生條件的風險,只有通過在現(xiàn)實世界水平上的執(zhí)行,其結(jié)果才能展現(xiàn)出來。起因于技術(shù)系統(tǒng)的潛在的致命功能錯誤或附加在生態(tài)系統(tǒng)或人類健康上的不能預(yù)料的風險,定義了'相關(guān)知識缺乏'的情形,開辟了真正生活實驗的領(lǐng)域”[8]。甲流疫苗的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按照科學(xué)常理和規(guī)律,疫苗從研究到實用的整個過程,大概需要上十年時間。即使這樣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風險。但是,很顯然,這樣的研制生產(chǎn)程序很難滿足控制當前甲流蔓延的需要。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就省去了許多試驗和檢測手續(xù),直接上市,這就加大了接種者承受風險的概率。到現(xiàn)在為止,已出現(xiàn)數(shù)例接種甲流疫苗致人死亡事件[10]。雖沒有明顯證據(jù)表明被接種者死亡與疫苗有直接的關(guān)系,但也無法找出證據(jù)證明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
三、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復(fù)雜性是技術(shù)風險產(chǎn)生的時代誘因
首先,現(xiàn)代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加劇了風險。技術(shù)從本質(zhì)上來講是一種伴隨著風險的實踐活動。技術(shù)風險具有必然性,而非“異常事故”。并且,技術(shù)越復(fù)雜,則意味著技術(shù)風險越大。社會學(xué)家查爾斯·佩羅認為,技術(shù)具有的兩個特征使技術(shù)系統(tǒng)充滿風險,即“緊密結(jié)合性”和“復(fù)雜相關(guān)性”。如果一個過程是按照以下兩個方式連接起來的,即一個環(huán)節(jié)影響另外一個環(huán)節(jié),并且通常這種影響是在很短時間內(nèi)實現(xiàn)的,那么這樣的過程就是緊密結(jié)合的。在這樣的緊密結(jié)合體中,通常沒有什么時間留給我們?nèi)ヅ懦收希⑶規(guī)缀醪淮嬖诎压收暇窒拊谀硞€部分內(nèi)的可能性,所以整個系統(tǒng)會遭到破壞。進一步說,要使一個系統(tǒng)既松散地結(jié)合又不復(fù)雜化是不可能的。一個既復(fù)雜又緊密結(jié)合的系統(tǒng)發(fā)生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事故是“正常的”[11]。由于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將一個小的設(shè)計疏漏放大為技術(shù)災(zāi)難的事例很多。2009年12月22日清晨上海軌道交通一號線發(fā)生兩列列車側(cè)面沖撞事故,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事故肇始緣于九年前的一個設(shè)計疏漏[12],這一設(shè)計缺陷通過復(fù)雜技術(shù)系統(tǒng)的無限放大,造成整個地鐵管理系統(tǒng)一環(huán)接一環(huán)地出現(xiàn)問題,使系統(tǒng)自身具有的自我糾錯功能得不到發(fā)揮,終于釀成了事故。另外,全球經(jīng)濟危機的爆發(fā)與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不無關(guān)聯(lián)。美聯(lián)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計算機技術(shù)和通訊技術(shù)導(dǎo)致了金融大廈的坍蹋。
這正如風險文化學(xué)者斯科特·拉什對當代技術(shù)資本主義的現(xiàn)狀進行批判時所指出的那樣,“為了執(zhí)行和完成難度很大的確定性判斷,各種門類的專業(yè)系統(tǒng)程序自身設(shè)計超乎尋常的復(fù)雜,然而這種復(fù)雜性可能會將更多更大的不確定性帶入這個世界,可能會導(dǎo)致更大范圍更大程度上的混亂無序,甚至?xí)?dǎo)致更為迅速更為徹底的瓦解和崩潰”[13]。以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的聯(lián)結(jié)形成的復(fù)雜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為例,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加劇了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聯(lián)系,減少了系統(tǒng)之間發(fā)生交換的成本,提高了系統(tǒng)交互作用的效率,促進了聯(lián)系的擴大化、密切化、復(fù)雜化。但是,技術(shù)系統(tǒng)網(wǎng)絡(luò)化的另一不可避免后果就是風險的擴大化。通過技術(shù)系統(tǒng)中介環(huán)節(jié)的聯(lián)接,任何單一部門、單一環(huán)節(jié)的風險都可以演化為系統(tǒng)風險,任何局部風險都可以擴大為地區(qū)甚至全球風險。擁有高超技術(shù)的電腦“黑客”可以通過識別技術(shù)系統(tǒng)的某一缺陷,通過對系統(tǒng)某一環(huán)節(jié)的入侵而導(dǎo)致整個部門或地區(qū)電腦系統(tǒng)的全盤崩潰,造成災(zāi)難性后果。
其次,現(xiàn)代技術(shù)的自主性特點加劇了風險。技術(shù)本是人類實現(xiàn)自身目的的手段,是人類追求福祉的工具。但是工業(yè)革命以來,技術(shù)先進和經(jīng)濟效益成了技術(shù)發(fā)展的唯一目的,技術(shù)的人文本質(zhì)和人文目的被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所遮蔽和遺忘。因此,在現(xiàn)代社會,追求更先進更完善的技術(shù)成為社會公眾的一種信條,人們潛藏著一種刻意追求技術(shù)進步的思想傾向,使得技術(shù)手段成了“技術(shù)目的”,人成了實現(xiàn)技術(shù)目的的工具。這種擺脫人類目的和人類控制的技術(shù)發(fā)展,必定會脫離既定的“技術(shù)軌道”,增加技術(shù)的風險。特別是現(xiàn)代技術(shù)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提高了技術(shù)的自主性和不確定性,加劇了技術(shù)風險的發(fā)生。“現(xiàn)代技術(shù)創(chuàng)造設(shè)計的是高度專門化的復(fù)雜技術(shù)系統(tǒng)。它們是一個具有自身規(guī)律的領(lǐng)域,只有人們愿意服從其固有規(guī)律的時候,它們才會產(chǎn)生并發(fā)揮出預(yù)期和非預(yù)期的結(jié)果。它們與人相分離,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而存在,深刻地影響著現(xiàn)代社會的形態(tài)和面貌”[14]。
再次,“技術(shù)升級”消除技術(shù)風險的非徹底性。常識告訴我們,技術(shù)不但是引發(fā)現(xiàn)代社會風險的根源,同時又是現(xiàn)代社會風險的根本治理對策之一。這是因為,技術(shù)本身是一個不斷發(fā)展和進步的過程,技術(shù)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還需要通過技術(shù)進步和升級來解決。正是由于這種科學(xué)知識及其技術(shù)應(yīng)用具有的“反身性”,越來越多的新技術(shù)被用于處理其它技術(shù)所產(chǎn)生的危害,比如運用污染治理技術(shù)去處理工業(yè)生產(chǎn)和生活中產(chǎn)生的大量污染物,運用水的凈化技術(shù)去處理工藝過程產(chǎn)生的廢水,運用殺毒軟件技術(shù)來預(yù)防和治理電腦病毒的入侵,運用安全檢查技術(shù)來預(yù)防各種恐怖主義事件的發(fā)生,運用反導(dǎo)彈技術(shù)來阻止和對付導(dǎo)彈的來襲。可以說,以技術(shù)手段來治理技術(shù)風險和技術(shù)問題的現(xiàn)象在我們生活中比比皆是,并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效果,因而在實踐中產(chǎn)生了處理技術(shù)風險的一種科技樂觀主義思想,即認為科學(xué)技術(shù)所引發(fā)的風險和產(chǎn)生的問題,唯有通過科技的進步才能解決,只有科技才能將我們從科學(xué)產(chǎn)生的罪惡中拯救出來,較低級的技術(shù)產(chǎn)生的問題可通過技術(shù)的升級,借助于技術(shù)的高級化可得以解決;人類完全有能力不斷追求新的技術(shù),并通過技術(shù)的不斷進步為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開辟更多的領(lǐng)域,創(chuàng)造更多的機會。
但是,事實并非完全為人們所料,技術(shù)升級在解決一部分技術(shù)問題時,往往同時又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以技術(shù)手段來規(guī)避和治理技術(shù)風險的過程是不徹底的,有時甚至是徒勞的。比如說,污染處理技術(shù)自身會發(fā)產(chǎn)生二次污染問題,有時甚至?xí)惹按挝廴靖鼑乐兀粴⒍拒浖夹g(shù)只能識別和殺死已列入軟件包中的常規(guī)病毒,給高級別的病毒留下了可乘之機;安全檢查技術(shù)難以應(yīng)對恐怖分子精心設(shè)計的“體內(nèi)炸彈”;反導(dǎo)彈技術(shù)系統(tǒng)所構(gòu)筑的安全屏障也是令人質(zhì)疑的。后現(xiàn)代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用技術(shù)手段解決技術(shù)問題的“非徹底性”。他指出,就技術(shù)而言,有了化肥生產(chǎn)技術(shù),就解決了提高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的問題;有了建壩蓄水技術(shù),解決了穩(wěn)定水源的問題;有了水凈化技術(shù),解決了由于化肥未被作物吸收而污染水源的問題;運用磷肥,解決特殊建造的去污工廠的污染問題;緊接著又需要一項去除那些富含磷酸化合物的水庫中的毒藻的技術(shù)……難題的解決又導(dǎo)致了難題的產(chǎn)生,又需要新的處理技術(shù)[15]。因此,如果說提高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技術(shù),穩(wěn)定水源技術(shù)是一般工業(yè)技術(shù),可能引起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的話,那污染水源凈化技術(shù),去除毒藻技術(shù)就可以算作一種名符其實的“生態(tài)技術(shù)”,但是,顯而易見,“生態(tài)技術(shù)并非有利生態(tài)”,甚至可能產(chǎn)生破壞性影響。因此,這些不斷進步和發(fā)展的復(fù)雜技術(shù),在解決原有風險問題的同時,可能會將更多更大的風險帶入這個世界,使我們真正置身于后果嚴重的“風險社會”中。正如德國社會學(xué)家U.施曼克指出的,經(jīng)過修正的技術(shù)本身仍然是風險的生產(chǎn)者,技術(shù)水平的升級不僅不會消除風險,反而會帶來風險水平的相應(yīng)升級[6]。
綜上所述,風險是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內(nèi)在屬性。所有的技術(shù)都蘊含風險,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風險技術(shù),這是由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特點所決定的。試圖開發(fā)一種只對人類有利的無風險技術(shù)的想法是徒勞的。但我們可以通過技術(shù)的生態(tài)化與人性化轉(zhuǎn)向,來達到從科技自身出發(fā)規(guī)避技術(shù)風險和降低風險損失的目標。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話題。
[1] 安東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爾森.現(xiàn)代性——吉登斯訪談錄[M].尹宏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191-192.
[2] 宋明哲.現(xiàn)代風險管理[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3:21-26.
[3] 伊利亞普里戈金.確定性的終結(jié)[M].湛 敏,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4] 徐 凌.科學(xué)不確定性的類型、來源及影響[J].哲學(xué)動態(tài),2006(3):48-53.
[5]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知識的不確定性[M].王日丙,譯.濟南: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2006:2.
[6] 趙萬里.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風險[J].科學(xué)技術(shù)與辯證法,1998(3):50-55.
[7] 卡爾米切姆.技術(shù)哲學(xué)概論[M].殷登祥,譯.天津:天津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9:中文版序言.
[8] Wolfgang Krohn,Johnnes Weyer.Society as a La-boratory:the Social Risk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1994(6):173-183.[9] 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yè)社會到風險社會[C]∥王武龍,譯.薛曉源,周戰(zhàn)超主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5.59-134.
[10] 甲流疫苗致4人死亡副作用隱患不可小視[EB/OL].(2010-02-08)[2010-0610]http:∥www.shengyidi.com/news/d-117884/.
[11] 哈里斯等.工程倫理:概念和案例[M].叢杭青,等,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06:122.
[12] 上海地鐵撞車事故緣于9年前疏漏[EB/OL].(2010-03-18)[2010-06-10]http:∥news.cn.yahoo.com/10-01-/346/2jv7f.html.
[13] 斯科特拉斯.風險社會與風險文化[M]∥王武龍,編譯.李惠斌,主編.全球化與公民社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298-320.
[14] 高 偉,陳 華.雙刃利劍——百年科技利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15] 齊格蒙特鮑曼.現(xiàn)代性與矛盾性[M].邵迎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19-22.
On the Inherent Shaping of Modern Technology Risk
MAO Ming-f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S,The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ee,Changsha 410006,Hu'nan,China)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risk society,the mechanism and level in technology risk have changed greatl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society.The modern technology risk is the aggregation of objective risk and subjective risk.The risk i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elf on the one hand,and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regime,culture and personal mentality on the other hand.But out of question,the de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radical cause.The uncertainty of science is the inherent origin of modern technology risk,the non-logic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important cause,and the technological complexity is the inducement of the risk.
technology risk;risk society;uncertainty;complexity
B028;N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01
2010-06-18
毛明芳(1976-),男,湖南省益陽市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哲學(xué)博士,主要從事技術(shù)哲學(xué)與技術(shù)風險理論研究。
2010年度湖南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課題“現(xiàn)代技術(shù)風險的主觀建構(gòu)與文化規(guī)避研究”
(責任編輯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