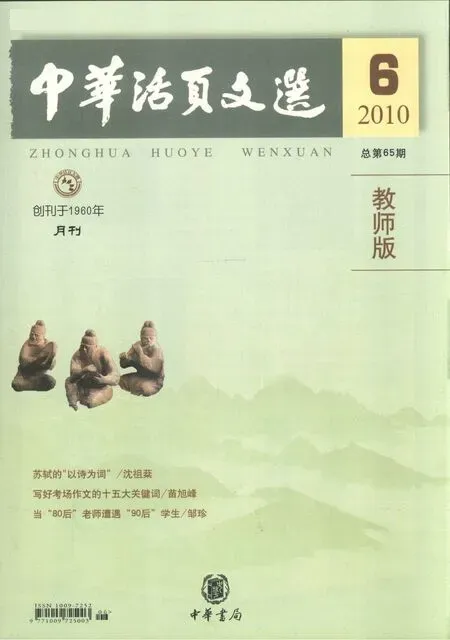懷念一位大學者——錢鐘書
■高 莽
懷念一位大學者
——錢鐘書
■高 莽
大學者錢鐘書離開了神州,愛他敬他的大地頓時出現一塊空白。這個空白也許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才能補上。
錢先生是老前輩,他的學術成就,為人功德,社會早有評定。晚年不肯濫用時間,閉門謝客,婉絕采訪,澹泊明志,但對新事物極其注意,對后生成長關心備至。僅僅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命運的安排,我有幸接觸過這位老人,聽過他的講話,按照他的意思辦過幾件事,從此在生活與工作中竟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的恩澤。
回憶中不可或缺的人
回憶錢先生時,我的腦子里總有另一個人和他相隨相伴。她無時無刻不和他在一起。她就是他的夫人楊絳(楊季康)先生。他們是一個分不開的組合體。無論探討深淵的學術問題,還是處理平凡的日常瑣事,二人總是合商共議。
他們從大學相識,到錢先生只身先逝,在60多年的漫長人生道路上,不管風吹浪打,命運如何擺布,他們榮辱與共,同舟共濟。
錢楊是同道是知音。1941年,錢先生出版《寫在人生邊上》一書,扉頁上特注明是“贈予季康”的。他的《圍城》也是獻給楊絳的。是楊絳不斷地督促,替他擋了許多事,讓他省出寶貴時間,使他在繁忙中完成傳世奇書。40年后,楊絳回憶錢先生創作《圍城》的過程時說,他們二人每天晚上在一起閱讀他寫成的稿子:“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么,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么寫。”
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做到心照不宣,相互理解。錢先生再版《圍城》,楊先生在一位熱心友人的再三慫恿下寫了一篇記述他寫作那部小說時的歷史背景與經過,文章寫好后,又是經那位友人多次催促,三年之后才發表出來。她說:“我既不稱贊,也不批評,只據事紀實。”錢先生認為楊先生的記述“沒有失真”。她的《記錢鐘書與〈圍城〉》一文,是研究錢先生小說創作的極有價值的第一手文獻。
我珍藏著楊先生寫給我的一封信。信是楊先生寫的,而信封是錢先生的手筆。可見他們連寫信時也在一起。
錢先生是楊先生的書法老師。年逾七旬的楊先生拿起毛筆練字。她請錢先生當教員,錢先生慨然接受,但提出嚴格要求:學生每天必須交作業,由他判分,認真改正。錢先生審批楊先生寫的大字,一絲不茍或判圈兒或打杠子。楊先生嫌錢先生畫的圈不圓,找到一支筆管,讓他蘸印泥在筆劃寫得好的地方打上標記。楊先生想多爭幾個紅圈兒。錢先生了解楊先生的心理,故意調侃她,找更多的運筆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我見過楊絳先生的大楷“作業”,她很重視錢先生的批示。二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純真如初。
錢楊觀點相同、語言相近、志趣相投,彼此絕對信賴,在任何情況下都相互支持與贊同。十年“文革”浩劫期間,我們都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錢先生被封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無端地攻擊與誣陷。楊先生全力地維護他,安慰他。造反派把憤怒灑在楊絳頭上,批斗她給錢鐘書通風報信。楊絳沒有感到屈辱。反而認為值得自豪。這位看起來弱不經風的女性用堅定的語氣說,她是通風報信了,因為她能擔保“錢鐘書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為他的行動負責”!她的聲音不高,每句話卻擲地有聲,震撼人心。這種崇高的表現,遠非每一對夫婦能夠做到。
錢先生臥病住院期間,楊先生幫助他解脫痛苦,給予安慰。“鐘書仍重病。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前,妻在后’,錯了次序就糟糕了。”這是楊先生在1995年5月18日信中的話。話中的深情,令任何人不能不為之感動。多么偉大的女性!多么崇高的聲音!如今,錢先生確實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許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錯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錢先生在病中,他們的愛女逝世。這是何等沉重的打擊,全由楊先生承擔了。錢先生走了,可是我總覺得他仍然和楊先生在一起,而楊先生的整個身心也在守護著錢先生。她身單力不薄,年老意志更堅強,她絕不允許誰來欺侮錢先生,不管是在錢先生生前還是身后,她都一如既往。
錢楊二位先生也有不同。錢先生是一位思想家、科學家。他用一生的努力,揭示著證明著一個個真理。中外古今,哲學、藝術、文學被打通融匯、通感、靈性、詩畫的命題也清晰明白。淵博的學識,準確的譬喻,透徹的論證,從過去現在到將來,都被人心悅誠服地認同。他的結論,將不斷地得到人們的重復驗證。而楊先生,則是一位藝術家、文學家,她用一支普普通通的筆,創造出來許彥成、姚宓、李君玉、張婉如等一群人物,在是與不是,似與不似之間漫步,也得與方鴻漸比肩而立。楊先生在許多平白淺淡的散文中,寫了錢鐘書,寫了父親、姑姑、妹妹,也寫了許多普通的人,他們都已成了眾口樂道的熟人。她還為小癩子、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從外國文學神壇上走進神州大地鋪設了多彩之路。楊絳先生作為一位文學藝術家,她所從事的勞作,是任何人不能重復的。這就是他們二位的不同。但更為奇特美好的是,錢楊二位在生活中,又恰恰相反,錢先生在用功之余,興致所致,頑皮淘氣,大有藝術家的脾氣。楊先生則冷靜認真,一絲不茍,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條,地道是一位科學家的性格。這真是郎才女也才,女貌郎也貌,天作地設的夫妻啊!
錢楊二位先生是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但他們保持并發揚了中華民族夫妻關系的傳統美德。他們是我們后人永遠應當學習的榜樣。
為錢楊二老畫像
楊先生在外國文學研究所期間。我在《世界文學》雜志編輯部工作,為了處理一些稿件,有時需要請教楊先生。錢先生在中國文學研究所任職,那時,他經常來看望楊先生。兩位學者總在一起,形影不離,令人羨慕與贊嘆。
我一直想把他們畫出來,不是畫單獨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在一起。可惜總也沒有機會。
“文革”期間、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紛紛被趕到河南信陽去走“五七”道路,任聽軍宣隊擺布,今天蓋房子,修豬圈,明天開批斗會。這些知識分子什么都可以去干,就是不讓他們真正研究學問。
政治運動第一。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圈在干校內的知識分子除有限的幾種政治書報之外,什么也不許看。他們被強制地與書隔緣。不看書,不了解外部世界,還稱得起什么知識分子?天長日久,批斗會也開得有氣無力了。那一陣晚飯后,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們三三兩兩地到干校附近的野外去散步。活動天地不大,迎面總會遇見熟人。我常常看到錢楊二老的身影。在眾人當中只有他們顯得無比親密,因為大多數人的感情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已被扼殺了。他們二人的影像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床鋪上,興致所致,默畫了他們的背影。夸大了錢先生的笨拙可笑的體態和楊先生親昵的嬌小身姿。二人并肩漫步,滿身人情味。朋友們傳看,說這是漫畫,認為畫中抓住了他們的特點。不知何人把那幅漫畫拿給了錢楊二位。我得知后真有些害怕,怕惹得二老不高興,怕說我丑化了他們,更怕別人上綱上線說我宣揚資產階級愛情觀,給自己惹來新的麻煩。我心中犯嘀咕,因為早在1950年,《文藝報》就曾以 6個版面載文專門批判過我的漫畫,說我丑化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我心有余悸。后來欒貴民告訴我:二老看后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稱贊了幾句。
我的膽子大了些。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又給錢楊先生畫了幾幅速寫像和漫畫像。漫畫像曾刊載在《南方周末》上,有些地方報刊還轉載了。我將自己畫的幾位文學前輩的漫畫像送給二老聽取意見。楊先生告訴我:何其芳的畫像最好。其次是俞平伯。她的畫像比錢鐘書的好。他還指出:畫的她和錢先生都“偏向美化”,絆住了我的畫筆。這里需要做一點說明。自從我因漫畫挨批以后,再不敢畫漫畫。隨著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的開展,我學乖了,只美化不丑化。有一次,我媽媽對我說:“你畫男人時,畫得年輕一點;畫女人時,畫得漂亮一點。”她的話甚靈,每次按她的信條作畫時往往博得被畫人的肯定和贊美。這話傳到了錢楊二老耳中。有一天,欒貴民告訴我:“有人說‘按他媽媽的話畫下去,他作不出真正的藝術作品來。’”他沒有指明“有人”是誰,但我可以想像這話出自何人之口。這也正是為什么二老肯定我的漫畫而否定我的美化的原因。“我很感激二老一針見血的批評。他們的話,我銘記在心。可惜長期的禁錮使我已放不開手腳了。
學者的書房
198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代表《世界文學》雜志去向錢先生邀稿。我當時還懷抱著一顆私心,想趁機觀賞一下錢先生這位滿腹經綸、學貫中西、國內外遐爾聞名的大學者的書房。
三里河。小樓的三層。錢楊兩位的寓所。我準時走進了他們的家門。
錢先生諳通多種西語,著述中旁證博引古今中外名篇。據專家考證,僅《管錐編》一書中就引證了幾千名文人的話,提到近萬篇作品。我相信這樣兩位大學者家里到處會是書。他們家就是書的世界:軟皮線裝的中文古籍,硬皮燙金的厚實洋書,大本小本,無所不有。主人即使不讓我翻閱,用眼睛瞄一瞄書脊也很過癮。
我們在客廳里談完了工作。我怯怯地提出想參觀一下他們書房的希望。二位老人笑了。錢先生當時坐在一張寫字臺的后邊。他扭頭看看背后的兩個書柜,意思:這就是我的書房。楊先生還領我參觀了一下他們的住宅、寢室、女兒的房間,還有一間作為餐室的小房間。每個房間都有一些書,但不多。
其實,客廳就是書房。他們家中就那么些書,好像還是字典一類的工具書,少得驚人。我感到愕然。
也許正是這種意外的反映使我突然領悟到一個真理:真正的學者不僅博覽群書,更善于啟動頭腦的全部功能。知識不是在書柜上,書本里,而是像電腦似的儲存在自己的頭腦里。他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只要需要。呼之即出,寫作時信手拈來。錢先生就是這種大學者。
錢楊似乎沒有藏書的習慣。不過我從他們的著作中知道,他們沒有書又活不下去。楊先生在《干校六記》中記錄了他們二人這樣一段對話。
“默存(即錢先生——筆者注)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真的,什么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這是錢先生和楊先生的肺腑之言。
我在他們的書房里仿佛受了一次理智上的洗禮。認識到真知不在于藏書多少,而在于書房主人的內心充實。錢楊二位不用書籍裝點自己的房間,沒有讓成堆的書籍擠掉生活的空間,更沒有讓現成的書籍束縛住自己的頭腦。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了頭腦的清醒和內心的自由。
他們的作品,無論是鴻篇巨著還是散文詩詞,含金量極高。
錢先生和電腦
錢先生家中沒有電腦,自己也不使用電腦,然而,他深明電腦的作用和發展前途,便大力倡導電腦事業,并多方予以支持。每次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開會,他必然要抽出時間了解一下計算機室的工作。他不肯擔任任何單位的“顧問”,唯獨計算機室例外。他不僅接受了“顧問”的委任,而且時時顧問計算機室的事業。
改革開放初期,錢瑗訪問英國回來后,向父母介紹了國外使用電腦的情況,談及英國用電腦儲存莎士比亞資料與查閱資料的各種功能。錢先生立刻意識到這一新鮮事物的意義,便建議中國文學研究所成立電腦組,即后來的社科院直屬下的計算機室,并為之以英文命名,希望其走向世界。
為了發展電腦事業,使其有效地為中國文學研究服務,錢先生沒有少費心血。他以其不尋常的思辯方法提出首先要把我國文學史中的精品全唐詩全部輸入電腦,進而解決如何查閱的問題,用何種數據格式,怎樣通過一個字能調出全詩,等等。錢先生在編制程序上的意見成為計算機室的指導思想。錢先生的指示具體、有遠見,使電腦工作者都感到驚奇。在他的指導下,《全唐詩》等課題,獲得了科研工作國家科技進步獎。成為當時使用電腦處理中國古典文獻的先行隊伍。錢先生的原則指導,是迄今為止解決這個領域的基本原則。這不禁使我聯想起,早在1946年《圍城》首次使用“電視”這個中文詞,錢先生那種對未來的微笑。他在病中,為中文古文獻的數字化成果。又起了一個準確而響亮的名字——“電書(Telebook)”,這也必為世人所認可。
錢先生在經濟上對電腦工作者也予以支持。他幾次將自己的稿費,如 《寫在人生邊上》《人·鬼·獸》等作品的稿費,全部支持了這項事業。
由錢先生提議,1992年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曾在汕頭舉行過中文電腦研討會。國內外有60~70人參加研討會,成績斐然,新聞媒介有所報道。
1993年準備再舉行一次研討會。總結前次研討會的經驗,代表們可以攜帶自己的作品來參加會議。對參賽的作品還準備進行評比,并向成績突出的前10名頒發獎狀等。錢先生建議設立“倉頡獎”,因為中文電腦的作用似倉頡造字。為了突出前三名,還建議另加獎品。籌委會考慮再三,決定前三名增獎國畫一幅,請錢先生在畫上題字,以示重視。錢先生同意了。
由于種種原因,研討會沒有開成。然而錢先生的題字對鼓勵中國電腦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錢先生修改題詞
中文電腦研討會籌委會讓我來完成作為獎品的三幅畫。我畫了三種不同的倉頡像,我想為倉頡畫像寫幾句話。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文字,可是自己沒有足夠的把握,交給欒貴民修改。我沒有想到他把這段文字呈送錢先生審閱。如果我早知道他這樣做,我會用一張好紙,規規矩矩地把題字寫出來。
過了幾天,他打電話找我,說有要事相商。我匆匆來到他的辦公室。他面無表情地把我的文字還給我。我的心砰砰在跳。“你看吧!”他說。當我打開那張紙時,發現句句有改動。我立刻意識到這是好現象。他說:“你細細看看。”當我仔細看了以后,認出那是錢先生的字跡。我一下子怔住了,接著高興地叫了起來。他黝黑的臉上這時才露出憋了很久的喜悅。這么一般的文字,竟請錢先生浪費精力與時間去改,我深感內疚。
錢先生改后的文字:
“倉頡造字,歷史傳說由來久矣。雖屬神話,而其實質蘊含開拓與創造之旨。所謂倉頡其人者,觀日月山川之形,察鳥獸蟲豸之痕跡,觸類啟悟,獲得表達思維之記號或方式。于是漢字萌生,混沌轉為清晰,人之知力征服自然,能使‘天雨粟,鬼夜哭’,人類文明于是乎始。偉哉倉頡!”
遵照錢先生的旨意,我把這段題詞寫成了條幅。籌委會又把這段文字印在專供會議參加者用的T恤衫上。
那次研討會雖然沒有開成,但錢先生改動的題詞卻成了歷史的記錄。
兩幅小畫
錢先生在三幅倉頡畫像上題了字。對一幅畫題字他感到不滿意,于是在另一張小塊宣紙上重寫了兩遍,蓋了章,并囑咐田奕裝裱時用后題的字代替原畫上的字。但我覺得挖補錢先生的題字,可能會招來別人的懷疑,甚至不明作品的真偽。我建議重畫一幅,麻煩錢先生再題。
錢先生后來題的字,保留在我手中。我常常拿出那塊不大的宣紙思考。有一天,頭腦里忽然閃現一個念頭,何不借用錢先生的字,補畫成小品呢?于是,我把那張小紙按題字分成兩塊,在每一塊上又畫了兩種很小的倉頡像。一幅是倉頡在觀看龜甲圖案,一幅是倉頡站在荒原中思考。在后一幅小畫上我有意把他畫成類似耶穌。我想,倉頡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決不亞于耶酥。我還利用錢先生試筆時留下的未寫完的字作為草叢上飛舞的昆蟲。
過了一陣,我覺得小畫很有情趣,便把原畫拍成照片,寄給楊先生,如楊先生愿意,可拿給錢先生看一看。我想這類趣事或許能給病中的老人帶來些愉快。當時錢先生正在醫院治療。1995年5月18日,楊先生寄給我一封信:“收到來信并附照片,已帶往醫院給鐘書看。他十分欣賞你的兩幅小畫以及‘草叢上飛舞的昆蟲’。”
捧讀楊先生的來信,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動,熱淚奪眶而出。默默祝錢先生早日康復。
錢先生的風范
錢先生高高的身材,戴著一幅深度近視鏡,犀利的目光,碩大的額頭,整天躲在書房里作學問。如果有事,他總是認真地靜聽對方講話,從來不打斷言者的思路。錢先生喜歡交談,一出口,必語驚周圍。他臉上總是浮著會心的微笑,他身邊總有楊絳的陪伴。
從五七干校回京以后,錢先生格外珍惜時間,他覺得白白浪費的光陰太多了。他有很多學術課題待深入探討與解決。因此,他謝絕采訪,電視臺請他上鏡頭,他退避三舍,社科院決定為一批老學者們錄相,他婉言回避。
社會上廣泛流傳著錢先生的一句名言:“假若你吃了雞蛋認為不錯,何必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這句話最早是楊先生透露出來的,是為了謝絕一位外國記者的采訪而說的。
但,錢先生決不是毫不講情面的人。他那濃濃的深情,在他的著述中彌漫于字里行間。
晚年,他也接見過為數不多的外國客人。譬如,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這位作者來我國訪問時,出于舊情,他們見了一面。錢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在自己的文章中已提及過莫拉維亞。順便提一句,錢先生在很多領域是超前者。我們外國文學工作者現在探討的不少問題、一些人物,他在三、四十年代已經有所論述。
俄羅斯漢學家索羅金要求拜見錢先生,錢先生在家中接待了這位學者。記得錢先生說過:索羅金是《圍城》的俄譯者,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在國內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錢先生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種文字,可惜不懂俄文,否則他也許會對俄譯本和俄羅斯文學有所評論。
有一次,聽錢先生談作家的使命。他說,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誘惑,要有一支善于表達自己思想的筆,然后拍了拍肩頭。他看著我茫然的表情,想到我可能沒有理解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解釋:“要有鐵肩膀,能扛重擔。”然后概括地說三個詞:頭腦、筆、骨氣。
《世界文學》雜志準備刊出一篇外國人贊揚錢先生的文章。錢先生得知后,希望我們不要登載。他說:“你們若一定堅持自己的編輯計劃,我意改成一條小消息就算了。”要求在《世界文學》上刊出自己的譯作或評論自己作品的譯者大有人在,而建議不刊登的人廖廖無幾。
我與錢先生接觸有限,但每次都能聽到一些精辟的見解。
有一次,錢先生談到“開放”政策。他說:“開放的政策有兩種。一種是殖民地式的;另一種是有主見的。所謂殖民地式的開放政策,就是外國說什么好,就跟著人家說什么好。我們要施行的開放政策要有氣魄,有自己的觀點。”
錢先生80壽辰時,有一些單位要為他祝壽。先生聞訊后,堅決不同意。錢先生講過一句極富哲理的話:“老去增年是減年。”他還提過一件事,有人準備為他父親開紀念會,被他婉言辭謝。同時,他給朋友寫信,說:“何苦來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閑人,說些不痛不癢的廢話,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錢。”這是真理,是實話,更是人生的觀點。可是他的話被人給捅出去,又被人誤傳。其實這句話有普遍意義,真正做到需要有膽識。
錢先生臨終的遺愿是: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退花籃花圈,不留骨灰。忠貞的伴侶楊先生嚴格地執行了錢先生的要求。
1998年12月21日,楊先生帶著幾位親友在火化爐前鞠躬三次,不聲不響地送走了這位20世紀的偉大學者。
錢鐘書先生走了,但他的學術成果與為人的風范永遠地留在人間。
(胡小明選自李明生、王培元《文化昆侖:錢鐘書其人其文》,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