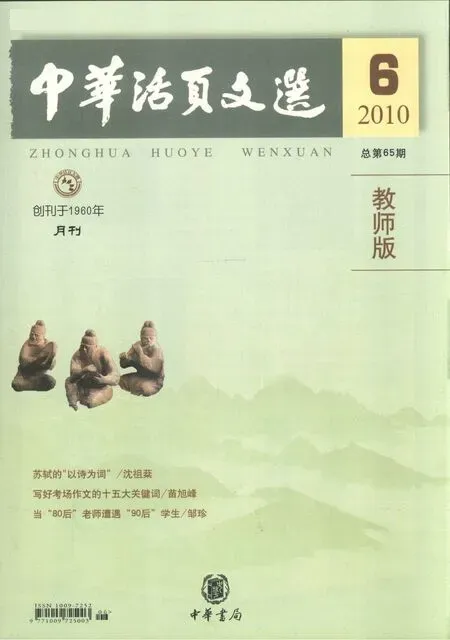蘇軾的“以詩為詞”
■ 沈祖棻
蘇軾的“以詩為詞”
■ 沈祖棻
一個大作家總是以自己的創作特色將他自己和其他作家區別開來。同時,創作特色顯然并不是什么單一的東西,它們往往以自己豐富復雜的呈現,反映了作家的精神面貌和藝術手段的豐富復雜。但是,在一個作家身上所具備的許多創作特色之中,其中又必然有一種是主要的,對這個作家來說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么,蘇詞最主要的創作特色是什么呢?歷來的作家和批評家都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是以詩為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載晁補之、張耒云:
(東坡)先生小詞似詩。
陳師道《后山詩話》云:
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云:
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云:
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
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劉熙載《藝概》卷四云: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
上舉這些大家所熟知的材料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那就是:無論他們對于蘇軾以詩為詞所采取的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但意識到這一點是蘇詞主要的創作特色,卻是共同的。
肯定了這一點,我們就很自然地要提出兩個問題。其一,人們根據什么理由在蘇詞的許多創作特色之中,突出這一點來加以注意和褒貶呢?其二,所謂以詩為詞,又包含了一些什么具體涵義呢?關于前者,可以從對于詞史的回溯上得到解釋。關于后者,蘇詞本身就可以給人們作出確切的說明。
詞,本來是唐代人民群眾所創造的一種新的音樂歌詞。和其他樣式的民歌一樣,它必然地會廣泛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映當時人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況和愿望,當然其中也包括了男女愛情方面。現存敦煌卷子中的作品,雖然為數不多,但是大體上也可以看出其中消息。作家們,無論他們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總是要向民間的新興文學樣式學習,并在其中吸取養料的。這,實質上也就是由民間詞上升為文人詞的歷史過程。這種學習,雖始于中唐,但到晚唐、五代才獲得較大的發展。由于當時政治混亂,社會黑暗,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以及統治者內部之間的斗爭都日趨激化,多數作家們的精神狀態都陷入頹廢空虛;加以某些地區(如黃巢起義以前的長安以及十國中的西蜀、南唐)暫時茍安的政治局面和畸形發展的都市繁榮,又為這些作家(特別是一些上層的貴族,如《花間集》中某些詞人和南唐二主、馮延巳等)提供了享樂的條件,因而在他們通過其創作實踐來發展和提高這種音樂歌詞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按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美學趣味片面地突出了其中有關男歡女愛、別恨離愁的部分。這就使得這種樣式,本來和其他樣式一樣,可以反映廣闊的生活面的,變得反映的范圍相當狹窄,似乎詞只能是剪紅刻翠的“艷科”,或者旖旎溫柔的“情語”了。從溫庭筠到柳永,這種“艷科”、“情語”,在詞中,竟成為普遍的和最有勢力的題材和主題。作家們在填詞的時候,幾乎完全排斥了,甚至認為應當排斥廣闊的生活畫面和比較重大、嚴肅的內容,否則就要被認為不合色,不當行。在這一段時期中,如李殉、孫光憲對風土的歌詠,鹿虔扆、李煜對故國的哀思,范仲淹寫塞上風光,柳永寫都市繁華,對多數詞人們所拘守的狹窄范圍有所突破,并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但沒有能夠改變它總的傾向。直到蘇軾,以詩為詞,才比較徹底地打破了這個相當悠久的,但并非健康和合理的傳統,使讀者、歌者和其他作者一新耳目。這自然不能不算是一項重大的革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還意味著恢復了民間詞無論從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段上都能夠比較廣闊地反映生活的那種古老而優良的傳統。試想,這怎么能夠不成為詞壇上令人十分重視和關切的事態呢?
現在,可以進一步探索一下以詩為詞的具體涵義究竟是什么?
我認為,以詩為詞,首先指的是詞所反映的生活內容的擴大。蘇詞中所描寫的情事,當然有許多是和其以前的詞人相同的。但是,許多被別人認為不適宜于用詞來描寫的情事,蘇軾也毫無顧忌地將其寫入詞中來,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交游的聚散、州邑的去留、自然景物的欣賞、農村生活的寫照,甚至打獵、參禪等,都是前人詞中反映較少或完全沒有涉及的。另外,在少數篇章中,他還隱約其辭地表現了自己的社會政治觀點和對于時政的看法,雖然這一方面還發展得不夠充分。總的說來,蘇詞中一些題材和主題,是從溫庭筠以來的詞人的作品中所找不到的,但卻是前代詩人的作品中所常見的。劉熙載說,蘇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可能還不能完全落實,然而這位批評家所指出的蘇軾以詩為詞的具體涵義的一個方面,顯然是正確的。
被蘇軾所擴大了的詞的內容,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藝術手段,首先是語言。因此,以詩為詞的具體涵義,就不能不將以詩的語言來寫詞這個概念包含在內。如果我們細加辨別,就可以發現,這還不只是一般地以詩的語言來寫詞的問題,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是以有別于唐詩語言的宋詩語言來寫詞的問題。宋代詩人如歐陽修、王安石等已有意識地從唐代大師杜甫、韓愈等的語言寶庫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營養,從而形成了宋詩語言的特色。蘇軾也正是積極參與了這一藝術活動的人。這樣,在他從事詞的革新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或者說很自然地將詩的語言,特別是宋詩的語言帶進了詞里,從而形成了炫爛多彩的風格。例如,雄壯超脫的則有 〔念奴嬌〕(“大江東去”)、〔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清新明快的則有〔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洞仙歌〕(“冰肌玉骨”)等,奔放流轉的則有〔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水調歌頭〕(“落日繡簾卷”)等,沉摯深永的則有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永遇樂〕(“明月如霜”)等。此外,如〔哨遍〕(“為米折腰”)、〔滿庭芳〕(“歸去來今”)等,則已經高度散文化;〔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無愁可解〕(“光景百年”)等,更出之以議論;〔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自凈方能凈彼”)、〔南歌子〕(“師唱誰家曲”)等,又加之以俗語、禪語。這一切,都是由于適應詞的內容的擴大而形成的語言特色,并從而直接構造了蘇詞的獨特風格。將這些作品和前人的詩和詞分別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它的語言和風格,是更其接近于前人的詩(和蘇軾自己的詩)而遠于前人的詞的。在《文說》中,蘇軾將自己的文章描寫為:“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這位藝術巨匠以水之能“隨物賦形”來比喻他運用語言的本領,是合適的。他創造性地使用詩的語言來寫詞,為他所擴大的詞的內容找到與之十分相適應的形式,也足以證明他自我評價的正確。
勇敢地將詞寫成如李清照所譏諷的 “不協音律”的“句讀不葺之詩”,乃是蘇軾以詩為詞的又一具體涵義。前人曾將這一點歸咎于蘇軾不通詞樂,不善唱曲。但根據有關這個問題的現存全部材料看來,陸游在其《老學庵筆記》卷五中所說的“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這個結論還是下得對的。由于蘇軾在其創作實踐中并不十分嚴格地拘守聲律成規,就使得詞從他開始,更其明確地不僅以音樂歌詞的身份存在于藝苑,而且以抒情詩的身份出現于詩壇。在其后詞樂逐漸消亡的過程中,詞終于脫離了音樂,成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樣式,而依然存在下去。從元、明以來,直到現在,還有人用這種樣式來進行創作。所以蘇詞不剪裁以就聲律,從音樂和歌唱的角度看來,在當時也許是不怎么妥當的;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說,則是一種當內容與形式發生矛盾的時候,寧肯使內容突破形式,而不肯使形式束縛內容的正確方法。這不僅對當時的創作風氣起了良好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于詞之成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樣式也起了不可抹殺的支持作用。我們在估計蘇詞的歷史功績時,似乎不應當把這一點除外。
綜上所說,蘇軾以詩為詞的積極意義就在于改變了詞的傳統,擴大了詞的內容,豐富了詞的語言和風格,并且為詞發展成為獨立的抒情詩樣式準備了條件。
蘇軾寫的詞為數不少,但是,關于詞的意見,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卻并不多。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來證明:蘇軾的以詩為詞,正是他自己的理論的實踐。他在《祭張子野文》中云:
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婉轉,蓋詩之裔。
《與蔡景繁簡》云: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答陳季常簡》云: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這些極其簡略的意見,至少告訴了我們兩點:首先,蘇軾認為詞是詩的后裔;其次,因此好詞就是好詩,或者說,詞應當向詩看齊。這正是他的詞體革新的理論綱領,也就是以詩為詞的出發點。這種新的意見和新的實踐,在最初是不容易被人認識到它們的意義和價值的。所以即使是和他私交極篤、關系很深的人如陳師道,具有高度文學修養而又對他很尊敬的后輩如李清照,都曾經對他的詞加以非笑。直到南宋以來,才逐漸有人從理論上肯定了它,在創作中繼承和發揚了它。這正證明了,新事物總是在和舊事物的斗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以上我們探索了蘇軾以詩為詞這一創作特色的積極意義。但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它和估價它,同時指出以下各點也是必要的。
第一,以詩為詞雖然是蘇詞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創作特色,但這一特色卻不能夠反映其全部面貌。我們都知道,蘇軾是祖國文學史上為人們公認的大家,而大家的創作,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總是豐富復雜、兼容并包的。因而蘇軾雖然以詩為詞,并以此比其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但決不掩蓋他在以詩為詞那一方面所達到的造詣。在《東坡樂府》中,婉約綺麗、細膩溫柔,近于晏、歐、秦、柳的作品,仍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如〔浣溪沙〕(“道字嬌訛語未成”)、〔點絳唇〕(“月轉烏啼”),完全是秦觀的風致;〔蝶戀花〕(“蝶懶鶯慵春過半”)、〔木蘭花令〕(“經旬未識東君信”),則神似大晏、歐陽;〔定風波〕(“莫怪鴛鴦繡帶長”)、〔減字木蘭花〕(“曉來風細”),則逼真小晏;至如〔雨中花慢〕(“邃院重簾何處”、“嫩臉羞蛾因甚”),則簡直近于他所鄙薄的柳詞的情調了。不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無從全面地認識蘇詞,也難于體會蘇軾在詞史上作為一個大家的意義。
第二,我們推重蘇軾以詩為詞,但決不可以導致蘇詞可以勝過、代表或包括蘇詩那種概念。從詞的發展史上看,蘇軾的成就顯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輩詞人,但就他本人的創作而言,則很難說他在詞一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他在詩一方面的成就。根據不很完全因而不很精確的統計,這位作家的編年詩起于1059年,訖于1101年,一共有 2454首詩 (據王文誥 《蘇文忠詩編注集成》);編年詞起于 1072年,訖于 1100年,一共有344首詞(據朱孝臧《彊村叢書》本《東坡樂府》)。這就是說,他詞的創作時期只有詩的創作時期的三分之二,而詞的數量只有詩的數量的七分之一。由于蘇軾寫詞的年限較短,詞的數量較少,也就不能不對表現他內心世界的全貌有所影響。他的政治社會觀點在詞中反映得固然很少,就是在詩中占有大量篇幅的其他方面,在詞中寫得也不太多。這也就說明了蘇軾以詩為詞,雖然較之以前的詞人,已經大大地擴張了這一新的抒情詩樣式的內容,可是,在非常廣闊的生活里,仍然有某些極其重要的領域是他所沒有想到要用,或者不準備用詞去反映的。這,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由于詞這種樣式本身的局限性所導致的,并非完全由于蘇軾的“以詩為詞”還不夠徹底。
第三,蘇軾的以詩為詞雖然兼賅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并沒有超出下列范圍,即由比較狹窄地反映士大夫的有關男女關系方面的生活,擴大到比較廣泛地反映士大夫的其他許多方面的生活;或者說,由專門反映比較放浪的生活,擴大到也同時反映比較高雅的生活而已。和這種內在要求相適應,其藝術語言和風格就不能不依舊處于士大夫的美學觀點支配之下。這樣,才可以在除了綺羅香澤、綢繆婉轉之外,還“寓以詩人句法”,而不至于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蘇軾以詩為詞,作為一種重大的革新手段,本來是可以,而且應當繼承《詩經》、《楚辭》以及漢、唐詩歌的優良傳統,而使詞的成就更高一些的,但由于他受到自己世界觀中保守落后部分的制約,卻沒有能做到這一點。這是蘇軾全部創作中帶有的根本性弱點,在詞中也顯得很突出。這,也同樣有待于他的繼承者來加以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