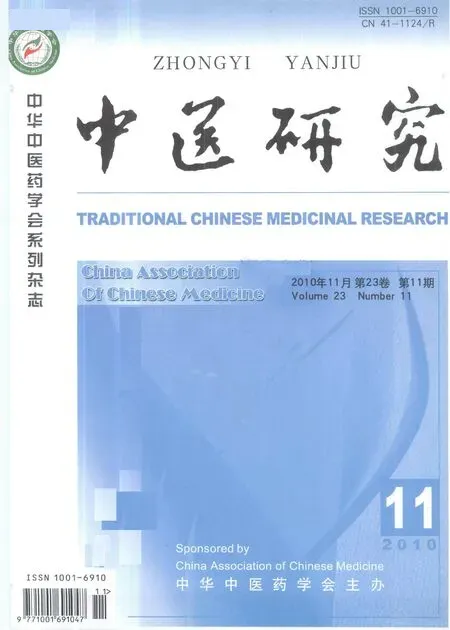方證相關的用方原則探析
張均克
(江漢大學醫學院,湖北 武漢430056)
從辨證論治的角度來看,“方雖來自古人,藥必出于己手”。無論多么優秀的方劑,要實現對具體患者的卓著療效,都有賴于用方者的匠心獨運。蓋因如此,歷代醫家都十分注重用方的變化。
1 方之既成,全在乎用
《醫學源流論》曰:“用方之妙,莫如加減,用方之難,亦莫如加減。”所謂加減,就是變化用方,對成方運用的知常達變。可見用方的實質就是方劑的變化。制方有定規,用方有法度。《傷寒雜病論》對用方之通變早有記載。《湯液本草》曰:“或以傷寒之劑改治雜病,或以權宜之料更療常疾,以湯為散,以散為丸,變宜百端。”此實乃用方變通之濫觴。清代醫家雷豐著有《時病論》,記載“成方須益損”專論,主張“醫者必須臨證權衡,當損則損,當益則益,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得能隨機應變,則沉疴未有不起也”。清代醫家吳儀洛強調,用方一要切于時,二要切于病,他認為“方有宜古不宜今者,設起仲景于今日,將必有審機察變損益無已者”,并告誡“醫貴通變,藥在合宜,茍執一定之方,以應無窮之證,未免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余,反致殺人者多矣”。然而,用方之變化又要遵循一定規矩與法度,加減化裁絕非隨意取舍,湊合處方。清代醫家徐靈胎言:“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癥,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根據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損取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癥,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他在《醫學源流論》中總結到:“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癥,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癥皆合,更與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予所現之癥相合,然后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可以看出徐氏在此提出的用方之論有三個層次:一是用全方,不作任何加減,其條件是兩個相合,即方證相合和藥證相合;二是加減用方;三是另擇一方。從徐氏用方之論可略窺前人對用方變化所持的基本準則。
2 方劑要素,方證相關
一首合格的方劑應具備6 大要素:組方藥物的味數、劑量、配伍關系(君臣佐使的結構關系和體現治法的功能關系)、劑型、用法以及它所要主治的病證。亦即[1]:成方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疾病制訂的。從方劑學的發展歷史看,方劑諸要素的出現是有先后的,早期的方劑要素很不完整,但是縱覽歷代方書,所載方劑有兩項內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藥物組成和主治病證,反映了有方以來人們的一個共識:方乃治病之方,方證不可分離。方劑所主治的疾病是方劑創制的目的和運用的目標,沒有適應癥的藥物組成算不上方劑,任何改變方劑要素的因素也必然會改變方劑的功效。從方劑內涵要素看,在用方過程中進行加減化裁時必須做到方證相關。
唐代學驗具豐的大醫學家孫思邈是第一個提出“方證”名詞的人。他以方證同條對《傷寒論》進行編次,按方證比附歸類,各以類從。如桂枝湯法57證,方5 首;麻黃湯法16 證,方4 首;青龍湯法4 證,方2 首;柴胡湯法15 證,方7 首等。診病療疾,檢方證相符而用之,簡便易行,有利獲效[2]。徐靈胎經30 年臨床研究,“不類經而類方”,將仲景113 方進一步歸類于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等12 類,各類主證中,先出主方,隨以證論,以方類證,證從方治[3]。當代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方證相關、方證對應或方證相應等概念,進一步強調了方證不可分離的邏輯關系。所謂方證相關,是指一個方劑內的藥物及其配伍關系與其所針對的病證之間,具有高度的針對性和關聯性[4]。這一概念不僅是對方劑學本質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制方用方應遵循的首要原則。臨床運用成方時,要充分考慮到目前病證與原方證之間的相關程度,方隨證變,隨癥加減。正如唐容川所云:“用藥之法,全憑乎證,添一證則添一藥,易一證則易一藥。”(《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仲景的不少方劑本身就制訂了明確的加減法,如本為發汗解肌、調和營衛主治太陽中風表虛證的桂枝湯,臨證應用時則根據病情的不同兼夾證而進行相應的加減變化:若見項背強痛者,加葛根(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加厚樸杏仁(桂枝加厚樸杏子湯);下后脈促胸滿者,去芍藥(桂枝去芍藥湯);微寒者,去芍藥加附子(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上述用方的變化都是在桂枝湯主證未變的情況下,隨兼癥不同而進行加減。后世正是從這些方劑的加減變化中認識到仲景遣方用藥的經驗和辨證論治規律的。遵循方證相關的用方原則,就要求做到方劑與證型諸要素之間的絲絲入扣。辨證一經明確,確定了證型的病機和相應治法并選擇合適的主方之后,就必須依據病勢之緩急、病情之輕重、病程之久暫、病位之高低內外以及病性之寒熱虛實等因素來進一步加減變化,或因勢利導,或引經直達,或丸者緩圖,或改丸為湯。如九味羌活湯之服用方法就是依據病勢緩急和治療目的而定的,若急汗則熱服并以羹粥投之,若緩汗則溫服而不用湯投之;又如理中丸治脾胃虛寒證,也有丸法和湯法兩種劑型用法,此類一方之二用,都是為了更加切合病情、更好地做到方證相關。
明代張景岳在《景岳全書·新方八略引》中提出的“因方”概念,是對方證相關理論的發展,他指出:“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證而用之,是謂因方。如癰毒之起,腫可敷也;蛇蟲之患,毒可解也;湯火傷其肌膚,熱可散也;跌打傷其筋骨,斷可續也,凡此之類,皆因證而可藥者也。然因中有不可因者,又在乎證同而因不同耳。蓋人之虛實寒熱,各有不齊,表里陰陽,治當分類。”可見景岳的“因方”概念有兩個層次,一是病同而證不同,即同病異證者,要因證用方;二是證同而因不同,即同證異因者,當按因用方。異病同治和異證同治的內在依據就是證的相同,而景岳的因方屬于證同因不同,則用方必須體現“同證異治”,這才是方證相關,表明同只是相對的,異才是絕對的。方證相關的用方原則要求醫者在“同治”用方時,要根據病因、證因之異而進行加減變化。如當歸四逆湯原系仲景為厥陰病(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而設,若用于治療血虛寒凝之月經不調而痛經者,常需加川芎、烏藥、香附;用于治療凍瘡之已潰者,則應酌減桂枝、細辛。方證相關的用方原則是動態的。由于很多疾病如內癰、時役溫病、皮疹等在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其臨床癥候及病機有明顯不同,即便是無明顯傳變特點的疾病,也存在正邪消長的不同,因而不可執滯一方于全程,必須根據不同階段的病機特點分期用方、次第而進,方顯出用方法度。機體狀態是用方必須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根據“從化”學說原理,患者的體質稟賦往往決定疾病發展的方向及癥候類型,正邪相搏表現出不同的病理生理狀態,而不同的病理生理狀態往往對方藥的反應有所不同,所呈現的功效也不同。因此,方藥的功效并非只是方劑內藥物的整合,而是方藥、病邪與機體三者之間相互作用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效應。前人觀察到桂枝湯有汗可止、無汗可發的雙向功效,也是視機體當時的病理生理狀態而定。五苓散對正常機體的水液代謝無明顯影響,而對水腫患者有利尿作用,且在一定范圍內隨病勢的加重而增強藥效。
3 同方異證,異同求之
歷代方書中都有一方主多病或多證的方劑,比如腎氣丸,仲景云:“婦人病……轉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又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轉胞和消渴主癥截然相反,病因和病機也頗多不同,如何分析和運用這些方劑也是值得研究的。從制方要素來看,這類方劑在組成上往往存在多種功效;從機體因素來看,也往往是患者在體質、年齡、性別、人種、個體稟賦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或者病理狀態不同,對于此類情況,一方面注意異中求同,同中變異,把準病機;另一方面通過調整配伍方中藥物來控制方劑的功效方向。以炙甘草湯為例,仲景治心悸,外臺治肺痿,孫思邈治虛勞,一方可主3 病證。異病同治的基礎在于3 者有著氣血陰陽不足、津涸燥淫的共同病機,但是3 者的病位不同、病機側重點不同、病理狀態也不盡相同。因此,同為炙甘草湯用方,加減變化是不同的,心悸者乃心脈失養、心不藏神,需加棗仁、柏子仁,甚或龍齒、磁石以助養心安神定悸,此時該方功效為通陽復脈;肺痿者陰傷肺燥為甚,又當酌減桂枝、生姜、清酒,以防溫藥耗陰劫液,此時該方的功效為滋陰補肺。吳鞠通對溫病后期熱灼陰傷之身熱面紅、口干舌燥、脈虛大證,采用炙甘草湯去參桂姜棗加白芍,有滋陰養血、生津潤燥之功,名為加減復脈湯,與炙甘草湯(又名復脈湯)雖同名“復脈”,但在功效特點上有溫涼通斂之不同。對于出現陰虛動風者,則又相繼加入牡蠣、鱉甲、龜板以及五味子、雞內金等,從而分別形成了一甲、二甲、三甲復脈湯及大定風珠等滋陰熄風的系列方劑。
4 小 結
以上分析至少給筆者兩點啟示:一是用方必須基于制方諸要素,尤其是方劑的內涵要素,遵循方證相關原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既充分尊重原方主旨而不失用方的原則性和科學性,又能做到正確的加減變化而實現靈活用方。二是基于方劑內涵要素的用方原則不僅是臨床辨證論治的需要,也有助于發掘方劑的新功效及新方劑的創制。
[1]謝鳴.方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
[2]辛智科.《傷寒論》方證治法的源流及發展[J].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7,19(3):13-15.
[3]王階. 方證對應與方證標準規范探討[J]. 中醫雜志,2002,43(7):489.
[4]謝鳴.“方證相關”邏輯命題及其意義[J]. 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26(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