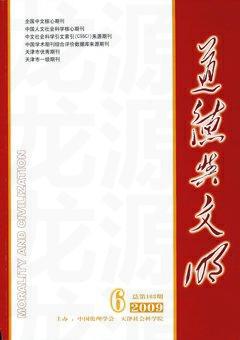論“義·利·禮·法”關系的歷史建構及其當代意義
〔摘要〕 中國傳統諸子的義利觀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它們在本質上具有“義利合一”的社會價值取向。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傳統社會的“義利之辨”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義”的確立來設定個體利益獲得方式的評價標準。“義”是社會交往的抽象原則,而“禮”則是“義”的具體化。“禮”是通過“分”來實現的。將“禮”的規定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傳統社會中,“禮”相對于“法”來說具有指導性地位。“禮”與“法”實質上是對“利”的一種調整機制。“義?利?禮?法”關系的歷史建構與展開對于當代中國的道德與法律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義利合一 義 利 禮 法 歷史建構
〔中圖分類號〕 B8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1539(2009)06005405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儒、道、法、墨等主流學派的“義利觀”具有一定的差異性,但從其本質內涵來考察,各學派的義利觀都蘊含著“義利合一”的價值原則。“義”與“利”在“禮”與“法”中獲得其具體性和客觀性,“禮”與“法”則通過“分”的中介,分別以“德得相通”的道德文化設計原理來維護“義中之利”,以“罪罰相連”的法律文化設計原理來否棄“義外之利”。 在當代和諧社會語境下,“義?├?禮?法”關系的歷史建構對于當代道德與法律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義利之辨”與“義利合一”價值觀主導地位的確立
朱熹曾認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朱文公集》二十四卷)。事實上,義利之辨不僅是儒家的主要哲學命題,更是中國傳統諸子百家的根本出發點。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義利之辨為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倫理的生成提供了核心資源,以至于古代所有理論學派都要對這一問題予以關注,提出自己的主張。
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質”(《論┯?衛靈公》);“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被視為君子的內在價值與固有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義”的價值要優先于“利”的價值。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為儒家學派確立了“重義輕利”的價值基調。繼孔子之后,孟子進一步闡發了儒家的“重義輕利”觀。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如果后義而先利,勢必會引起人們之間的沖突和爭奪,乃至國滅君亡。所謂“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認為:“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荀┳?大略》)。這也充分體現了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總之,在儒家看來,義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質需求更為有益,提倡“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等道德┰則。
與儒家相反,法家在義利觀上的特點是“重利輕義”。管仲曾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明確指出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后來的法家更是表現出一種功利主義傾向。商鞅認為,為了達到功利目的,大可不必拘泥于道義,“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君┦?更法》)。韓非子則根據社會變遷的事實分析對“義”進行了完全的否定,所謂“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韓非子?五蠹》)。在法家看來,人們都“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子?解老》),“利者,所以得民也”(《韓非子?詭使》),“利之所在,民歸之”(《韓非子?外儲說在上》)。但仁義不僅不能禁止現實中惡的力量,而且也破壞了自食其力的原則,追隨仁義的結果會使賞罰不分,是非不定。因此法家攻擊儒家的“先義后利”、“以義制利”等思想。仁義道德不僅對治國無益,反而有害。行仁義的最終結果不僅不利于國富民強,反而使國家貧窮沒落。因此,為了國富民強的“利”就必須放棄和改變“義”,從而使“義”最終從屬于“利”。
道家崇尚“自然”、“無為”,認為“義”的出現是社會倒退的結果,因而表現出“絕仁棄義”(《老子》十九章) 的思想傾向。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莊子排斥仁義的觀點更為鮮明,甚至將其視為天下禍亂的根由。“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莊子?馬蹄》)。在道家看來,仁義使人們有了利益之心,進而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因此,要使社會安定,就必須通過“攘棄仁義”(《莊子?胠篋》),使人們達到“無欲”、“無情”的境界。因此,道家認為,不僅仁義必須摒棄,利益觀念同樣是要被消滅的,唯有如此,社會才會走向和諧。
墨家主張“兼愛”思想,其核心內容是“兼相愛,交相利”,它基本涵蓋了墨家的義利觀。“兼相愛”即墨子之“義”。《墨子?兼愛下》中說:“兼即仁矣,義矣。”兼愛就是仁,也就是義。在義利觀上,墨子主張“義利” 兼重,并把“利”視為“義”的根據與目的。《墨子?耕柱》篇說:“所為貴良寶者,必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壓,歿世而不倦”(《墨子?節用中》)。《墨子?兼愛下》中更明確指出:“今吾將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取之以兼為政。”以“兼”即以“義”來實現興利除害的目的。這樣,“義”便成了實現“利”的一種手段或途徑,“義”是一種工具,它有明確的功利性,而“利”則是“義”指向的最終目的。后期墨家基本上繼承了墨子的“義利”兼重的思想,甚至提出了“義,利也”(《墨子?經上》),更為明確地表達了墨家的義利觀。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諸子中義利觀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性。究其原因,則在于各家對“義”的概念本身有著不同的理解。儒家的“義”是一種具體性的社會關系之“義”,它是以傳統家族血緣為原則來安排人際交往關系、設定行為規范的。正由于此,儒家之“義”才成為法家、道家的批判對象。從這一視角來看,道家之“絕仁棄義”是為了重建其所主張的道德之“義”,即作為一種世界本源與本性的人類生活最終準則。因此,道家對其“道”、“德”之“義”的提供實質是主張回歸到歷史原初的社會秩序之中。相反,法家的“重利輕義”則是為了建構一種新的“義”,即“法”之義。相對于上述各家而言,墨家的“義”則具有更為廣泛的內涵,它不僅包含著儒家之“義”,而且具有超出儒家之“義”范圍的“兼愛”┲“義”。
如果進一步理解傳統諸子中“義利”關系的具體內涵,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的價值取向,即“義利合一”。 首先,傳統諸子都對“利”給予了一定的承認與肯定。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論語?里仁》)。 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 (《孟子?告子上》)。荀子說:“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荀子?非相》)。他們都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家韓非子認為:“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子?解老》); “利之所在,民歸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道家盡管否定儒家之“仁義”,但其所設想的理想社會中,人們也是“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老┳?八十章》),因而也從另一角度對“利”予以了肯定。墨家由于“義利”并重,其對“利”的承認則更為明確,所謂“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墨子?經上》)。“利”是與人的生存直接相關的。其次,傳統諸子都反對“義”外之“利”,肯定“義”中之“利”。儒家孔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墨子?大取》)。因此,在儒家看來,一方面,盡管“利”是人的本性要求,但“利”的獲得必須以“義”為前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告子上》)。另一方面,在“義”的前提下,必須努力促進“利”的實現。所謂“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勸之。民勸之,然后國豐富也”(《賈┮?新┦?大政下》)。法家盡管反對“私義”,但卻主張“法”之“公利”,即“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以使“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利”(《韓非子?八經》)。道家則以“自然”、“無為”來成就個體利益。老子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如果我們將道家所主張的“道”、“德”視為一種“義”的話,那么,道家所主張的實際上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義中之利”。墨子對“義”之于治理國家的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墨子?天志中》)。因此,墨家也不是一般地肯定“利”,而是要求以“義”制“利”。“利”同樣是從屬于“義”的。
傳統諸子中“義”的差異性及其對“利”的承認,使“義利之辨”成為一種制度設計的爭論,而不是對“利”本身的絕對否棄。相反,貫穿于傳統諸子中“義利”關系的根本精神則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義利合一”的價值取向。由于封建體制下“家國一體”的政治模式,儒家以家族血緣為指導的人際規范與法律制度成為一種主導性的設計方案,其他各家則因其與政治現實不相符合而被否定、選擇、融合。但是各家所共通的“義利合一”的價值內核和人文精神則被儒家及統治階層繼承下來,最終確立起其在中國價值文化中的主導地位。
二、“義?利?禮?法”關系的歷史建構過程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義利”關系不僅是物質利益與交往規范之關系,也是個體與社會之關系,其最終目的是通過“義”的確立來設定個體利益獲得方式的評價標準。因此,上述諸子“義利”之爭實質上也就成為評價標準之爭,由于歷代封建統治階層的強有力支持,儒家之“義”的評價標準獲得了最終的支配性地位。“義”并不是一種抽象的評價原則,而是一種客觀性的具體規范。在儒家看來,這種體現“義”之原則的客觀性具體規范就是“禮”,“國無禮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如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荀子?王霸》)。因此,在儒家看來,以“禮”制“利”也就是以“義”制“利”,以“義”制“利”要求以“禮”制“利”。“義”、“禮”相為表里,“義”是“禮”的普通原理,而“禮”則是“義”的客觀體現。
在儒家看來,“禮”是通過“分”來實現的。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春秋繁露?奉本》);“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禮記?輿禮》)。當然,正如前述,儒家之“禮”是以傳統血緣家族范型為基礎的社會交往規范,“禮之為用,時義大┮印…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禮”(《隋書?高祖紀》)。“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 。由此可見,“分”的具體化功能體現在主體與物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自然血緣為標準來區別家族成員的主體地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與朋友五倫關系;另一方面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對利益進行不同的分配。也正是由于這一點,儒家之“義”與道、墨家之“義”才得以相互區別開來,因為后者否定或者是超出了上述主體地位的區分。然而,從規范原理的角度來看,法家之“義”的基礎亦是上述家族血緣主體。法家之“公義”實質上就是“君義”或“君法”。因此,儒家與法家的區別不在于其血緣主體的定分,而在于其對君臣上下之分位的強調。從表面上看,法家之“法義”與儒家之“禮義”是有一定區別的。人在社會中各有所處的分位,各處其分位而不混亂就是理,其行為適合于所處的分位就是“義”,用禮節儀式將“理”或“義”文飾起來就是禮,而法則是將等級制度的規定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強制性地要求社會成員共同遵守,但是這種區分的意義卻極為有限。首先,君主之地位即是“禮”之基礎,也是“法”之根據,君臣上下之定位是儒家與法家之共同基礎。其次,“法”之刑罰是儒家“禮義”的內在要求。最后,“禮”與“法”相輔相成,共同確立起完整的規范設計。在儒法兩家看來,“禮”側重于預防犯罪,即導民向善;法側重于懲罰犯罪,即禁人為非。只不過“法”或“刑”的直接依據是“禮”,即所謂的“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后漢書?陳寵傳》)。因此,在傳統社會中,作為“法度之通名”的“禮”相對于“法”來說具有指導性地位。從這一意義上來看,中國傳統社會中“義”的客觀化不僅具體體現在“禮”的規范之中,也體現在“法”之律令之中。
既然“禮”與“法”都是“義”的具體體現,而“義”都是與“利”緊密相關的,因此,“禮”、“法”的實質也就是“利”的一種調整機制。但是“禮”與“法”對“利”的調整方式是不一樣的。首先,“禮”的調整遵循“德得相通”的邏輯。在每一種社會秩序之中,在相互聯系的社會關系中,每個人都被安排好了確定的位置,他必須具備相應的德性。“自我不得不在社會共同體中和通過它的成員資格發現它的道德身份,如家庭、鄰居、城邦、部族等共同體”[1],而“德性就是維持一個充當某種角色的自由人的那些品質,德性就表現在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行為中”[1](154)。德性就在于個人應該扮演社會安排的角色。黑格爾也認為:“一個人必須做些什么,應該盡些什么義務,才能成為有德的人,這在倫理性共同體中是容易談出的:他只需做在他的環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確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2]同時,“分”的權利指向特定主體的利益要求。“禮”通過“分”安排利益,從而實現“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荀子?禮論》)。由此可見,正是“禮”通過“分”中的權利與義務的安排或“德得”相通的邏輯,“義”與“利”的關系才得以具體化,以“義”制“利”以及“義以生利”才得以客觀化。其次,“法”對“利”的調整則是遵循“罪罰相連”的邏輯。與“禮”相同,“法”亦是通過確立社會交往主體的地位或“分”來實現其對“利”的調整,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但是由于“法”更多的是強調對行為的禁止,因而其“分位”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是責任與懲罰。所謂“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商君書?禁使》)。當然,這種禁止同樣是對利益的一種特殊安排,可見,如果說“德”是對“禮”之義務的遵循的話,那么“罪”則是對“法”的義務的違背,并進而使“禮”對“利”的調整失去了平衡與穩定,而“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貫性和恒長性的話,則任何人都不可能從事其事業,甚或不可能滿足其最為基本的需求”[3]。這樣,懲罰作為一種對利益平衡的補償就成為必要。“徜若是一個人打人,一個人被打,一個人殺人,一個人被殺,這樣承受與行為之間就形成了一種不均等,于是就以懲罰使其均等,或者剝奪其利得。”[3](96)“現實的法就是對那種侵害的揚棄,正是通過這一揚棄,法顯示出其有效性,并且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必然的被中介的定在。”[2](119)法的現實性也就是“法通過對侵犯自己的東西的揚棄而自己與自己和解的必然性”[2](118),其具體表現也就是“罪罰相連”的邏輯┦迪幀*
如上所述,傳統社會的主導價值是“義利合一”,它提倡“義中之利”而否定“義外之利”,進而通過“禮”、“法”中“分”的具體定位來實現利益調整中的道德關系。從這一意義來看,“禮”、“法”實現利益調整的具體機制就是其各自所遵循的邏輯:“禮”之“德得相通”邏輯所維護的是“義中之利”,而“法”之“罪罰相連”邏輯所否棄的則是“義外之利”。兩重邏輯相輔相成,共同促使利益調整的道德關系之實現,并最終達到社會生活的和諧。
三、“義?利?禮?法”關系的歷史建構的當代意義
從歷史經驗與社會發展的要求來說,“義利”關系總是辯證的:一方面,“義”的產生源于制“利”的需要,不具備調整利益關系功能的社會規范是不可能存在或是無意義的;但另一方面,“利”的實現又必須在“義”的指導下進行,那種不能實現物質利益功能的社會規范同樣是不可能存在或是不可接受的。“義利” 關系的合一必須是“義以制利”與“義以生利”兩個方面功能的統一,上述傳統諸子的爭論及其內涵即表明了這一點。然而,“義利合一” 的實現方式卻不是一成不變的,換言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以“義”為重或是以“利” 為主都可能具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一般來說,在社會規范、法律制度比較完備的社會發展階段,“義利合一” 的形態中主要是以“義” 為重,而在缺失“義”的社會發展階段,就只有“利”才是選擇“義”的標準,進而推動社會道德規范、法律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在這一點上,傳統諸子中法家之“義利”觀被優先獲得認同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傳統諸子關于“義利”的爭論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而其爭論的實質則是為新生社會形態確立一種有效的社會道德規范、法律制度。在這些爭論之中,道家表現出一種復古保守的傾向,試圖倒退到“小國寡民”的原始狀態;墨家則不顧家國一體的現實,企圖超越家族視野,建構一種適用于市場交往的社會狀態,兩者都因為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而被淘汰。相反,法家則正視“利”的合理性,從“利” 的有效實現的角度來建構新的“法義”,從而最終實現了“義利合一”的特殊形式。如果說,當代中國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所處階段與傳統諸子開展“義利”爭論的變革時期相類似的話,那么從道德建設和法制建構或創新的角度而言,“利” 同樣應該成為我們進行規范選擇、制度建構的評判標準。當代中國社會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所謂轉型實質上也就是人們交往實踐的耦合結構的整體位移,它以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革為起點,完成于交往規范中權益的定型化。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原有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交易失敗”[4]的結果,其原因就在于原有社會規范系統失去了“義以生利”的功能,因此,如何促進利益的實現應當成為當代中國進行規范選擇的評判標準和規范創新的指導性原則,用中國傳統話語來說,即“重利輕義”。當然,這里的“重利輕義”并不是完全否定作為“義”的道德或法律規范,而是說,要從利益實現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原有計劃經濟時期的道德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批判的基礎上實現市場經濟時期的道德規范的更新與法制創新。利益是規范能否得到認同的物質基礎,因此,在社會變革時期,以“利”為標準來選擇、建構道德與法律規范是實現道德與法律中“普遍遵從”這一要求的前提之一。
儒家與法家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使其“禮”、“法”獲得普遍的認同,其原因還在于其是以當時社會實踐中的主導性交往范型(即家族血緣范型)為基礎的。所謂主導性交往范型,即社會實踐中普通民眾所傾向的并一直在運作的交往行為模式,也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模式。“禮”、“法”的創制以主導性范型為基礎,實際上也就是將其上升為國家規范,同時也是對該主導性范型及其所蘊含的利益予以強制力的保護,因此,人們對“禮”、“法”的服從事實上也只不過是對自身所“自然”擁有的行為模式與利益實現方式的服從。這一點對于當代中國道德與法律建設同樣至關重要。具體而言,即將道德更新與法制創新建立在當代中國的市場契約型的人際交往模式基礎之上,進而根據市場契約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平等與公平互惠的“分位”來完善道德與法律規范。可以說,將道德與法律規范建立在人們已有的實踐范型及其規范原理基礎之上,是使法律規范獲得人們的普遍服從的最為有效的方式[5]。事實上,以“利”為標準與以主導性交往范型為基礎是同一事情的兩個方面:主導性交往范型蘊含著其“自然權利”,“利”體現在主導性交往范型之中。換言之,任何現實的交往范型都具有“義利合一”的必要品格。因此,以“利”為標準來建構中國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必然要求其建立在中國人民自身的市場交往實踐模式基礎之上,因為這里的“利”顯然只能是人民的利益。事實上,在西方道德與法律發展的過程中,實踐理性、自然法、社會契約論也是通過其所確立的主導性交往范型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利”來實現其對道德與法律規范的批判功能的。當然,中國儒家的成功具有頗多的曲折性,并且由于其滿足于“義利合一”的現成模式,從而走向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道德、法律保守主義。而這一點,不僅說明“利”在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應當作為一種道德更新與法制創新的指導性原則,而且也意味著在社會發展的穩定時期,“利”的標準也是不能被完全放棄的。總之,要使當代中國道德和法律獲得普遍的遵從,社會實踐的主導性交往范型與“利”的原則是其重要的基礎。
(作者:黃國偉 南京審計學院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碩士,江蘇南京 210029)
參考文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