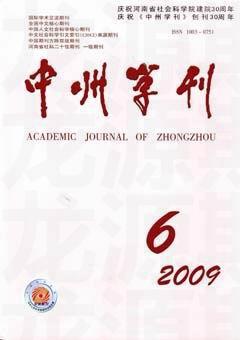郁達夫新論
許鳳才
摘 要:自身復雜的性格、放蕩不羈的私生活、悲歡交織的愛情行旅和良莠相間的交游活動是構成詩人郁達夫生前和死后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要因素。我們可以從他的婚姻愛情觀、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文壇上的“和事佬”等方面來解讀他那“光輝的特異的人格”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跡,還原出一個真實的郁達夫。
關鍵詞:郁達夫;愛情;性格;哲學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6—0210—05
郁達夫是我國“五四”新文學發展史上最負盛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無論是小說,抑或是詩歌、散文,都達到了同時代其他作家所難以攀登和逾越的高峰,有許多名篇佳章至今還仍閃爍著燦爛的光輝,尤其是他那坦蕩的胸襟,高尚的人格及瑰麗多姿、帶有浪漫和傳奇色彩的生活世界,則更是每每為人們所稱道。郭沫若就曾著文贊揚他的“卑己自牧”是和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一樣為文壇之絕。但遺憾的是,由于諸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像郁達夫這樣的有著“光輝的特異的人格”的著名作家、愛國主義戰士,幾十年來卻沒有得到公允評價,更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歷史地位,甚至還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
造成人們對郁達夫誤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卻眾所周知的歷史因素之外,恐怕其自身復雜的性格、放蕩不羈的私生活、悲歡交織的愛情行旅和良莠相間的交游活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赤者嫌其白,白者嫌其赤。
婚姻愛情觀
以熾熱的情感,虔誠的心靈,博大的胸懷,努力不懈地去追求新時代具有科學文化知識和青春氣息的浪漫女性,并希望從她們那里得到純潔的擁抱,溫柔的慰貼,來彌補精神上的創傷和空虛寂寞的心靈,是構成郁達夫絢麗多姿一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以此作為生命歷程的啟航點,便導演出了他一生中三次結婚兩次離異及多次婚前婚后戀的悲壯劇。
愛,就愛它個熱烈真誠,暢快淋漓;決裂,就來它個干凈利索,清澈見底。這就是郁達夫的婚姻愛情觀。他一生都遵循著這個原則行事,從沒有違背過。
郁達夫對女性的追逐和愛戀,在很大程度上是靈的需求,而非肉欲的滿足。從少年時代起,他就視女性為圣潔美和崇高美的象征,一直是在幻夢中生活,清醒之日,便是愛情進入墳墓之時。
綜觀郁達夫一生的婚姻愛情糾葛,始終都是受這種指導思想支配的,即從傾慕到熱戀再至失望到最終分手,冬去春來,夏過秋至,周而復始,從未超越過這個“愛情”的怪圈。
他和第二位夫人王映霞的“熱戀”及后來的“婚變”遵循的就是這個“原則”。
郁達夫與王映霞是一見鐘情,整個心都沉醉了。初出茅廬的王映霞在他的眼里,既像一株出水的芙蓉,是那樣的清純,那樣的蒼翠欲滴,給人以精神,給人以力量。而同時,她又像一朵春雨后盛開的牡丹,是那樣的美艷絕倫,國姿天香,令人陶醉,使人無限遐想。
為了這株芙蓉,為了這朵牡丹,郁達夫開始發“狂”了,什么家庭、地位、金錢、名譽、權利,一切的一切,他全可以拋棄。此時此刻,他對王映霞的愛,是發自心里深處的,是真摯、純潔、高尚的,上蒼的日月星辰,大地的山川海洋都可為其作證。他認為,只有像王映霞這樣有知識、有文化、有教養、有地位,既年輕美貌,又時尚新潮的女性,才能夠享受他那“猛如電光”似的愛,否則,那就是對愛的褻瀆和踐踏,而王映霞,只有接受他的愛,以后的人生道路才會越來越光明寬闊,精神世界才會更加豐富多彩。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郁達夫和王映霞終于幸福結合了,成了人人所羨慕的“富春江上神仙侶”。
然而,他們的婚姻一旦出現“裂痕”,彼此不再那么熱烈相愛時,郁達夫又回歸到了原來的“自我”,毫不痛惜費盡萬般辛苦所建立起來的“愛巢”,棄之如履。
無可諱言,在長達數十年的婚姻和愛情的糾葛中,既給郁達夫帶來了充滿甜蜜的歡樂,同時也給他留下了許多難以啟齒的苦痛和悲傷。但這二者的混合交織卻不期然地成就了他那光輝燦爛的文學大業。少年時代和趙蓮仙、倩兒等少女“初戀”時,感情激越奔騰,筆走龍蛇,寫下了數百篇天真爛漫、辭藻華美的詩詞歌賦,描摹出了那個時代少男少女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愛情的心靈軌跡。在東洋島國留學時有所愛,而始終得不到愛的痛苦磨難,成就了他那曾震撼過一代青年讀者心靈的光輝名篇《沉淪》。與第一任妻子孫荃的感情波折,生活煉獄,使他產生了《茫茫夜》、《蔦蘿行》等扛鼎之作,在“五四”新文壇上風靡一時。20世紀20年代中期與杭州四大美女之首王映霞的幸福結合,使他再度煥發青春,創作也達到了高峰。像風光旖旎、引人入勝的山水游記《屐痕處處》,清新美麗的小品文《閑書》,抒情詩般的《東梓關》、《遲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說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而與王映霞的婚變,則使他寫出了轟動海內外的千古絕唱《毀家詩紀》。
總之,無論是表現“五四”青年性苦悶的《沉淪》,還是抒發作者憤世嫉俗情感的《毀家詩紀》,或是贊美大革命時代追求進步女性的《她是一個弱女子》等,都是長期蘊藏在他心中的愛和恨相互撞擊時所迸射出的耀眼火花。
郁達夫一生中曾三次結婚,兩次離異,多次婚前婚后戀,而且每到一處都對那里的女性產生異樣的感覺,創作上也隨之會出現新的起色和亮點。之所以在他身上會出現這樣的奇跡,這除受他獨特的婚姻愛情觀支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他的泛愛女性心理有關。
在郁達夫的眼睛里,所有的女性都是可親可敬的,個個都值得男人們去追求,去憐憫,去愛戀。促使郁達夫產生泛愛女性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由他幼年及少年時代的生活環境所致。
由于父親的英年早逝,和兩位哥哥長期在外求學的原因,造成了郁達夫從三歲至十五歲這個黃金時代的生活環境,始終是以女性為核心的世界。祖母、母親、使婢翠花和鄰居家的少女趙蓮仙等,即是他這個核心世界里的主要精神支柱。她們的言論、行動、情感及生活方式都“潤物細無聲”地在潛移默化著年幼的郁達夫。從兩代寡婦——祖母和母親那里,他懂得了什么叫剛毅堅強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道理;從使婢翠花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善良、純樸、高尚和人間真情;從小學時代的女友蓮仙、倩兒等人那里,他品嘗了愛情的瓊漿玉液,并且還領悟了“愛”的真諦。這幾點交織融合在一起,便使郁達夫產生了一種對女性的泛愛心理。以后每當在人生的征途上遇到坎坷和曲折的時候,他都自覺不自覺地到女人那里去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
年輕時代的郁達夫,特別推崇英國19世紀初葉“交游最廣,和同時代的作家都處得很好”的浪漫主義詩人萊漢特,并且希望自己“將來在中國文壇上也能作個萊漢特那樣的人。”綜其一生,他也的確實踐了自己年輕時代立下的諾言,在紛繁復雜,氣象萬千的五四新文壇上他是朋友最多的一個,也是大家所公認的“穩健平和,不至于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在新文學團體內部,除十惡不赦的民族敗類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幫兇之外,他與其中任何一位都能友好相處,善始善終。革命陣營內,他的朋友有象魯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忠誠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在進步勢力和中間力量方面,他的朋友更是不計其數——像鄭振鐸、葉圣陶、蔣光慈、阿英、許欽文、沈從文等成績卓著的小資產階級左翼作家,都和他保持著親密的來往;即使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閑”文人,只要他們不投敵賣國,并能夠堅持用白話進行創作,反對文言復古這個大方向,郁達夫也仍以“朋友”待之,如他與胡適、徐志摩、林語堂、陳源等人的關系就是范例。
郁達夫在“五四”新文壇上之所以能夠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這是由他“外圓內方”的處世哲學所決定的。
“圓”——系指郁達夫的交游廣,朋友多,不管是什么風格,什么流派的作家,只要能夠堅持五四新文學的大方向,熱愛祖國,追求進步,人格光明磊落,他都能夠友好相處;而一旦失去這個前提,“方”的一面也就露崢嶸了,不管你是何人,彼此的關系多么密切,他都會毫不客氣地與之決裂,并以敵人視之。
周作人是郁達夫當時最敬重的朋友之一,倆人的關系一向很密切,周作人曾多次對人講,他不佩服魯迅的小說,而對郁達夫的小說卻情有獨鐘,并多次為其唱贊歌。是他的《自己的園地?沉淪》的出現,方使罵郁達夫“誨淫”和“造作的文壇壯士,才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
20世紀30年代前后,郁達夫因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等進步組織,反對封建軍閥專制,提倡革命文學,幾度上了執政當局的“黑名單”,屢遭迫害,險些遇難,身心都很疲憊。
遠在故都北平的周作人,得知郁達夫的真實處境后,不顧受牽連的危險,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多次邀請和敦促他北上任教,以解困厄。
對周作人的深情厚意和古道熱腸,郁達夫是很感激的,也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永志難忘。1931年7月6日,他寫給周作人的信就是其諸般感恩、欽佩心情的最好體現。
啟明先生:
來信早已接讀,終因雜事沉繁,迄未作覆。溯自兩三年來,因無業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幾多次。心里頭的感激,真沒有言語可以形容。這一回的北來,恐也終不能成為事實,所以幼漁先生處,并不發信去問,怕又要踏去年之跡,再失一次信,負一次約也。
自廣東回滬之后,迄今五年,因為一時的昏迷,就鑄下了大錯。遇人不淑,絕似法國Verlaine的晚年。(以此自比,原知僭越得很,然而事實卻很相像,并不說個人的天才相像也。)欲謀解脫,原非不可能,但是責任之感,又不能使我斷然下此決心,不得已只能歸之前定的運命而已。五年來的無心創作,無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婦人難養,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
近來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還以為我戀愛成功,不想做事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irony。
南方霉雨未晴,郁悶難堪,北國天氣,想較好一點,若有閑暇,請時時賜書,好使我在無可奈何之中略能得著一時半刻的解放,余事后敘,就此請你們全家的安。
達夫敬上七月六日
這封信表明,周作人和郁達夫確實是相濡以沫,肝膽相照的好朋友。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位“摯友”,一旦淪為漢奸,郁達夫也毫不客氣地撰文撻伐。在《“文人”》一文中,他怒斥周作人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文化界永遠洗不掉的恥辱。
……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終于到了現在,也被證實是事實了。文化界而出這一種人,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時窮節而見,古人所說的非至歲寒,不能見松柏之堅貞,自是確語。
大義凜然,怒斥為私欲而出賣“靈魂”的昔日好友——佐藤春夫,憤然與之割袍斷交,是郁達夫“外圓內方”處世哲學的又一具體體現。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私小說”的代表人物,作品素以表現現代人的孤獨、憂郁、厭世等苦悶情緒而著稱,這一點正吻合郁達夫的文藝思想,所以,倆人自1920年訂交后,十數年來關系一直很密切,來往也很頻繁。
殊不料,郁達夫的這位私交甚篤,十數年如一日的摯交,中日戰爭打響后,竟一反常態,肆意污蔑攻擊郭沫若等文藝界的抗日先鋒,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推波助瀾。《亞細亞之子》為其代表作。該文的大意是: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學家,北伐之后流亡日本十余年,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個姓鄭的朋友銜中國最高領袖的密諭,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訪問。煽動他回國去作抗日宣傳。蘆溝橋事件后,汪一個人悄然留下遺書逃回了中國。在各地作了許多熱烈的抗日的宣傳。最后他發現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時代的一位情人,卻被姓鄭的騙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于是他就幡然醒悟,重新投入日本人的懷抱。
凡有常識的人一看便知,“姓汪的革命文學家”影射的是郭沫若,“姓鄭的中國朋友”暗指的是郁達夫。整個故事梗概是以郁達夫秘密動員郭沫若回國作藍本的。在這篇惡劣之作中,佐藤“處處高夸著日本皇軍的勝利”和日本女人愛國愛家的高尚人格,而對中國人民則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進行攻擊和詆毀,在他的筆下,中國的男人都是些“出賣朋友的劣種”,女人則“比日本的娼婦還不如”。
《亞細亞之子》雖是文學作品,但影響極壞,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郁達夫看到后氣憤異常,除與作者割袍斷交外,還接二連三地撰文進行反駁,以正視聽。在《日本的娼婦與文士》中他怒斥佐藤春夫道:
佐藤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野人頭吃飯的。平常只在說中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國藝術是如何如何的進步等最大的頌詞,而對于我們私人的交誼哩,也總算是并不十分大壞。但是毛色一變,現在的這一種阿附軍閥的態度,和他平時所說所行,又是怎么樣的一種對比!
平時變化莫測的日本文人,如林房雄之類的行動,卻是大家都曉得的。在這一個時候,即便一變而做了軍閥的卵袋,原也應該,倒還可以原諒。至于佐藤呢,平時卻是假冒清高,以中國之友自命的。他的這一次的假面揭開,究竟能比得上娼婦的行為不能?我所說的,是最下流的娼婦,更不必說李香君、小鳳仙之流的俠妓了。
憤怒之情溢于言表,流于筆端,一針見血地戳穿了佐藤自命“清高”、“友善”的畫皮,沉重地打擊了其反華的囂張氣焰,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和威風。
北伐戰爭時期,郁達夫因誤解創造社同仁與蔣介石軍閥政府的合作,便毅然和他們斷絕往來,視同陌生人,而隨著歲月的流逝,彼此間的誤會消除后,政治觀點又趨同一致時,馬上又是兄弟,和好如初。
郁達夫和郭沫若既是留日同學,創造社的發起人,又是十幾年相濡以沫的摯交好友。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因對政治形勢和國共兩黨的認識方面發生了嚴重分歧,以至反目為仇。在《日記九種》中他不但給郭沫若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還罵他是新軍閥新官僚階級的代言人。
對郁達夫的嘲諷謾罵,郭沫若也因忍耐不住,遂在《英雄樹》、《桌子的跳舞》、《文學革命之回顧》等文章里進行反駁和批評,甚至還說出了許多超越理智和傷感情的話,以致彼此十年未再發生任何聯系。
對與郁達夫的“反目”,郭沫若在《再談郁達夫》一文里曾有過很深刻的檢討:
我們那時還年青,感情彼此都不容易控制,是值得遺憾的事,但我始終對達夫是懷著尊重和惋惜的意思的。我尊重他的天才,尊重他的學殖,尊重他的創作成績,更尊重他的坦白直率,富于情誼,為了朋友每每不顧一切,把自己置諸度外;但我可惋惜他有時候比我更加輕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過于沖動,而且他往往過分自賤自卑,這在我看來有點類似于自暴自棄或不自愛不自重的程度的。可是今天我得承認,這些都正是達夫的美德。他那樣容易忘我,實在是他的品格崇高的地方。我自己比起他來,實在是庸俗得非常。我雖然也是一位沖動性的人,但比起他來,我更要矜持得多,更有打算得多了。我做一件事情,每每有點過分的思前想后,而采取保守。在表面看來,我好像是位急進分子而達夫傾向于消極,而在我們的氣質上,認真說,達夫實在比我更要積極進取得多,但他的積極進取沒有得到充分的適當的展開,那是應該歸罪于時代和環境的。
這一段話既有對于郁達夫高貴品德的贊美,又有作者良心上的自我譴責,即譴責自己不應該輕信達夫的情感沖動之言,而與其“反目”。
經過十年的風雨滄桑,郁達夫和郭沫若彼此都認識到了當年“反目”時的輕率和魯莽。1936年郁達夫訪日,又重新溝通了他們的友誼。
1936年的11月底,郁達夫應日本友人的邀請,前往東京講了一個月的學,他到達東京的第二天,就驅車郊外的千葉縣看望郭沫若及其家人。
反目十年,初次相見,他們早已把過去的那些齬齟丟得一干二凈,仍同少年同學時代一樣,天真地談吐,愉快地歡笑。一天的時光不知不覺地流逝了,直到日本朋友再三催促他們赴宴時,方才結束了這不同尋常的談話。
在日本友人舉行的歡迎郁達夫的宴會上,郭沫若心潮激蕩,思緒萬千,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他們在上海一塊過“籠城生活”的時代,特別是四馬路醉酒時的情形又栩栩如生地浮現在眼前,他按捺不住奔涌的情思,揮筆寫道: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家又亡。
接到郭沫若的贈詩,郁達夫也同樣激情滿懷,潑墨如云:
卻望云山似蔣山,澄波如夢有明灣。
逢人怕問前程驛,一水東航是馬關。
新文壇上的“和事佬”
五四新文壇上不同的流派、不同風格的社團多、雜志多,人與人之間也因文學主張不同而分成一群群,一團團,這樣也就造成了社團與社團之間,雜志與雜志之間,作家與作家之間經常發生相互攻訐,摩擦不斷。這樣也就需要一個德高望重、學識淵博、通情達理,無論是哪一方哪一派都能夠接受的“和事佬”來調解彼此間的爭執。無疑,這個角色在當時非郁達夫莫屬。
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雙方激烈爭論正酣的時候,是郁達夫借郭沫若《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際,把雙方在上海的會員召集到一塊開了個紀念會,以求“把微細的感情問題,偏于一黨一派的私見,融合融合,立個將來的百年大計”①。
圍繞女師大風潮,以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為首的“語絲”派和以胡適、陳西瀅等人為主的“現代評論”派爭斗得如火如荼,郁達夫站在中間立場上,以客觀的態度,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指東道西,調解矛盾,緩和氣氛,以求雙方化干戈為玉帛,對郁達夫的調解,雙方都頗以為然。陳西瀅等人向魯迅“求和”休戰時,還是郁達夫從中傳的話。
魯迅性情剛烈,嫉惡如仇,新舊朋友都既敬之又懼之,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定居上海后,時常與朋友發生矛盾,而一旦矛盾出現,雙方都不能自行解決時,無一例外地都請郁達夫出面調解。如1927年,北新書局長期拖欠魯迅版稅,累積達一萬四千元之巨,多次索要不得時,魯迅只好請律師準備訴諸法律,以求公正解決。北新老板一看形勢對自己不利,一天就向暫居杭州的郁達夫發了兩封電報請他回上海調解,而魯迅也在同一天既去信又發電報,敦請郁達夫出面解決這件事。而這時的郁達夫正在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接到雙方的電報,只好犧牲計劃中的創作,不辭辛勞地奔波于滬杭之間。經郁達夫的調解,雙方重新握手言好。
雖然因奔波于滬杭耽擱了計劃中的長篇小說《蜃樓》的創作,但郁達夫并沒有感到遺憾,相反的他還常常引以為自豪。10年后,他在《回憶魯迅》中特重彩濃筆地描述了這件事的起因和經過: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后,和魯迅、啟明、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糊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楚。
后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處的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后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余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舊中國,從宏觀——整個社會的角度上來看,是矛盾重疊,關系錯綜;若從微觀——個人生活的角度上來看,那則是年年歲歲都可稱得上是多事之秋。表現在一代文豪巨匠魯迅和郁達夫的身上更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就在魯迅和北新書局的版稅糾紛得以和平解決的當天晚上,卻又發生了魯迅和林語堂因誤解而引起的矛盾沖突。
魯迅和林語堂,也與他和郁達夫、李小峰等人一樣,彼此間是早就有來往了,并存在著一定的友情。說起來此友情還可追溯到1923年他們一同在北京大學任教時。“那時北大的教授們分為兩派,帶甲備戰,旗鼓相當:一是《現代評論》所代表的,以胡適博士為領袖;一是《語絲》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樹人(魯迅)為首。”②當時的林語堂曾態度很鮮明地表示,他是屬于后一派的。據許廣平講,她在《兩地書》中稱魯迅為“小白象”就是從林語堂的一篇文章中借用過來的。“象”多是灰顏色的,偶爾遇到一只白顏色的,就為一些國家所寶貴珍視了。林語堂認為,魯迅在中國的難能可貴,就如同自然界的白象一樣應該為人們所稀罕所珍貴。由此也說明了林語堂對魯迅精神及其著作的認識和理解程度。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不顧個人受牽連的危險,接二連三地發函邀請身處逆境的魯迅到自己任職的廈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27年魯迅離開廈門輾轉來到上海時,他也接踵而至,其交往也比以前更加頻繁。1929年的8月28日,魯迅與北新書局的版稅糾紛得以和平解決的當天晚上,李小峰為答謝這次矛盾的調解人,緩和書局與魯迅之間的矛盾,特在南云樓舉行宴會。作為北新書局及魯迅和郁達夫的共同朋友林語堂,也應邀前往作陪。在酒酣耳熱之際,林語堂不知是有意地或是無意地竟突然對春野書店的創始人張友松大發了一通議論,而且言語中還多含批評和譴責的成分。
張友松原與李小峰一樣,系魯迅在北京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他在籌辦和經營春野書店的過程中曾得到魯迅不少幫助。魯迅這次為版稅問題計劃向北新書局提出法律訴訟,外間及北新書局方面的人多誤認為是由他從中挑唆作梗而引起的。在這樣的一種背景和場合下,林語堂突然對他進行評頭論足,很自然地要引起魯迅的反感。剎那間,魯迅的“臉色變青,從座位里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并非由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并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③
在魯迅與林語堂這場面對面的沖突中,郁達夫又一次起了和事佬的作用。他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就又“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這一按一拉,便平息了這場“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的沖突。
但據郁達夫的觀察,造成這次魯迅與林語堂發生沖突的主要原因,是由魯迅的疑心和誤解所致。他的論據是:依林語堂與魯迅多年的交情,及他對魯迅的崇拜程度進行推猜,他是不會在眾目睽睽的場合上譏諷魯迅,替北新書局鳴不平的,這是其一;其二,憨厚正直有余的林語堂在宴會上說出了一些令魯迅疑心和不快的話,那也只是偶爾的疏乎所致,根本不存在著什么對魯迅不敬和諷刺的意思。
由于郁達夫認為,林語堂對魯迅并沒有懷什么惡意,彼此間是因誤解而發生沖突的,所以在這之后,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來疏通他們之間因誤解而形成的隔閡,使他們重新言和語好。后來林語堂在《無所不談合集?林語堂自傳附記》中談起這件事時說到,當時魯迅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象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一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渡過了。”
經郁達夫的斡旋,魯迅與林語堂的關系很快又重新融洽起來。如1932年林語堂創刊《論語》,提倡“幽默”、“閑適”的小品文時,魯迅雖不太贊成他這種做法,但還是給予了有力支持。
1931年,《文學》雜志的主編傅東華在雜感《休士在中國》里發表了對魯迅不敬的言辭,魯迅看后非常反感,一方面寫文章聲明傅東華文中所言非事實真相,另一方面則寫信責怪《文學》雜志編委會,揚言要退出編委會。
傅東華原沒有想到問題這么嚴重,只是興致所至,隨手拈來而已,一看事情鬧大了,急忙請茅盾召集編委會商量解決辦法。編委會的意見,一方面委托茅盾出面代表編委會向魯迅道歉,請其原諒,另一方面則公開發表編委會向魯迅道歉的書面函。盡管如此,魯迅的怨氣仍未消除,決意要退出《文學》雜志編委會。茅盾等人無計可施,最后還是請郁達夫出面,才算把這事擺平。
注釋
①郁達夫:《〈女神〉之生日》,《郁達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②林語堂:《林語堂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
③郁達夫:《回憶魯迅》,《郁達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責任編輯: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