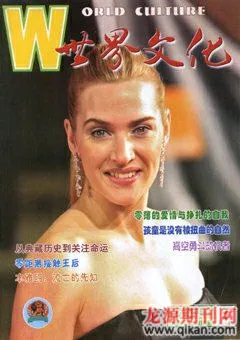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哲學王”和“友愛”
正義是社會倫理生活中的一個核心價值。正義的根據是什么?這是自政治哲學產生之日起就未曾停止過的追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政治哲學的奠基者,他們的“正義”概念深深地植根于雄渾的政治理想之中。解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我們理解其“正義”概念的一把“鑰匙”。
一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政治哲學的奠定者,他們研究政治哲學的出發點皆起自對社會的不公和無序的反思。柏拉圖認為“傷害任何人無論如何是不正義的”,而在當時的社會生活當中人傷害人的種種現象非但不為人們所反對,反而是非顛倒:傷害他人的不正義者被認為是強者,且富有智慧;堅持正義觀點的人卻被認為是迂腐的和沽名釣譽的。更為嚴重的是,是非顛倒的觀念和風氣一點點滲透著人們的性格和習慣,又逐漸滲入人際關系,再由人際關系滲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最終破壞了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的公正秩序。不公正的秩序和敗壞的道德互為表里地存在著,生活在這種狀態下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樂和幸福,向善之心被屈服、迷惑于不正義現象的錯誤觀念層層遮蔽著,人們喪失掉了追求正義的自覺精神。柏拉圖對正義的哲學思考,其間不僅包含著他為后人創立的正義觀,在其正義觀的深處,我們還能體會到他藉政治理想之力對人們的自覺的向善之心的啟蒙。自覺的向善之心是正義觀賴以確立的基礎,也是正義觀念轉變為現實意志力的源泉。亞里士多德秉承了乃師的深憂遠慮,以更為現實的態度反思政治中個人的有限性以及政治制度的蛻變。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我們閱讀到的是他對共和制度之合理性的論證,然而在他的論證中,我們仍然可以解讀出包含在合理性論證中的理想性預設。與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不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人與人之間不分貴賤的“友愛”。“哲學王”和“友愛”的政治理想深刻地蘊涵著古代正義概念的根據。
二
柏拉圖的正義概念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正義是心靈的德性;第二層涵義:個人心靈的正義與整個城邦的正義是相一致、相匹配的,二者的關系頗似“內圣外王”;第三層涵義:每個人如果在其自身之內使各種品質各就其職、秩序井然,那么國家之中每個人就能夠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兼做別人的事情,這樣國家就會變得和諧起來。總起來看,具有正義德性的公民在內心中使各種品質和諧發展,他在行動中就能與他人和諧相處,他知道自己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正義而和諧的城邦正是由這樣的良好公民組成的,它的特點就是公民各安其位,各盡其能。在公民中,堪稱榜樣的是那些內心最為和諧的有德之人,這些人可以擔當維護城邦的正義的責任,這樣的人就是“哲學王”。柏拉圖認為適合這種正義的制度應該是貴族制,因為貴族制度的國家既是“哲學王”產生的土壤也是他們得以成就的舞臺。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團結統一為榮,因而奉行“化多為一”,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最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這就是柏拉圖的政治理想。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概念也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正義是為政的準繩;第二層涵義:正義是一種中道;第三層涵義:正義是自由平等,是讓一切人以同等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共同參與某一政體。總起來看,亞里士多德將正義當作一種可望實現的政治準則,他認為中道是哲學的現實化道路,正義原則的現實化應當惠及每一位公民。亞里士多德認為共和政體,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決定力量的共和政體是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因為這一政體最符合“中道”——它既反對個人以權謀私,又反對多數人的暴政。亞里士多德質疑貴族的統治,他認為“由多數人執政勝過由少數最優秀的人執政”。
如果說柏拉圖的理想政治——“哲學王”的統治是一種人治,那么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治則是法治。柏拉圖反對繁瑣地去制訂法律,而主張人人皆有“心靈的憲法”,先立德而后生法。亞里士多德也并非認為法律能夠決定一切,他主張人人遵守法律,法律是為政的準繩,但前提在于法須是良法。
三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將政治理想上升到了哲學理念的高度,他們都提出了“至善”這個概念。柏拉圖認為“哲學王”所熱愛和學習的善乃是善的全部和整體,這就是至善。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著他們所認為的善”,城邦追求的是匯集諸善的至善。兩位哲學家對至善都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他們對至善內涵的理解卻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根源于他們對第一哲學的不同建構。“理念”二字是由柏拉圖最先確立起來的哲學范疇,柏拉圖認為善的理念給予知識的對象以真理,給予知識的主體以認識能力,它比真理和知識完善,是它們的原因,善的地位超過實在。善的理念在柏拉圖那里是純粹理想性的,它為實在所分有和摹仿。與柏拉圖不同,亞里士多德反對將理念超出實在,而主張理念和實在不可分離。他認為理念是實在的形式,形式與質料是不可分離的。因而他在質料與形式的關系中進一步抽象出潛在和現實這對范疇,他認為潛在轉變成現實就是理念的實現。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生活中的至善是一種自足,是事物完全由潛在轉變為生成的自足。這樣,亞里士多德的理念已經由純粹的理想性進步到向現實的轉變,他的理念更加富有辯證法的意義。因為柏拉圖主張至善是超實在的完滿實體,萬物不過是分有、摹仿至善,所以他認為接近至善的途徑是“化多為一”,這就是讓分有在眾多個人中的善復歸到整體意義上的善,柏拉圖堅信整體優于并且高于部分和個體。因為理念觀的不同,亞里士多德所認定的實現理念的途徑也大為不同,他承認個體的有限性,相信整體優于個體,但他主張整體并不高于個體,整體之中應包含個體的自由,整體不過是大眾合成的單一人格,是個體自由的完整的和現實的表達。因而在亞里士多德的理想政體中,不是追求個體如何提高、升華到全體的路徑,而是論證整體如何表達個體、成全個體。
柏拉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由“哲學王”實行統治的貴族政治,因為“哲學王”是最為接近“至善”理念的人。哲學家熱愛永恒的理念實體的全部,他的身心發展是全面的,他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是純粹的和道德高尚的人。哲學家熱愛智慧,勇敢地保持自己的信念,只做屬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兼做別人的事情,因此他自己能夠主宰自己。“哲學王”內心的秩序井然必然反映在他的行事之中,他富有智慧、生活節制、不畏懼死亡且處事公正、天性和諧,因此他可以成為人民的導師。柏拉圖認為這樣的哲學王在人民當中是少之又少的“極品”,但哲學王的誕生不是空中樓閣。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詳細地研究了培養和教育“哲學王”的方法,這種方法也是啟蒙全民向善之心的教化之法。柏拉圖要求全民生活在物欲極小的公有制條件下,自幼接受“思無邪”的愛美教育并強健體魄,終生為國奮斗,并始終接受信念忠誠與否的考驗。柏拉圖認為以“哲學王”為榜樣對全民實行向善的教育,是根本上轉變是非觀念,從而使公民人人具備從內心遵守法度的根本政治措施。可以這樣說,缺乏理想、不熱愛真理的人是不可能從根本上遵守法度并恪守職責的。
亞里士多德也堅信“善良之人的德性與最優良城邦的公民的德性必然是同一的” ,但他從自己的第一哲學出發,最為關心的是善如何由觀念轉變為實踐。他認為“在情感與實踐的事務上,只有在與對象有關時才具有確定性”,因而,他從行動和生成的角度出發,反對公有制,主張個人的多元化和自主發展。他不企求少之又少的哲學王的產生,而是奉行中庸,在個人私欲膨脹與集體暴政當中選取中間值,并鼓勵人們在行善過程中及時享受快樂,而無需要禁欲,因為快樂本身也是符合中道原則的。我們是否可以說與柏拉圖這位完美主義者相比,亞里士多德就是一位折中主義者呢?事實上,亞里士多德也有類似柏拉圖“哲學王”這樣的政治理想,這就是他對友愛的理解。亞里士多德認為友愛高于正義,他說“既然做了朋友就不必再談公正,但對公正的人卻須增加一些友愛” 。亞里士多德也同柏拉圖一樣信仰總體上的善,主張個人應喜愛總體上的善,但他更看重將善的觀念轉變為行動,這是生成中的善,這種善就是友誼。亞里士多德指出人不能離開共同生活而生,而共同生活中的快樂莫過于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一種強烈的友情就是如同對待自己一樣的關懷,”而“一切與友誼相關的事物,都是從自身推廣到他人” , “事實上善良的人,總是為了朋友,為了母邦而盡心盡力,必要時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 亞里士多德的共和政體,以輪流執政的方式保障公民具有既能統治,又能被統治的正義,但他認為這還是不夠的,這只是“報其所值”,而他認為友誼是超乎其上的“盡其所能”。“報其所值”的法終有其不甚完滿的地方,它很容易流于一種商品交易式的庸俗之中,那時法就不再是良法。亞里士多德以友愛彌補法律的不足,并把友愛看作具有比法律更高的境界。亞里士多德認為在友愛當中,即使“報其所值”的衡量者不是供給者,而是需求者,在友愛當中,人與人之間仍可以各盡所能。因此,凡是不違背和傷害友愛的法律就是良法,相反情況下的立法就會毀滅正義。
四
柏拉圖認為理念是實體,超出象外,如神存在。亞里士多德將理念貫諸實在,將之定義為駕馭質料的形式。前者關注至善的純粹性,后者關懷善的現實化,這種區別根源于二者所選擇的倫理學視角的不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探尋的是如何使公民中的優秀者“超凡入圣”,從根本上改變是非混淆的道德沉淪,而以“哲學王”的形象為公民樹立榜樣,并使其成為人民的導師,使公民具有守法的自覺性。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和《尼可馬科倫理學》中探索的是如何使至善在現有的條件下變為現實,使公民在共同生活中各司其有,得到與其利益相當的報酬。在這個基礎上,憑借友誼的作用達到“與人為善”,逐漸地接近于至善,而這就是良法的標準。
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為后世勾畫了一篇譜寫人類最高理想的典范,并第一次探索了道德教育的“化多為一”之法,我們從中體會了個人融入集體,集體共同向善的為政綱領。亞里士多德反思了其師的政治理想在現實化過程中的困難,注意了個體與集體矛盾的另一極——個體如何保持。他提出了集體是個體的單一人格的思想。但他并沒有把善的最高理想取消,他力圖借助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友誼,在“與人為善”的微觀建設中,逐步達到大同。亞里士多德將政治理想的現實化當作關鍵,他著力研究了政體的蛻變,從中總結經驗,尋找符合中道原則的合理政治,為大同思想的產生創造條件。
柏拉圖以嚴格的精神考察了人如何達到至善,他把道德教育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人的終生事業,他認為永不停止地接近“至善”才能保持人的純粹性,才不至于退步和沉淪。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和倫理學著作中也強調了教育,把教育當作國家的公共事業,他以中道為準繩約束人們的行為,但中道并不是折中,亞里士多德在人們的共同生活中尋找著最可行的盡善之道,他發現友愛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他和孟子一樣發現了“與人為善”的方法,“與人為善”是在復雜的道德行動中人與人互相鼓勵、互相協助遵循道德的可操作之法。
今天,當我們在追問正義之源泉的時候,仍然能從“哲學王”和“友愛”這兩個古老的政治理想中獲得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