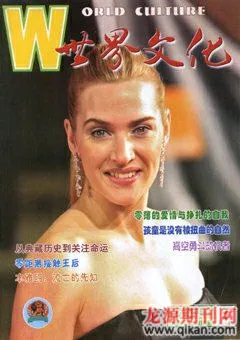零落的愛(ài)情與掙扎的自我
在俄羅斯文學(xué)史上,普希金被稱為“俄羅斯詩(shī)歌的太陽(yáng)”,而阿赫瑪托娃則被稱為“俄羅斯詩(shī)歌的月亮”。這位女詩(shī)人以纖細(xì)入微的筆觸,將女性在愛(ài)情中幽微曲折的心理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將一串串優(yōu)美動(dòng)人甚或凄婉的詩(shī)歌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更可貴的是,她的詩(shī)還包含了對(duì)愛(ài)情清醒冷靜的思考,承載了一種獨(dú)特的堅(jiān)強(qiáng)與鮮明的自我意識(shí),因此引得人們爭(zhēng)相傳頌。然而令人費(fèi)解的是,她曾與藝術(shù)理論家布寧及其妻室同居生活了長(zhǎng)達(dá)10年,這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否與她對(duì)精神獨(dú)立的自我追求相抵牾呢?這個(gè)問(wèn)題應(yīng)該怎樣理解才算恰當(dāng)呢?
在阿赫瑪托娃的詩(shī)中,抒情主人公多是因失去愛(ài)情而孤獨(dú)、冷落、絕望的女性,但詩(shī)人也塑造了一些更為可貴的形象,她們更多的是為保持自尊、自愛(ài)的女性人格而吟唱、呼喊。如“我被拋棄?簡(jiǎn)直是胡編亂造——/難道我是小花還是信箋?/……”(《我把朋友送到前廳》)詩(shī)中,堅(jiān)強(qiáng)的女主人公大膽地譴責(zé)了負(fù)心的情人對(duì)自己的遺棄,表明自己不是“小花”或“信箋”之類的物件,可以信手拈來(lái),把玩一番后便隨手棄之不顧,她并不乞求廉價(jià)的憐憫,她要的是將自己看作人的那種尊重。她的另一首詩(shī)《我生活得像掛鐘里的布谷鳥》是寫彼得堡的冬天詩(shī)人閉門索居,伴著孤燈讀書寫詩(shī)的情景,詩(shī)作將內(nèi)心的寂寞和惆悵和盤托出,然而詩(shī)人并不認(rèn)為這種機(jī)械、單調(diào)的生活是自己應(yīng)該默默承受的,她大聲呼喊“只有仇敵,我才愿他有”。詩(shī)人更不想過(guò)一種無(wú)聊放蕩、自暴自棄的生活,這從詩(shī)作《這兒我們都是醉鬼和蕩婦》可以看出這樣不體面的生活方式只會(huì)使她備感空虛和哀愁。
然而她卻從1927年起(此時(shí)她與第二個(gè)丈夫什列依科還未辦理正式的離婚手續(xù)),開始在噴泉樓的布寧家定居。她住在布寧的辦公室,隔壁就住著布寧的妻子阿蓮斯。阿蓮斯是一位善于主持家務(wù)的精明的女人,有不錯(cuò)的收入并為丈夫生有一女,她們與阿赫瑪托娃同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但這并不代表她們之間沒(méi)有出現(xiàn)緊張的局面)。這種生活竟持續(xù)了十多年。對(duì)此,甚至阿赫瑪托娃的摯友也都對(duì)她頗有微詞,認(rèn)為這是有損詩(shī)人尊嚴(yán)的錯(cuò)誤選擇。這樣的選擇確實(shí)難以為常人所接受,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俄羅斯的戀愛(ài)觀念和生活壓力,更重要的是當(dāng)時(shí)詩(shī)人坎坷的經(jīng)歷和絕望的心情。
首先,俄羅斯人推崇戀愛(ài)自由,對(duì)于兩性道德的觀念意識(shí)相對(duì)淡薄,在下層勞動(dòng)者中往往傾向于建立“某種溫厚、某種優(yōu)雅的無(wú)憂無(wú)慮的關(guān)系”,兩性關(guān)系依雙方自愿,自然地存在,并被賦予一種輕松的色彩。在上層社會(huì)中,對(duì)于諸如男人擁有情婦這類的事情更是感到平淡無(wú)奇,習(xí)以為常。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知識(shí)界對(duì)婚姻道德觀念有過(guò)激烈的爭(zhēng)論,許多作家都反對(duì)失去感情基礎(chǔ)的婚姻對(duì)追求幸福的束縛,而強(qiáng)調(diào)自由愛(ài)情的權(quán)利。同時(shí)在20世紀(jì)初的蘇聯(lián),同在一個(gè)屋檐下,一個(gè)丈夫同兩個(gè)妻子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格局是不足為怪的。1920年俄共中央婦女部長(zhǎng)柯倫泰就提出了“一杯水主義”,認(rèn)為在新政權(quán)下要滿足性欲和戀愛(ài)的需要,可以像喝一杯水那樣隨意。所以,當(dāng)時(shí)馬雅可夫斯基就和勃里克夫婦生活在一起,帕斯捷爾納克也同樣有兩位盡人皆知的妻子,更何況,對(duì)于阿赫瑪托娃來(lái)說(shuō)這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與她本人不幸的生活經(jīng)歷和生活壓力息息相關(guān)的。
美麗端莊的阿赫瑪托娃曾受到眾多男性的追求,她對(duì)愛(ài)情充滿了向往和追求,然而卻一生遭遇痛苦和厄運(yùn),先后與幾位戀人的愛(ài)情都以失敗告終:她首先嫁給了曾為她自殺過(guò)4次、詩(shī)才出眾卻其貌不揚(yáng)的詩(shī)人古米廖夫,但經(jīng)過(guò)苦苦追尋而得之不易的愛(ài)情并沒(méi)有使他從此以后就矢志不渝。格·伊凡諾夫在回憶他時(shí)說(shuō)道:“古米廖夫說(shuō)過(guò),‘戀愛(ài)對(duì)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是職業(yè)需要’,他時(shí)常涉足愛(ài)河,不加區(qū)別地墜入情網(wǎng)。古米廖夫的‘獵艷名單’開出來(lái)的話會(huì)有幾頁(yè)之多”。同時(shí)對(duì)于古米廖夫來(lái)說(shuō),生活永遠(yuǎn)在別處,他總是向往那遙遠(yuǎn)的非洲海岸,唯有漂泊和探險(xiǎn)才能安頓他那顆不安分的心靈。他常常一去就是半年,這使阿赫瑪托娃的生活更加寂寞,她也常常將內(nèi)心的惆悵抑郁訴諸筆端:“小窗前我把蠟燭點(diǎn)到黎明,/不管對(duì)誰(shuí)也不思念分心,/我就是不想,不想,絕不想/知道他們?nèi)绾稳ノ莿e的女人。”(《致繆斯》)最終他們因感情破裂而離婚。她曾愛(ài)過(guò)軍官安列坡,這位白軍軍官在二月革命時(shí),為躲避憤怒的群眾不得不逃到國(guó)外,而阿赫瑪托娃卻誓死不離開她摯愛(ài)的祖國(guó),兩人又不得不分手。第二任丈夫什列依科雖然愛(ài)她,卻蠻橫地不允許她寫詩(shī),她來(lái)到這個(gè)家“就好像進(jìn)了修道院,失去了自由、意志……”他甚至粗暴地將詩(shī)人的詩(shī)扔進(jìn)火里付之一炬,這讓阿赫瑪托娃不能忍受到了極點(diǎn),她寫道:“我既不想顫抖,也不愿痛苦,/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丈夫是劊子手,家是牢獄!”(《叫我服從你,……》)因此為了擺脫困難、屈辱甚至是鞭笞,也為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她與什列依科分手。然而愛(ài)情上的苦難只是她全部苦難的一部分,幼年時(shí)父母離異,兩位姐姐因肺結(jié)核而早逝,1918年—1922年,她的小弟、哥哥、小妹接連去世,接二連三的噩耗已使阿赫瑪托娃痛心不已,朋友們又紛紛因?yàn)閲?guó)內(nèi)形勢(shì)的變化流亡國(guó)外,1921年好友勃洛克去世,前夫古米廖夫被槍決并被認(rèn)定為反革命分子,生活中的不幸一個(gè)接著一個(gè),心情抑郁的女詩(shī)人簡(jiǎn)直想撕心裂肺地大聲呼喊,詩(shī)作《黑暗中到處充滿恐懼》、《你已不在人世》等都描寫了這些事件。
然而對(duì)她打擊最大的是“拉普”派對(duì)她的圍攻,她被誣蔑成“國(guó)內(nèi)的流亡分子”“不知是修女還是蕩婦”,詩(shī)歌也被認(rèn)為是“有罪的”“公開的資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被大加撻伐,正如詩(shī)人自己所說(shuō)“從上世紀(jì)20年代中葉起,我的新詩(shī)幾乎不再有人刊登,而舊作亦不再重版”。作為一個(gè)人,她失去了親情、友情和愛(ài)情,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身患重病的她常常是饑腸轆轆地寄居在別人家里;作為一個(gè)女人“她的情愛(ài)總是苦多甜少,由于遭到冷淡與背信,結(jié)果總是吃苦,她期望溫柔時(shí)所遇到的只是獸性的貪婪,經(jīng)過(guò)一番陶醉后她被遺棄,獨(dú)自受苦”;作為一個(gè)女詩(shī)人,她被誣蔑、查封,被扼住了喉嚨,試想,此時(shí)她承受著怎樣無(wú)可消解的疼痛,她又能拿什么來(lái)拯救自己呢?這時(shí)候,布寧出現(xiàn)了,他的出現(xiàn)大大緩解了阿赫瑪托娃的痛苦——既在某種程度上幫她解決了生活問(wèn)題,又用他的溫柔乃至溫順撫慰了她那顆創(chuàng)傷累累的心,因此她在給布寧的第一首詩(shī)中寫道,人們感到吃驚:“九月已到,/冰凍潮濕的日子消逝到了哪里?/ 溝渠混濁的水變得晶瑩碧綠,/蕁麻沁香,比玫瑰更加濃郁。/……/ 正在這時(shí),溫順的你來(lái)到我門前。”(《美妙的秋色建起了高高的屋頂》)
但是他們面臨一個(gè)嚴(yán)肅的問(wèn)題——布寧的家庭,兩人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時(shí)間的認(rèn)真交談仍然無(wú)法擺脫熾熱的戀情,布寧也沒(méi)有離婚的打算,此時(shí)的阿赫瑪托娃勢(shì)必也經(jīng)過(guò)了激烈的思想斗爭(zhēng),一方面,孤寂無(wú)助的她強(qiáng)烈渴望有一個(gè)溫暖的家讓她躲避風(fēng)雨,另一方面,原本高傲的她不愿與另一個(gè)女人的丈夫以及這個(gè)女人共處一室,因?yàn)榘徇M(jìn)布寧家實(shí)質(zhì)上她便成了別人的情婦,這似乎與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簡(jiǎn)·愛(ài)拒絕羅切斯特先生的做法形成了對(duì)比,這從阿赫瑪托娃自己對(duì)這段生活的態(tài)度也能夠看得出來(lái),后來(lái)她始終對(duì)這段生活難以啟齒,詩(shī)人的秘書阿納托利·奈曼談起她與三個(gè)丈夫的關(guān)系時(shí),有過(guò)生動(dòng)的對(duì)比:“她談起布寧時(shí),只是有限的幾次,談起什列依科也是輕而易舉,談起古米廖夫則津津有味,她極力回避去談布寧。”最終無(wú)望的阿赫瑪托娃在經(jīng)歷了種種不幸后,對(duì)生活保障尤其是人間溫情的渴望戰(zhàn)勝了對(duì)自我精神獨(dú)立的向往。女詩(shī)人對(duì)“家”這一概念的理解發(fā)生了改變,這從她為布寧寫下的以圣經(jīng)為題材的《羅德之妻》一詩(shī)中可見(jiàn)一斑:“她看了一眼——于是致命的痛苦把她凝固,/……身體變成了透亮的鹽柱,…/誰(shuí)會(huì)去悲哀這女人,/難道這損失還算小?/只有我的心永遠(yuǎn)不會(huì)忘記,/為了唯一的一瞥付出了生命。”羅德之妻明知逃亡時(shí)不可以回頭看,卻又在無(wú)意之中看了一眼自己的家,于是她立即變成了一根鹽柱,從最后兩句可以看出詩(shī)人對(duì)這位為了一瞥家園而獻(xiàn)身的女子的感情,表明詩(shī)人為了這份在受到重重重創(chuàng)之后不期而獲的愛(ài)情,甘愿委屈自己的自尊,執(zhí)著地去建立屬于自己的生活。最終熾熱的戀情讓她無(wú)法懸崖勒馬,反而成為她被陰郁淹沒(méi)前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
這樣的愛(ài)情在一定程度上給了阿赫瑪托娃些許的安慰,然而這種缺失了自我的愛(ài)情注定是畸形的,不會(huì)是完美的。當(dāng)她介入布寧的家庭后,內(nèi)心便陷入了深深的譴責(zé)和負(fù)罪感當(dāng)中,正如她詩(shī)中寫到的那樣: “我對(duì)你隱瞞了心靈的秘密,/同把它扔進(jìn)了涅瓦河底……/我像一只馴順的、無(wú)知的鳥兒,/生活在你的家里。/唯獨(dú)……夜里我聽到吱喳聲。……/‘你希望舒適,/你可知道,它——你的舒適,在哪里?’”(《我對(duì)你隱瞞了心靈的秘密》)她并沒(méi)得到自己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