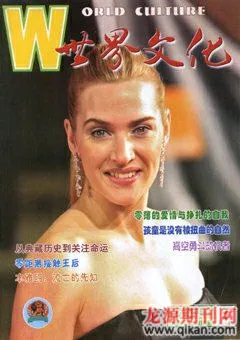揭開古埃及神秘面紗的商博良
古埃及文字很復雜,加之神廟僧侶又故意將其弄得十分晦澀,因此,隨著古代埃及的遠去,其文字也逐漸無人能解。15個世紀以來,世人都以驚奇的眼光觀察象形文字。歐洲學者一直誤認為它是宗教儀式上使用的神秘符號。直到19世紀,它才由法國學者商博良破譯成功,從而使光輝燦爛的古埃及文明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商博良也因此成為了埃及學的泰斗。
1790年,天賦異稟的商博良出生于一個書商家庭。他出生之時,父母和鄰人都驚訝不已,因為他的皮膚是黃色的,臉也酷似埃及人。幼年時期的商博良就酷愛讀書,渴求知識,尤其偏愛與埃及有關的知識。當他從朋友那里得到一包書籍時,商博良大聲說:“一切與未知領域有關的東西基本上都會吸引我……”。
哥哥讓·雅克在商博良成長的道路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一直為商博良的學習提供幫助。1799年,哥哥為商博良聘請了一位宗教老師Dom Clamels,教他古典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由此,商博良開始閱讀柏拉圖及其他古人的作品。1801年,商博良搬到格勒諾布爾,開始在哥哥指導下學習。1802年,他進入學校學習希伯來語。翌年,經老師批準,商博良開始學習阿拉伯語、古代敘利亞語、亞拉姆語和科普特語,其中他最鐘愛科普特語。
具備了語言基礎后,商博良開始研究古典學,研讀了希羅多德、斯特拉波、普盧塔克等人的著作。這些作品都涉及到與埃及有關的內容。1807年,商博良與哥哥遷至巴黎。此后,他進入法蘭西學院和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學習。在那里,他繼續研習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古代敘利亞語、亞拉姆語和科普特語。
商博良對埃及文化有著巨大熱情,一切與埃及有關的東西都深深地吸引著他。1809年,拿破侖遠征埃及的戰利品目錄出版,商博良開始投身于埃及文化的研究之中。同年,他還擔任了格勒諾布爾大學古代史的助理教授,隨后遷至格勒諾布爾。在巴黎和格勒諾布爾期間,商博良一直都在研究埃及語言,包括科普特語法和方言變化。
商博良破譯埃及象形文字所依靠的重要資料是羅塞塔石碑。1798年,拿破侖率軍遠征埃及。在這次遠征隊伍中還有一群科學家和工程師,其中包括考古學家、藝術家和動物學家等。這些科學家對所有的建筑、雕像、銘文以及其他文物、動植物、藝術品,進行了詳細記述、分類和研究。1799年夏天,一個叫做Boussard或Bouchard的人,在距離亞歷山大30英里的羅塞塔鎮工作時,偶然發現了一塊玄武巖厚石板。這塊石板有3.9英尺九長,24.5英尺寬,11英寸厚,上面刻有三種文字:圣書體文字(通譯埃及象形文字)、希臘文、民用體文字。
法國人將羅塞塔石碑轉移到了1798年在開羅建立的國家研究所。1802年,石碑銘文的副本被送至巴黎。然而,在對銘文的研究正式開始之前,這座寶貴的紀念碑被英國人占有了。英國人在1801年打敗了法國人,并從其手中搶得大量的古器物。其中,最令他們珍視的就是羅塞塔石碑。英國人將這塊石碑火速送往倫敦,并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大英博物館。時至今日,石碑仍存放在那里。
顯然,英國人認為,將石碑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掌控象形文字的研究狀況以及致力于解讀銘文的研究者。然而他們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最先解讀出象形文字的依然是法國人。在英國,解讀象形文字的重任落到了學者托馬斯·楊(1773-1829)的肩上。楊是一名物理學家和醫生。他于1802(也就是在發現石碑三年后)年加入皇家學會,1804年成為皇家學會的特別會員。他曾研究過一些東方語言,但并不是語言學家。楊的研究標本十分豐富,擁有很多其他的象形文字副本和紙草文本。而商博良卻不具備同樣的條件,就連他的同胞、導師Silvestre de Sacy,也致力于讓他在黑暗中繼續摸索。De Sacy在1815年7月20日寫信給楊,建議他就現在的工作對商博良保密。他寫道:“如果要我給你什么建議的話,我建議你不要同商博良交流你的研究成果”。商博良倒也收到過一篇菲萊的銘文,不過那已是在楊得到這篇銘文的4年之后。
楊的研究的確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始終沒能解讀羅塞塔石碑。而商博良卻在別人不斷失敗的時候,在此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績。他在使用羅塞塔石碑以前,研究了很多其他的資料,并且像兒時做游戲那樣,將不同的字母表放到一起進行比較。他將羅塞塔石碑上的民用體文字同其他紙草上的文字相比較,盡管無法準確理解它們的意義,卻可以試著從文本中辨別出最簡單的特點或標志。此外,商博良還將民用體、祭司體和圣書體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并且把同一文獻的幾個版本放在一起比較——例如,對比圣書體和祭司體版本的《埃及死亡之書》。此外,對于朋友和同事提供給他的其他一切文本,他都會仔細研究。每卷新的拿破侖遠征埃及的戰利品目錄都會為他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
商博良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終于探究出了這神秘文字的含義,找到了開啟古埃及文化大門的鑰匙。他欣喜若狂,丟下手頭的工作,沖出房間,穿過大街跑到哥哥工作的法蘭西學院,大喊:“我發現了!”
商博良多年的研究成果在《Lettre à M. Dacier》上首次公布,轟動了整個歐洲。他總結出象形文字包含864種符號,這些符號有的表示物體(天體、動物、植物等),有的表示幾何圖形,有的表示想象出來的動物(獸頭人身的動物)等等。他意識到,圖中畫的都是側面,這是為了標示出文字的書寫方向。如果它們面向左,就意味著人們要從左向右閱讀。當然,這些字也可以垂直書寫。
商博良還精心制作了一個表格來描述象形文字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一個物體的圖像可以作為符號來表示一個音,但此物體在口語中的名稱需以想要表達的那個音開頭:例如,古埃及語中的鷹叫做Akhom或Ahome,用來表示A;香水盤叫做Berbé,用來表示B;膝蓋叫做Ke’li,用來表示K;獅子叫做Laboi,用來表示L。就這樣一個語音要用幾個不同的圖像來表示。
此外,這類語言既表發音,也有象征性和符號性:例如Het意為“心”,由此延伸出精神和智慧。要表達“憂慮的”,就可以寫作“小的心”;“耐心”就是“沉重或緩慢的心”;“驕傲”就是“高高在上的心”;“膽小”就是“脆弱的心;“猶豫不決的”就是“有兩顆心”;“頑固的”就是“堅硬的心”;“懊悔”就是“吃掉某人的心”等等。
商博良的另一偉大成就是揭示了古代埃及文字三種文字——圣書體文字、祭司體和民用字之間的關系。商博良指出,三者中最古老的就是圣書體文字,基本上用于雕刻公共紀念碑。隨著對更簡便寫法的需求,出現了祭司體,這是圣書體的速寫法。這種字體由祭司使用,書寫在紙草上。祭司體具有象征性、符號性和表語音的作用。
最后出現的文字是民用體。它幾乎完全表語音。有象征意義的字符只用來表示神靈和神圣的東西。商博良宣布“在整個埃及地區,這三種文字一直都在同時使用。”他還補充道:“全國各個等級的人都使用民用體來進行通信,記錄涉及到家庭利益的公共和私人事件。”
然而,商博良的成果并沒有立刻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不列顛的學校聯合起來抵制他,并對他進行誹謗,否認法國人的成果。楊也站出來貶低他的成就。但在德國,洪堡兄弟、威廉聯合達西埃、傅立葉等眾多知名人士,團結起來捍衛商博良的理論。直至1866年,另外一篇著名的象形文字文本《坎諾普斯法令》出現,并根據商博良的理論成功解讀,才令那些質疑者緘口。事實證明商博良是正確的。
1826年,商博良回到巴黎,擔任埃及博物館保管人。1828年,在法國和托斯卡納政府支持下,商博良和洛塞利尼同到埃及游覽。不幸的是,天妒英才,商博良此行身染重疾,于1829年返回巴黎。1931年,年僅41歲的商博良去世。
商博良于人世匆匆四十載,猶如美麗的流星一閃而過,卻用短暫的生命再現了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完成了幾代人的夢想。他仿佛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只為破解象形文字而生。
商博良取得重大發現的決定性因素是熱情和專注——15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他學習語言輕松而迅速,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從中獲得樂趣。對他而言,研究語言就是最大的娛樂。例如,在他學習阿拉伯語的時候,就穿著阿拉伯風格的服裝,稱自己為“al Seghir”(阿拉伯語意為“年輕人”)。另一種“玩語言”的形式就是比較字母表:商博良將古代敘利亞語同亞拉姆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字母表放到一起進行比較,然后再將它們同科普特語、希臘語等語言的字母表進行比較。這是一種他用來消遣的方式。正是這種在孩童時期的游戲,后來幫助商博良破譯了神秘的象形文字。雖然所獲評價褒貶不一,但商博良并不在意。因為他專注于追求的是真理,而非他人的認可。
天才語言學家商博良,用自己超凡的熱情和毅力為世人揭開了古埃及神秘的面紗,但卻在鑄就輝煌之后悄然逝去,不禁令人扼腕嘆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古埃及文明這顆璀璨的明珠不斷地為我們帶來驚喜。但驚喜之余,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為象形文字而生的商博良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