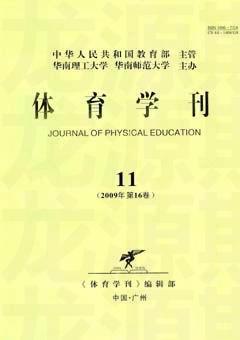論“體育”的名與實
謝松林
摘要:從語言學入手,以名實論為理論基礎,對“體育”這個實詞的“名”與“實”(概念)進行了分析,指出了“體育”的名與實不符的邏輯錯誤,提出了“應該把與‘體育一詞對應的‘實歸為‘教育這一臨近的屬”的意見。
關鍵詞:體育概念;名實論;語詞邏輯;教育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09)11-0005-05
The designation and mea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E Song-lin
(Department of Military-based Education,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by basing 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n the designation and meaning theor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designation” and “meaning” the notional word “physical education”, pointed out such a logical error as that the design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its meaning, and put forward such an opinion as that the “mean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word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long to such a proximity attribute as “education”.
Key wor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designation and meaning theory;wording logic;education
“體育”這個詞耳熟能詳,但它的內涵卻自其出現在本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統一的界定。在1982年,這一問題還引起了國家體委(現在的國家體育總局)的重視,體委特意在煙臺組織召開了一次專門探討體育本質與概念問題的討論會,并最終把體育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或稱“大體育”和“小體育”,分別冠以“體育運動”和“體育教育”的名稱。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內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的快速發展,體育概念外延的不斷擴大和體育現象的復雜化,體育概念的爭論在21世紀前后再次掀起高潮,各種觀點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本文對各種觀點進行梳理,并從語言學入手,以名實論為基礎,提出界定體育概念的意見。
1體育概念的爭論焦點
目前國內體育界在體育概念上的爭論焦點是“大體育”是否成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分成兩派:真義體育思想和大體育思想。主張真義體育的學者對國內大小體育的區分和界定提出了疑義。如林笑峰先生[1]畢生呼吁教育體育觀,他指出要嚴格區分“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體育對應的是“physical education”,而不是“sport”。韓丹先生[2-6]在查閱了豐富的外文資料后指出,在國外sport和physical education從來不是一回事。贊同這一觀點的還有吳翼鑒[7]、王學鋒等[8-9]。龍天啟先生[10]對廣狹義體育的劃分也持反對意見,“廣義體育(各種身體活動的總稱)和狹義體育的定義上可以看出,這樣的劃分是不科學的,因為‘廣和‘狹的區分應該只在于體育對象廣、狹的差別,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也有很多人維護現在的界定方法,他們支持大體育概念的理由,大致有以下種種:首先有些學者聲稱這樣的大體育概念(sport)在國外也存在,中國只是效仿而已;其次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了概念上有不科學的地方,但建議維持原狀。如劉秉果先生[11]認為:“體育作為廣義概念的使用,是比較恰當的,對于這樣一個社會上已經約定俗成、習慣成自然的詞語,我們就沒必要對它的概念作較大的更動。”又如譚華先生[12]認為“應該維持‘體育是指所有非功利性、非藝術表演性的身體活動這一規定,因為體育現在已經成為了億萬人約定成俗的語言習慣,改變它的內涵和定義不太現實,不如賦予‘體育以新的意義和解釋,在為數不多的學界人士中謀求一種共識”。再次有張洪潭先生[13]297-302認為“體育”一詞不能譯成“身體教育”,而應該譯成“sport”。最后還有張庭華等[14]認為下定義不能限于形式邏輯,而應該用形象思維或自然語言邏輯。其目的是要否定形式邏輯的概念和本質,為大體育的正當性提供理論基礎。
統觀體育概念的爭論,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事實:1)現在體育界普遍認為體育是競技體育、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的總和,學校體育是大體育的組成部分。這種觀點即大體育觀,把體育歸為“社會活動”或“文化活動”等。如在體育院系統編教材中,把大體育(亦稱體育運動)定義為“以身體練習為基本手段,以增強體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和促進精神文明為目的的一種有意義的、有組織的社會活動。”[15]2)就廣義體育來講,似乎沒有一個現有概念能比較恰當地統領其麾下的三大領域。也就是說,競技體育、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3者根本沒有共同的質的規定性——所謂的大體育的本質。學校體育是教育,大眾體育是生活方式,競技體育卻是一種產業(競技娛樂業),可謂天壤之別。由于競技體育、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之間沒有共同的大體育的本質,所以導致了大體育的定義在種差規定上一加再加,才導致了把臨近的屬向上一推再推,以至成為“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等的結果。
對于以上體育概念的混亂現狀,其中最需要澄清的地方有以下幾點:第一,內涵與外延有反變關系——即內涵越大,外延越小。所以在體育外延不斷擴大的同時,體育的內涵應該是縮小的,而不是和外延一樣不斷擴大。第二,一個概念中的種差規定必須能在所有外延中通約,如若不能就不能被定位為種差。就這一點來看,我國體育概念中的很多“種差”根本就不能通約到外延中的三大體育中去。如上面提到的體育院系統編教材中的大體育定義,其種差規定有:以身體練習為基本手段;以增強體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社會文化生活、促進精神文明為目的;有意義的、有組織的。其中第二點中的幾個目的規定就無法在三大外延中通約,因為競技體育(高水平競技運動)就顯然不是以增強體質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的。這里的錯誤是:廣義體育概念中的所有規定都應該是可以在所有體育外延中通約,而不是每一個規定對應一個體育外延。第三,把體育的臨近的屬說成是“社會活動”或“文化活動”時,其區分能力已經僅限于區分“自然”和“人類”,根本不能把體育與其他人類社會文化活動區分開來。就體育現象來看,至少可以更精確地被歸為一種身體運動或身體活動。
2從名實論分析現有的體育概念
以上敘述的是國內體育概念的大概情況。本文在此姑且不論這種把體育分為廣義體育和狹義體育,認為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和大眾體育共同構成廣義體育,并認為與“大體育”這個概念相對應的內涵規定是“社會活動”或“文化活動”的理論是否準確,但僅僅從語言學名實論的角度來看,把體育概念定位為是一種“社會活動”或“文化活動”絕對是錯誤的。原因在于這一定義(命名)違反了“能指與所指統一”,或者“名實統一”的定義學定律[16]。
“語言可以言說世界,也必須言說世界;世界可以被語言言說,也必須被語言言說,語言和世界是完全同型同構的”[17]。這是語言學的一個主流思想,而這個思想在我國的先秦時期就已經被先賢系統地論證過了,他們包括鄧析、尹文、惠施、公孫龍和荀子、墨子等。當時這類理論被稱之為“名實論”,其中公孫龍著的《名實論》和荀子著的《正名》都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名實問題。公孫龍指出,“夫名,實謂也”(《公孫龍子?名實論》),他認為,名的使用得當就是要恰如其分地指謂它所指謂的對象(“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荀子在《荀子?正名》中也指出,“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他認為“制名以指實”,名亂就會世亂。“制名”的解釋就是“命名”,即用語言符號來代指某一類外界現象。命名過程中用的是符號,但所指的是事物,符號和事物之間必須要對應——“名者,鳴也”,名稱意指的就是所指稱的那個對象。因此,在用文字對現象命名時,必須是“能指”與“所指”對應,否則該命名就不能成立。
“體育”是一個詞,或者說是一個術語。對“體育”這個術語的準確、簡要解釋就是概念,概念所對應的應該是體育現象。然而在當前的大體育框架中,情況并非如此。
先來看“體育”一詞的構成。按照構詞結構分析,名詞中都有一個主體字,這個字只能是名詞,代表該詞的屬,且常置于詞的后部;另外的字對主體字起修飾作用,代表性質,置于主體字之前。如在“步兵”這個詞中,“兵”代表屬,是個名詞,“步”代表特性,意思是“走步的”,用于規定“兵”這個名詞的性質[18]。這一結構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經典的定義公式——“概念=種差+臨近的屬”。“體育”這個詞是“體”與“育”的結合,這兩個漢字組合起來構成了一個在我們漢語語匯中意義明確的詞,就像“德育”、“美育”、“智育”一樣。按照語詞邏輯,“體育”一詞中的“育”字應該是臨近的屬概念,“體”是對“育”的規定,是說明特性的。“育”有生育、養育、培育、教育之意,但能和“體”字組合成有效詞匯的只有“教育”和“培育”兩種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有“身體培育”的說法,只是人們一般不把它簡化成“體育”。“身體教育”的說法早已被人們所接受。這就是說,“體育”這個詞所指的應該是一種教育,有如“數學”中的“學”代表“科學”,表明“數學”是一門科學;“字典”中的“典”代表“典籍”,表明“字典”是一本書。但“體育”無論如何也推不出諸如“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一類的意思。
如此看來,單就“體育”這個詞來講,它既然是“育”,就不能不歸“育”管,因此體育只能是屬于教育,而不是社會活動或文化活動。
有的學者會認為,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所以把體育定義為是一種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也未嘗不可[19]。但問題是,從定義學來看的話,這樣是不正確的,至少是不嚴格的。“所謂定義,是指對于一種事務的本質特征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確切而簡要的說明”[20]。名稱不只是一個抽象符號,它既是被定義項,也包含著定義項。被定義項和定義項必須對應,不能多出,也不能有缺失。被定義項多出定義項犯的是外延過寬(內涵過窄)的錯誤,定義項多出被定義項犯的是內涵過寬(外延過窄)的錯誤,這樣的定義都不完備。如在“單身漢是未婚男人”這個定義中,單身漢是被定義項,未婚男人是定義項;“未婚”與“單身”對應,“漢”也和“男人”對應;“未婚男人”準確地表達了“單身漢”的內涵。很明顯,把體育定義為是一種“社會活動”和“文化活動”是犯了內涵過寬的錯誤,這樣不能讓人很好地把握體育。
也許還有的人會說,名稱只是一個約定,我們可以給他加些新的含義“有億萬人已經接受了這一概念”[12]。這種說法同樣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如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種說法違反了語言的“經濟有效”原則。語言是一個自組織系統,是有生命的,它的目的是用最少的語匯創建一個健康的語言系統,這就是“經濟有效”原則。每一種語言的語匯量都有規定,只有是必要的才把它創造出來,相反,認為語匯越多越能有效地實現語言的功能的觀點是錯誤的。荀子說過:“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成俗謂之宜;異于約者謂之不宜”。這句話應該這樣理解:在每一次創造新詞給外界現象命名時,只能是采取約定的方法,但之后再用這個詞時就不能違反先前的約定了。如上分析,“體育”一詞不是一個毫無實意的新詞,而是一個意義明確的舊詞,并且在它最先從日本引入中國本土時,也是指教育。所以就不能再給“體育”約定意義,否則人們就不知道到底應該遵守幾千年的“教育”規定和最初從日本引進的“體育”規定,還是遵守剛出現幾十年的“體育”規定了。試想假若給“體育”重新約定意義,那么新約定的意義和以前舊有的意義之間勢必產生糾葛。如此強加給語言系統的東西將得不到它的承認,最終只能導致語言系統的紊亂。其次,說體育這個概念已經為億萬人所接受,從表面上看確實是如此,但仔細一看卻并非事實。嚴格的說是億萬人都對“體育”這個詞有所耳聞,也理解它的一些大概意思,但它的確切意思并沒有被大眾所了解,包括從事體育行業的業內人士。至少絕大多數青少年家長不同意“電子競技”也是體育。因此,賦予“體育”一詞新的意義之說也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
還有觀點認為把“體育”譯為“身體教育”并不是必然或必須,僅僅根據“體育”這個詞還可以譯出很多其它的意思來。張洪潭先生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把“體育”譯為“身體教育”不正確,是一個錯誤的直譯。他說,“任何教育都得通過人的頭腦參與方可見效,真不知對‘身體進行‘教育究竟何意?某些人想當然的把體育還原成身體教育,豈不知若一定要還原體育一詞,還有其他好多可能更適宜的詞語:例如身體養育、機體發育、體能訓育、體格培育,這些詞都符合語法規矩。”張先生[13]297認識到了“體育”這個術語的模糊之處,并主張概念問題是邏輯起點,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按他這樣說的去做,根本起不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不錯,任何教育都得頭腦參與,但我們仍然可以稱“有頭腦參與的身體教育為體育”,只要教育的目的在身體而不在腦力。張先生在這里是混淆了教育的對象:教育的對象從來不是頭腦,當然也不是身體,而是人。身體不能接受他人的教育,頭腦也不能,只有完整活生生的人才能。區分不同性質的教育根據的是教育的目的對象,是受教育者身上教育者想改變、培養的那個部分。體育的目的對象是身體,智育的目的對象是思維。體育必須有頭腦參與,但智育也必須有眼、耳甚至整個身體參與。教育的對象只能是活生生的人。張先生還說到“體育(physical education)”一詞還可還原成“身體養育”、“機體發育”、“體能訓育”和“體格培育”,并認為把“體育”還原為“身體教育”是錯誤直譯。張先生的意思是說把“體育”譯成“身體教育”在意義傳達上有錯誤,因為翻譯只能分為意譯和音譯,而張先生并沒有提及應該采取音譯的方法。那接下來看看“體育”意譯為“身體教育”是否不妥。張先生把“體(physical)”字譯為“身體”沒問題(嚴格來說physical應該翻譯成“身體的”,但按漢語習慣可以省略“的”),但譯成“體能”和“體格”顯然不精確。因為體能和體格都只是“體”的部分意思。而譯成“機體”的話同樣是不合適的,因為“機體”是一個生物學概念,而我們談的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所以,“體”字只有被還原成“身體”一詞才是正確的;關于“育”字,張先生認為還可以還原成養育、發育、訓育和培育。其中訓育和培育都包含在教育的意思之內,而如果把“育”還原成養育和發育的話就正好是落入了張先生自己給自己下的套,即錯誤的直譯了。總的來看,張先生是脫離了具體語境,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誤解。就國際范圍來看,存在“sport”和“physical education”兩個概念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一個國際語境。如果要和國際接軌——那就不應該把“sport”譯成“體育”,而把“physical education”譯成“體育教育”。這樣的翻譯無法理解,會讓我們寸步難行。胡曉風同志[21]講過一件往事,“我是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又是中國體育發展戰略研究會的副會長,因為有外事活動,需要印名片,這‘體育一字如何翻譯,找了許多人還是搞不清楚:結果還是翻成了sport,把sport的帽子給我戴上了。我不是搞sport的!外國人看了我的名片說:你是運動專家?我說:什么都不會。外國人又問:你不是研究sport的嗎? 你是sport戰略研究會的副會長,你們的sport戰略是怎么確定的?我說:我不懂,我不知道sport是什么。差到那里去啦!體育怎么成了sport呢?”胡先生的難堪和無奈可想而知。另外,“體育”一詞從學校體育衍化而來,這是一個中間語境,誰也不會把“體育”理解為身體發育,也不會把“體育”理解成身體養育。再者,在今天的現實生活當中人們已經習慣于說“詞”,而不再是“字”,像“身體發育”這樣的詞一般都不會被簡化。最后,學校教育由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育等組成,這是一個小的語境,我們都知道“體育”意為身體教育,是針對身體進行的教育。出于以上的3個語境,本文認為只有把“體育”譯為“身體教育”才是最合適的。
最后是張庭華等人[15]的觀點,他們提出了用形象思維給體育定義,自然語言邏輯,家族相似,概念與詞源無關和事物沒有一個精確的本質等說法。他們利用的工具是和本文所采用的完全背道而馳的思維路線——解構主義。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其步驟有二:顛覆和改變。顛覆意為對先前的解構、否定;改變意為不再構建,只承認游移和變化。張先生等確實找到了質疑經典邏輯學體系的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思想,可以對邏輯、概念和本質產生一定的消解作用;然而事實上他們并不是如解構主義所要求的不再建構,而是在“駁倒”了形式邏輯的概念和本質后,又應用“自然邏輯”去給大體育尋求“合理的”概念和本質。所以本文認為他們并不是解構的,而是純粹的為了駁斥形式邏輯才采用這種反理性的思維方法。這不得不讓人對他們的結論甚至整篇文章產生質疑。另外,在文章中他們引用了“語言沒有精確的定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語詞,就是這個語詞的定義”和“家族相似”(維特根斯坦)[22]之類的思想,來否定形式邏輯的本質和命題等概念。盡管張先生等的文章整體上已存在前后邏輯偷換的嫌疑,但僅就“自然語言”(日常語言)和“家族相似”概念的理解本文還有一些異議:維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自然語言主要是針對弗雷格和羅素等提出的人工語言而言的,意指離開特殊社會情境的語詞和語句其意義都不能確定;相反,語言惟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獲得它的完全意義。本文認為,語言不能離開情境是事實,但自然語言也絕不可能去否定科學語言的語義和邏輯。因為自然語言的應用基礎就是科學語言,不管是在邏輯還是在意義問題上,自然語言都只能是在科學語言的規定范圍內的具體應用,這就像自由只能是對必然的認識之后的自由一樣。我們應該承認自然語言和科學語言之間的細微差別,但不應該因為這些細微的差別和自己觀點的需要就徹底否定科學語言和形式邏輯;就“家族相似”而言,它確有解構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張庭華先生等應用這一學說也達不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家族相似”不僅可以否定真義體育,也可以否定大體育,利用它可以否定一切,其本質是懷疑論的。例如,如果可以用“家族相似”來否定共同的內在本質,只承認在外在形式上有某種相似的話,那我們就不能否定體育和勞動、戰爭等也有某種外在形式上的相似,進而體育自身也會被我們否定。可見,如果真的如此去討論、去做,那么體育學將不復存在。竊以為這也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對于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觀點,我們應該抓住“家族”一詞,而不是沒有任何規定性的“相似”。是一個家族最起碼說明都是一個姓氏的人員,并且是一個血緣比較近的群體才能稱之為一個家族。而家族的內在共性是遺傳基因,姑且稱這些基因也為本質吧。
3建議
19世紀末語言學開始興起,緊接著20世紀初興起了分析哲學,可以說20世紀以來的大部分哲學都是屬于分析哲學的。這也許是被科學理性支配的結果,是工具理性盛行的表現。盡管哲學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是分析的,但分析哲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態度倒是絕對可取的,尤其是對于接近科學(自然科學)的學科而言。科學精神就應該是一種分析精神。本文認為體育概念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其中不乏有語言學的問題。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亦或語言就是思維本身,而語詞是命題的材料,邏輯的起點。因此,語詞的錯誤決定了體育概念問題的難以解決,決定了體育范疇的無法統一,決定了體育學科體系構建的致命難點。
國內體育概念長期不統一,體育學界人士長期的努力也未見成效,這給社會和體育學的發展都造成了不良的影響。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體育現象會更復雜,到時候體育的概念也許會更加模糊。要根本解決體育概念問題,也許最終也得求助于分析的方法。通過本文的分析結果來看,“體育”一詞的內在指謂只能是教育,因而建議把大體育中真正屬于教育的部分條分縷析出來,“體育”這個名稱只能賦予他們;把不屬于教育的部分清除出去,取締它們姓“育”的權力,給它們另取姓名。這就像一個人的姓氏問題,既然姓“李”,就不能否定是李家的人,如果事實上確實姓劉,那就應該把姓氏改過來,否則就會讓世人誤解。至于當今的三大體育,如果它們確能統一在一個大概念之下的話,如何給它們起名,起什么名都還有待商榷。不過像這種情況,翻譯學一般采取音譯的方法,如把“sofa”譯為“沙發”,又如日本把“sport”譯為“斯波特”。
參考文獻:
[1] 林笑峰. 從日本出版《現代美國sport(競技)史》看美國體育思想的變遷[J]. 體育學刊,1995,2(3):96-97.
[2] 韓丹. 論斯泡茨(sports)與體育[J]. 山東體育學院學報,1999(15):6-14,38.
[3] 韓丹. 論“體育”詞的多義理解[J]. 體育與科學,2001,22(1):20-23.
[4] 韓丹. 論斯泡特(SPORT)的源流、發展和當代形態[J]. 體育與科學,2006,27(3):4-11.
[5] 韓丹. 俄(蘇)體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則[J]. 體育學刊,2001,8(2):14-17.
[6] 韓丹. 談跳出中國看體育[J]. 體育與科學,2007,28(2):13-17.
[7] 吳翼鑒. 《我心中的理想體育》質疑[J]. 體育學刊,2003,10(1):18-20.
[8] 王學鋒. 教育學視野下對身體教育與競技運動的思考[J]. 體育學刊,2007,14(9):15-19.
[9] 王學鋒. 真義體育思想對中國體育發展的貢獻[J]. 體育學刊,2004,11(4):7-11.
[10] 龍天啟. 體育哲學基礎[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
[11] 趙進,黃艷. 體育的本質和概念綜述[J]. 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005,21(1):42-43.
[12] 譚華. 體育本質論稿[M]. 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08.
[13] 張洪潭. 體育基本理論研究[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4] 張庭華,楊正云,李興志. 再論“體育”的概念問題——“自然語言邏輯”的哲學闡釋[J]. 體育文化導論,2004,11:16-19.
[15] 曹湘軍. 體育概論[M]. 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85:27.
[16] 韓丹. “體育”就是“身體教育”——談“身體教育”術語和概念[J]. 體育與科學,2005,26(5):8-12.
[17] 李國山. 言說與沉默——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的命題學說[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前言.
[18] 徐通鏘. 語言學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86.
[19] 熊斗寅. “體育”概念的整體性與本土化思考[J]. 體育與科學,2004:25(2):8-12.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現代漢語詞典[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256.
[21] 胡曉風同志在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體育研究會學術報告會上的講話[Z]. 體育學通訊,1989.
[22] 章啟群. 今天是什么?——用哲學的語言說[M].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94.
[編輯:李壽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