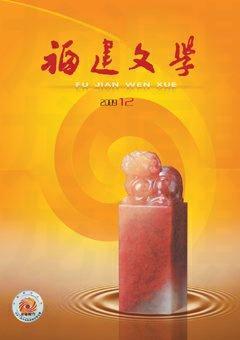“土人”班長
劉耀文
七年前的冬天,一節綠火車皮把未滿18歲的我從江西拉到了福建,從那一刻起,我便有了個名字,叫“新兵”。
我的新兵班長叫王有志。他不高的個子,卻有著一副結實的身板,成熟略帶稚氣的臉上,始終掛著一張嚴肅的面孔。說實話,對于還沒有掛上列兵警銜的我,對班長的崇拜一點也不亞于將軍。我的雙眼曾多次偷偷打量過他肩上那副閃著亮光的警銜,以至于那段時間我把“班長”當成了自己在部隊最大的奮斗目標。
老兵們并不稱班長為“班長”或王有志,而是叫他“土人”。起初我不太明白,后來才知道由來:有一次支隊組織看電影,當銀幕上出現影片名“沖出亞馬遜”五個大字時,班長激動地大喊“沖出亞馬孫”。從那以后,“土人”就代替了“王有志”三個字。
長時間的相處,我發現只有小學文化的班長的確有些“土”,他的談吐甚至有些粗俗。但正是從這種粗俗中,我感受到了鄉村人的純真和樸實,看到了軍人的堅毅和剛強。在我心中,這位“土人”班長就是一位親近的兄長、勇猛的斗士。
那天晚飯前,班長組織我們在器械訓練場練習雙杠。這是新兵連開飯前的必修課,也是我最弱的科目。因為我的動作不規范,班長罰我撐在雙杠上定了半小時的型。晚上熄燈后,雙手酸痛的我根本無法入睡。班長見我在床上轉動,便前來詢問原委。可我不敢說手痛,只好撒了個謊說肚子餓睡不著。聽完我的話,猶豫片刻的班長離開了房間。大約過了十來分鐘,他從大衣里端出碗熱氣騰騰的面條出現在我床邊。班長把我扶進懷中,一手抱著我的后背,一手給我喂面條。透過昏暗的手電光,我發現這張在訓練場上嚴肅的黑臉,瞬間變得如此熟悉和溫馨。他就像母親,每挑起一夾面,就輕輕地吹幾口,爾后送進我嘴中。
內心愧疚的我當時并沒去想面條是怎么來的。直到第二天,班長做檢討時,我才知道那碗面條是他翻圍墻偷跑出去買的。
生活中對我們細心照料的班長,在訓練場和戰場上卻變成了一個勇猛的“土人”。
新兵連的訓練場是塊還沒修建好的坑坑洼洼的石沙地。訓練走正步時,班長嫌我們的腳步聲不夠響。有人便咕嚕:滿地都是石沙,誰敢用力踢。戰友的話剛落,就見班長卷起褲管光著腳在石沙地上“啪啪啪”來回踢了好幾遍。從那以后,整個新兵連便數我們班的正步踢得最好最響亮了。令大家刮目相看的還是班長的戰術動作。他十米開外提著步槍沖鋒,緊接著快速臥倒,整個身體在地面上劃出一道五六米長的迷彩弧線,爾后“啪”的一聲響,便端著槍穩穩地匍匐在地面上了。我曾多次學這套動作,可每次不是臥倒的速度太慢,就是槍出來沒有響聲。我問班長該如何去練,他只是 了 頭笑著說:“你不夠土!”
三個月的新兵集訓在苦難與期盼中結束了,幸運的我被班長直接帶到了他所在的中隊。我又成了他班上的一個兵。
分到中隊后,班長對我已沒有在新兵連時的嚴格了,但因為我沒耐性,做事慌張,已幾次受到他的嚴厲批評。
那天晚上,班長冒雨從后勤班端來一碗米。正當大家不知道這米的用途何在時,班長對我說:“好好數一數,睡覺前告訴我有多少粒。”我不明白班長的用意,但心想既然是班長要我數,那肯定有他的用處。我一五一十很認真地用了半個多小時數這碗米,可當我把一萬零五粒這個數目告訴班長時,他卻說我數錯了,還命令我明天重數。
連續數了幾天,每次我一報數目班長都是說數錯了。后來,我干脆不數了,每次都在前一天的基礎上加幾粒或是減幾粒。看出我的心思后,每天一到數米粒的時間,班長便坐在我身邊盯著我。這樣一來,我只有一粒一粒認真地數了。數到第十五天,班長才讓我收起那碗米,并對我說:“如果你還沒耐性,我就換個臉盆給你數。”原來班長要我數米粒是為了磨煉我的耐性。
連續多天的大雨仍下個不停,這可樂壞了我們這幫不愿訓練的新兵。可班長卻嘆著氣說,別高興得太早,很快就會有任務的。當我們還沒理會班長那句“很快就有任務”時,中隊便接到參加抗洪搶險的命令了。
由于我是剛分配到中隊不久的新兵,還不具備上前線的資格,所以沒能親眼目睹班長在抗洪搶險中的“土人”風采。從老兵們口中得知:時刻沖在抗洪搶險最前線的班長為了救被困群眾,被泥石流沖走了。當大家以為班長遇難了時,他卻被另一股泥石流沖了出來。已變成泥人的班長從地上爬起來,用手揩了揩臉上的泥漿,便繼續投入到救援中去了。手術時,醫生護士被班長感動得淚流滿面——班長的肺部全是泥漿。
班長是支隊的特戰骨干,擔負急險難任務是常有的事。
班長出院不久,又接到了協助公安機關追捕在逃犯的命令。沒想到的是,他那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班長出動的第二天上午,隊長接了個電話就匆匆忙忙趕去了醫院,下午回來時,便帶來了班長犧牲的噩耗。
班長追捕的逃犯是個集偷盜、搶劫、殺人于一身,無惡不作的犯罪團伙,他們深藏在山林中。搜索到犯人后,班長用嫻熟的擒敵術拿下了兩名罪犯,當他準備撲向第三名罪犯時,一把長長的尖刀刺進了他的胸膛。
“命令已下,還沒公布……”一位支隊領導在清理班長的遺物時說。
原來班長在上次抗洪搶險中榮立二等功后,已經被直接提干了,但還沒來得及公布,他就犧牲了。
班長走后不久的金秋十月,我被調到中隊部接替年底將退伍的文書的工作。
事后從隊長口中得知,班長曾多次向中隊力薦我接任文書。中隊領導擔心我這個急性子干不好文書這份細心活,班長便向領導保證,一定讓我改掉沒耐性這一壞毛病。直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班長要我數米粒的苦衷。
窗外又下起了大雨,聽著嘩嘩的雨聲,借著微弱的燈光,我從床頭柜里端出那碗已泛黑的米粒,一粒一粒地數著。作為一個新兵,我還能靠什么寄托對班長的哀思呢?
責任編輯 賈秀莉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