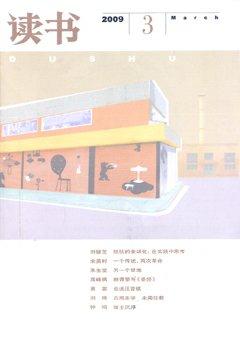一個廢墟上的棲居者的思考
郭 軍
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不是一本可從教育管理專業角度來評價的著作,他的專業領域是比較文學,生前是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而關于大學體制這樣一個話題,正如喬納森·卡勒所說,往往是大學中那些退了休的行政管理者才有資格去說的,但是,也正如卡勒所注意到的,出自那些人之手的同類話題的書,一出印刷廠,就只能在書店的處理圖書柜臺上銷售,而出自雷丁斯這位非專業人士的著作,卻引起反響,至今仍是熱門話題。
其實,這正是雷丁斯的非專業身份所帶來的不同視角使然,這個不同視角被形象化地概括在他的書名中,即他把當下管理體制越來越健全的一流大學看做廢墟。但他不想拯救廢墟,也無意離開廢墟,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廢墟上的棲居者”,因此必須面對廢墟,思考如何利用廢墟,使之擔當起“從未有人提過的角色”。他稱這是他的“實用主義”。
他之所以持這種態度,是因為他把當下大學管理者們已經認為理所當然的、并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的大學理念,即發端于美國大學的爭創“一流大學”(university of excellence)的理念,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量化評估、企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一概視之為對現代大學賴以建立的原初理念的背叛。
所謂“現代大學”,雷丁斯指的是與中世紀時由外在原則——即神正論——監督的大學相反,具有內在指導原則并以此來自治的大學。其自治的標志就是不迎合任何權勢、堅持真理、自由探索的理性精神,這是它的終極所指、目標和各種活動的統一原則及意義所在。雷丁斯把這種大學理念的起源追溯到康德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院系的沖突》(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寫于一七九五年,出版于一七九八年)。這部著作所針對的語境是普魯士時代大學的四院制結構,即神學、法律、醫學、哲學學院,其中前三者屬于較高等級學院,因為它們為國家培養專業技術人員,即牧師、律師、醫生,所以需對國家負責,而國家則有責任調控其教學內容。相比之下,哲學屬于較低等級學院,因為哲學沒有上述實用功能,除了對理性負責,它不盲從任何外在權威,包括國家和民族。在教學中,它質疑一切提供現成答案的“魔法師的才干”,教導學生使用理性進行思索與批判。在院系沖突中,它致力于使理性成為各學科的基礎,并具有絕對自治性。但同時它又保證理性并不因此成為另一種權威,而是不斷自我批判,使得理性的干預不是要產生同一性,而是旨在制造“不合的和諧”(concordia discors),即產生以探索、爭論、沖突為理念的共識,這也是制造健康的、和平的、合法的,具有創造性和更新性的沖突,由此而不斷給大學注入活力。從這種意義上,批判哲學或理性是智識(intellectual)的天堂、思想的王國,培養的首要目標是學生超越蒙昧、迷信、盲從的能力,而不是專業技能。
由此,康德把原來的等級顛倒過來,把哲學看做較高等級學院,看做一所大學的主導性院系,它教育并監督其他學院,借此,康德想達到的目的不僅只是改革大學,更是想讓發生于大學中的這種在自由的理性探索與無條件接受既定權威的傳統之間的永久沖突影響社會,催生人類的不斷進步。這點可從他同時完成的另一部著作《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中見出,這部著作的基本觀點是,只有用哲學的批判精神不斷質疑權威,才能真正創造和諧社會或永久和平。由此,理性盡管不直接與社會關聯,卻是社會的“秘密偵探”,監視權力泛濫,保證社會公正。從這個意義上,理性已經具有了德里達意義上 “理論陳述話語”(theorico-constatifs)和“創造行為句”(poetico-performatifs)的雙重功能。換句話說,理性既是作為行動或事件的思想,又是作為思想的行動或事件。
雷丁斯把康德設想的大學稱作理性大學(university of reason),但這在當時畢竟只是設想或理想,且康德在理性與國家、智識或思想與體制或管理的沖突問題上如一個本達式的知識分子,不留任何妥協的余地,所以“現代大學之母”洪堡柏林大學建成后,在其發展過程中,在接受理性大學自由探索的精神、接受哲學為主導學科的基礎上,提出以文化理念代替理性理念,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內在于康德理性理念中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十九世紀德國民族崛起的形勢,以便既造就理性的主體、又造就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體,由此大學真正進入現代,開始以揭示主體與國家的關系為己任,并在教學與科研中灌輸這種關系,具體體現為把傳授科學知識、打造思想和培養國民道德修養、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融為一體,而洪堡直接將這種融合叫做文化。在這種原則指導下的教育是一個將產品與過程、技能與修養、知識與思想、實事與批判、專業與責任相結合的有機整體,但重點在后者。由此,這種教育,盡管關注國家與民族,卻又不是造就服務者,而是造就主體。雷丁斯把洪堡大學稱作文化大學(university of culture)。而這樣的理念后又匯入紐曼所倡導的智識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教育,紐曼又稱之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可稱博雅教育、通識教育)或哲學教育(philosophical education)。
綜上可見,無論是康德的理性大學,還是洪堡的文化大學,以至紐曼的自由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一個烏托邦工程,它追求的首先是打造人性、塑造公民,而不是訓練專門技術人員。在這樣的大學,校長就是其理念的化身,因此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對外傳播他的辦學理念,對內則以其理念為原則,調整院系沖突,組織教學與研究,使兩者構成教育整體的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能夠生動演繹教育的整個過程。這樣的教育敘事,講述的是一個啟蒙、解放、成長的故事,作為主角的學生從蒙昧、無知、自在走向理性、博雅、自為、自治、自主,同時,這樣一個主角又是一個轉喻,體現了國民的成長歷程。
但是這樣的大學及其理念到了當代這個全球化即美國化的時代,被美國人提出的“一流大學”(university of excellence)理念所替代,原先的價值原則讓位于現在的一系列操作指標和量化計算,大學越來越按照企業或大公司的管理模式運作,校長變成了體制的管理者,不再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發表言論,更多地忙于籌措資金、拉來項目;在學校的運作上,重點也相應轉移,從研究與教學轉向管理與經營,大學故事的主要人物現在是教務長。同時,研究越來越專業化,與教學脫鉤; 而學校與學生的關系則走向服務和接受服務的市場消費關系。總之,大學教育進入了一個橫向的市場競爭體系,它與思想、民族、文化的縱向聯系開始松弛,因此它的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感衰微,而競爭意識增強——它追求在競爭中達到“一流”。
雷丁斯睿智而深刻的分析與批判便從這里開始,靶子便是“一流”概念,他認為這是一個沒有所指的空洞概念,一如一個索緒爾意義上的能指,它并沒有確定不變的意義或質量內容,而是一個體系(或內部市場)的比率原則,而能夠類比的是數量、指標、效益,至于質量、意義、價值的內容則在所謂科學化(或技術化)管理的各種圖表上再也找不到可置放它們的欄目了。由此,雷丁斯對 “一流”理念的第一種解讀是; 它是“解指涉化”的, 它就像貨幣關系,并不以實質的東西為統一價值標準,而是以一個流通體系內的可計算性和可交換性來操作,與內在于前兩種大學理念中的責任性(accountability)相比,“一流”管理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會計學(accounting)了。英文中這兩個詞貌似神離,不可同日而語,但“一流”管理卻把它們變成了同義詞。
一旦如此,必然產生“一流”理念的第二種特征,即,“解政治化”甚至“解意識形態化”,這是量化操作的必然結果,似乎也是全球化時代大學的必然命運,因為主導全球化時代大環境的跨國聯營公司的特征就是“解政治化”和“去民族化”,同樣趨勢在大學中的不可抗拒性和吊詭性,根源便來自于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巨大影響。眼下的跨國公司為了給資本尋找盈利機會,以便在競爭中處于一流,并不在乎民族疆界,也不在乎掙自己國家的錢。民族國家及其文化已不再是它聲稱要效忠的理念,而只是其資本流動中的一個因素,它真正效忠的是團隊(即公司利益)。當然,國家并沒有消失,但只是一個官僚管理機構,已經無法在經濟事務上推行其政治或意識形態意志。而經濟不再受制于政治,變成獨立實體,這已被認為是良性經濟的標志之一。然而,這塊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在全球化經濟時代,民族及其文化不再是一個象征層面的終極視域,個體在這種經濟模式中不再具有民族主體的身份和意識,他只是一個參與公司運作的技工,因此他的存在是非政治的、他的所屬關系是非意識形態的。這樣一個個體,又正如馬爾庫塞意義上的“單向度的人”,已經成為一個單向度社會的一部分,不再具有批判、向往、超越的意愿。用阿甘本的話來說,在這樣一個時代,小資產階級在全球出現,他們是千篇一律支持芝加哥公牛隊的一代人,“真理或謬誤,……對他們都已經失去意義,不再有任何表意和交流的功能。在他們身上,構成世界歷史的悲喜劇特征的各種差異被聚合在一起,以一種怪誕的方式顯現出來”。這在阿甘本看來,就是“存在之荒誕性”,但已成為人們渾然不覺、心安理得的日常生活。
這種環境給大學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大學要培養的理性和民族主體“我”之意義所在,全在于其所歸屬的共同體“我們”,但這個“我們”,無論是文化的、還是批判理性的,都正在消解, 因此在以“自我成長”為主題的大學宏大敘事中,目標不再是民族或理性主體,而是一流競爭者。而更關鍵的是,資本吞并一切的潮流也沒有放過大學,大學的“一流”評估,本身就是一個高等教育中的市場競爭機制。其結果是大學越來越從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機構走向一個相對獨立的經營機構,甚至有成為德里達所說的“集團或大公司的分店”的危險(《德里達中國演講錄》,111頁),其為民族國家培養民族和理性主體的使命讓位于各種任務指標的完成,包括各種資金數量、影響力指數、就業率等等,其科研和課程設置等方面也必然進行相應調整,以適應各種競爭。總之,它越來越需要學習企業化運作,而不能再以一個象牙之塔而自居。從這個意義上,雷丁斯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即洪堡意義上以承擔國家和民族文化為使命、以監督國民精神生活為己任的大學已經走到了黃昏時代,成為“后歷史大學”,即德國唯心主義那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大學的幻影,無理念、無文化、一無所指,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已成廢墟。
但“一流”理念的吊詭性在于,在解政治化、解意識形態化、沒有實質的價值內容、只要衡量不要判斷以后,它似乎成了一個如來佛的手心,誰也休想蹦出去。這不僅是指一切均受到量化評估和體制化管理,更指的是,這種量化管理可以吞并、消解、收編任何批判、激進、另類的思想,使它們按照對體制有利的方向流通,所以任何諸如此類的東西,如今不僅撼動不了這個管理體制,反而會正因為其別樣面貌而容易成為學術市場上的貴重商品,創造一流業績,為大學提升影響指數,帶來新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任何對峙都能被變成合作或共謀,這就是為什么,激進主義在西方大學市場一路暢銷,甚至用德里達意義上的替補邏輯來進行的解構和顛覆性批判,一旦作成一流學術水準,都有可能被轉換為剩余價值。而諸如一九六八年那樣的“學運”如今也無濟于事,因為它可以作為創造一流校園生活的事件而被整合到體制中去。
更讓人絕望的是,為上述局面提供佐證的正是如今聲稱主導大學人文理念的旗艦學科——文化研究。它聲稱要開創新范式來統一傳統學科,通過文化批判而恢復大學使命。這樣的旗艦地位曾被德國唯心主義者們賦予哲學系、被英國人賦予文學系,這兩者都曾經是“元學科”,即具有康德意義上的哲學主導性或洪堡意義上的作為指導原則、內在精神而貫穿在大學教育中的文化理念價值。但“文化研究”已今非昔比,它不再具有“元”地位,而是眾多被研究的對象之一。這本身就是文化理念衰微的表現,意味著這個“文化”已經不再是能夠賦予象征生活以意義的終極所指,而是學術言說的東西,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但無論以何種面貌登場,它們都不能給體制帶來所聲稱的政治差異或威脅,相反,諸如大眾文化研究,反而給體制帶來進一步投資的場所和商機,如對朋克音樂、怪異服裝、旅游景點的研究,就將它們提升到商品地位,使之具有了可售性。用阿多諾的話說,這種研究名義上追求唯物主義透明度,但實際上沒有使自己更誠實,反而更粗俗。
而那些反文化排斥(如中心對邊緣的排斥等)、倡導多元文化的研究,自以為具有顛覆性,但雷丁斯告訴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已經沒有文化堡壘可攻占,中心已是空穴,而尤其是,文化研究宣稱一切都是文化,那便意味著沒有可被排斥出去的可能了。至于倡導多元文化,更是無濟于事,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另類版本的“美國化”。如果認為這樣的研究有什么震撼力,那是忽略了體制的存在,在自己所建的空中樓閣中沾沾自喜。
總之,在雷丁斯看來,文化研究聲稱提供新范式來救贖大學,這是不可能了,反倒是一流管理體制下的大學拯救了那些處境尷尬的教授,給那些由于傳統人文學科衰敗而落魄的教授創造了留在大學的機會,因為如上所述,一流評估體系反倒成全了許多激進研究,如女性主義、非美研究、同性戀、酷兒理論等,使他們又得到布迪厄所說的參與文化資本分配的機會。
當然,雷丁斯并不如三好將夫等學者那樣,認為某個個人有什么可指責的,他如卡夫卡一樣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機構中再沒有個體英雄。大學的轉型、人文學科的破產不是個人與誰共謀的結果,而是在全球化形勢下的必然命運。
但是雷丁斯并不懷念旗艦學科引領下的大學,他彰顯內在于前兩種大學理念中的統一性、完整性,只是為了比照出“一流大學”的空洞,在完成了對比的任務后,他不僅立即放棄啟蒙敘事,反對培養主體,甚至認為,現代大學將一理念置于中心頂禮膜拜、并使教學和科研都依賴之的傳統,給了當下大學將官僚管理置于中心的機會。在這個問題上,他似乎有“求若珍寶,棄如敝履”之嫌,但實際上,這是他的清醒與務實。他認為,在經歷了法西斯主義、各種意義上的帝國主義以及“冷戰”意識形態的歷史教訓以后,再談回歸民族主義、主導原則等,不僅不再可能,而且充滿危險。在這個問題上,他深受阿多諾,德里達等人的影響,認為任何一種絕對原則或絕對主體的聲稱都會導致新的盲從、迷信、霸權、壓制。所以,他認為,對廢墟唯一有效的利用不是修復,而是拆解,即拆解任何意義上的中心。
如何進行?他提出以“思想之名”來操作,但什么是思想?思想是否會成為另一種理念、原則,并由此而成為另一個中心?雷丁斯借用海德格爾的界定繞過了這個陷阱,因為海氏的界定強調一種無限的開放性和對話性,即思想是一種由無數伸出的、接受的、歡迎的和受歡迎的手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禮物,是一種將我們的本質存在與思想聯系起來的召喚,思想送出的禮物就是思想本身,回應思想的召喚就是接受一種使命,去保存思想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質疑的地位。而思想所質疑的就是絕對主體性和絕對真理的意識形態,其運作方式就是為差異命名,引起爭論,但不提供解決方案,不提供元語言,不把自己變成一個能夠終結一切討論的指意行為,用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們》中的術語來歸納之,即思想是一門“幽靈學”(hauntology),一種對無限開放性和未來可能性的追索,而不是“本體論”,只追求為一個僵尸蓋棺論定。
以思想之名來操作的教育不是培養主體的自主、自治、解放意識,而是依附意識、他治意識,即對他者的依附,并以他者的存在反思、質疑、批判自我的理所當然性,這既是教育的責任和義務,又是教育交給學生的責任和義務。這種教學得以展開的條件是布朗肖所說的“對他者的無限關注”,而這在勒維納斯的倫理中便是正義,所以這種教學回答正義而不是真理問題,培養承擔“義務”的個體,而不造就追求“解放”的主體。
為實踐(而不是完成或終結)這樣的責任和義務,雷丁斯不再指望旗艦學科,而是訴諸所有教學場所,他要讓教學場所本身就成為這樣一個大的義務網,實地演繹思想的運作,所以,在此,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不再是主體,而是對話的一方,但這不是哈貝馬斯意義上能夠最后達成共識的交往行為,而是上演巴赫金意義上的對話主義,在此,對話不是發生在主體間際,而是話語間際,因此最后是不會由一方收編另一方的。老師的角色不是行政官,而是一個修辭家,但憑借這種身份,他并不發揮說服功能,而是如拉康在其精神分析中所借用的偵探杜邦的形象,表現為一個具有跟蹤能指的非凡能力的角色,既不會落入他人掌控的圈套,也不會像警長一樣受到誘惑去尋找實質性內容。借此,他維持教學場所的開放性,以價值判斷的參與替代知識劑量的分發,同時價值不再作為一個中心、而是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從而保持其開放性,而大學則被定位為是發問的許多地方之一,不是唯一。這樣的教育時空體與按時完成學業等量化時間流程的不同,就在于,這種教育雖發生在那一刻,卻影響學生終生,使思想成為他們終生的嗜好。
由此大學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共同體,但是這個共同體不再以“共識”為凝聚力,而是以差異,說得更確切一些,以承認彼此的差異為基礎,用雷丁斯悖論式的語言來說,即,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我們都同意我們是有分歧的”。他把這樣一個共同體叫做“各執己見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dissensus),這是把哈貝馬斯的“共識”(consensus)換上了否定前綴而構成的新詞,如果這樣一個共同體有共識,其共識就是這個“解共識”,因此也是解權力、解把控、解輕信、解盲從。這是雷丁斯這個“廢墟上的棲居者”對大學空間的新的設想。盡管他拒絕談回歸,但是實際上,他回歸了理性大學的理念,只是用德里達的警惕、勒維納斯的智慧進行了調整。
他稱這只是為了打開新的空間,而不是什么宏大政治舉動,更不是彌賽亞救贖的任務。但他實際是用德里達式的“沒有彌賽亞主義的彌賽亞”理想來構想新的大學空間,也正因為如此,他讓我們看到差異、遠景、可能,我們這些“大學里的棲居者”很難不為之所吸引。
(《廢墟中的大學》,比爾·雷丁斯著,郭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