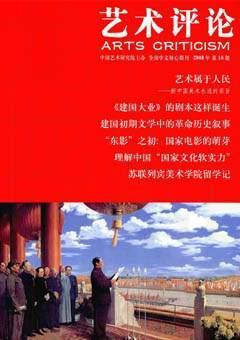作為先鋒文藝實驗的十七年戲劇
一
要認識十七年戲劇尤其是工農兵題材戲劇的“創造力”,應當把它看作中國當代戲劇的一個最初的實驗時代,社會主義戲劇的實驗時代。我們不能僅從表面上來看待它的藝術價值和成績,而要從戲劇的可能性來看。這種實驗是在戲劇中探討一種新型的、代表人類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的社群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在社會中的存在方式。
與此同時,它也是對人的舊的存在方式的批判。這種批判,與當時世界范圍內的先鋒戲劇運動是息息相通的。像美國阿爾比的《動物園的故事》、英國品特的《情人》、西班牙布魯埃爾《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電影)等一大批作品,也都是對資產階級的生活展開了尖銳的批判。《年輕的一代》等中國戲劇在國外演出成功,獲得觀眾歡迎,正是由于這種息息相通。其區別在于,歐美國家的先鋒戲劇乃是單純的“說不”的批判,其精神核心是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戲劇實驗,不是簡單地對人的舊的存在方式“說不”,而是希望建立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其精神核心接近于布洛赫的“希望的哲學”,亦即,展示那些不應該存在而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用的,關鍵在于展示那些應該存在而暫時沒有存在的東西,以及通向它的可能。
當時一些廣受歡迎的戲,比如1950年代前期的一批婚戀家庭劇,以及所謂“第四種劇本”的戲,都是以有人情味、有生活氣息而著稱的,但此后的研究者如果就此認定人的個體性存在才是戲劇中惟一合法的存在,卻是片面的。剔除掉對人的社群性存在的理解而單獨強調個體性存在,實際上也就取消了這些戲劇的價值所在。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范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玄學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
要正確理解工農兵戲劇,就要認識到這些戲劇中的個體存在,絕非馬克思諷刺的“玄學家們”宣揚的“純粹的”個體存在,而是與社群存在緊密相連、“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個體存在。所以,比方說,在《年輕的一代》中,正面主角肖繼業義無反顧地從上海來到青海的勘探隊才會感人,反面主角林育生想裝病留在上海才會讓人厭棄;在《千萬不要忘記》中,姚母的種種個人主義(代表人的舊的存在方式)的臺詞和行為才會顯得滑稽可笑,丁純如在姚母的鼓動下越來越軟弱,才會讓觀眾覺得可惜。在這些戲中,一個充盈的、把人的社群性存在與個體性存在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大我”,總是比那些猥瑣的、貪圖種種小利而喪失健康的社群性存在、畸形發展的“小我”顯得更為可愛,更有幸福感。《千萬不要忘記》原名《祝你健康》,就是這個意思。這些戲并非僅僅是“圖解政治”,它們講的就是切切實實的個體生活的事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是一種宏觀的政治理解,而這些戲在藝術上是把握住了社會主義戲劇實驗的微觀有效性的。能夠獲得當年如此多觀眾的肯定,并非偶然。工農兵戲劇就是希望在戲劇中探討如何實現“大我”、如何不蛻變為“小我”的實驗。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對那些略嫌生硬的實驗持有寬容的態度。比如《豐收之后》,一些學者認為,全劇斗爭的焦點,過于強調將余糧賣給國家,并不符合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兼顧的原則,難免有些不切實際,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要認識到,正是因為當時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的目光短淺的習慣思維,才更需要在劇中為無產階級樹立理想的“大我”的人格模范。個體存在的犧牲奉獻,將在社群存在中得到“復活”。個人在社會主義建設艱難起步的“大我”充盈之中,獲得“小我”前所未有的充盈。
二
“第四種劇本”多是工農兵戲劇。其中最著名的三部戲《布谷鳥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簫橫吹》都是農村題材,都涉及到農業合作社的問題,只是它們并不局限于入社和不入社的問題,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具體而微的人的復雜處境。其中《布谷鳥又叫了》最為突出,堪稱這一批作品中的代表,因為它討論的是個體應該以怎樣一種地位和姿態在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在1957年問世的《布谷鳥又叫了》這部戲中,我們看到一個這樣的世界,或者說,作者希望呈現出這樣一個世界:在這里,在經濟生活發生變化的同時,人們的精神生活、人際關系和情感結構也發生著變化;合作社不僅是合作生產,而且把村民變成了男女社員,大家共同參加生產勞動和社里的集體文化活動;自由戀愛,媒婆不再可以因為婚配而從中謀利和搬弄是非了;婦女也因為一樣掙工分、提升了經濟地位也提升了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再懼怕丈夫的權威,女性不再是男性的私有家產,而是獲得了獨立的人格地位和社會存在,不僅屬于家庭,也屬于社會(作為社員)。總之,合作社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重新組織了社會人群。
但是《布谷鳥又叫了》的突出之處在于不僅沒有以“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下去”這樣一種童話敘事方式來無視生活的復雜面,也沒有以“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樣一種主流的解決矛盾的視角來簡化問題,而是表現出這種新的理想社群性會受到舊的社群性習慣的挑戰。妻子,丈夫,戀人,等等,這些先出現的規定人際關系的詞匯總是附著它舊有的一切理解橫亙在類似“社員”這樣的新詞之前。
比如,不僅是像雷大漢這樣的莽漢子具有舊思想,而且像王必好這樣的有知識有文化被認為是思想先進的團員也一樣,想把女性繼續當作自己的私有家產。在這里,王必好和雷大漢沒有本質區別,無非雷大漢只會訴諸于肢體暴力——傳統的男性對女性的私有式的社群習慣,而王必好則更學會把自己的這些(其實相當傳統的)意愿與新的社群理想聯系起來,指責童亞男為“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不正”,認為童亞男是以一種與新的理想的社群生活相對立的方式來生活。這就使問題復雜化了:矛盾的雙方從不同的立場出發,都認為對方是阻礙新的理想的社群關系的力量。
如果這部戲的作者再多一點耐心,這個實驗可能會做得更加完美,但作者明顯偏向童亞男、童亞花這一方,認為王必好、雷大漢這一方顯然是錯誤的,這就使人物的描寫明顯帶有夸張和增飾。寫王必好幾近漫畫人物,雖然可以博得觀眾一笑,但卻削弱了此劇討論的問題。作家吳強(《紅日》的作者)當時就提出善意的質疑:把王必好寫成這樣,真讓人不能理解當初他和童亞男是怎樣戀愛上的。
其實,不僅是王必好、雷大漢帶有舊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痕跡,童亞男本身也并不能逃脫這個“原罪”。當她的意愿受到壓抑的時候,她的情緒表達和抗爭方式,確實也帶有相當的個人主義色彩。也就是說,作者非常不自覺地用人的個體存在壓倒了人的社群存在。這時,人與人之間可能的真實交流實際上已經被切斷,因為社群方式已經被舊有的個人主義方式破壞,每個人,包括作者希望樹立的正面人物在內,都是躲在自己拉來的為自己的個人沖動充當理論武器的觀念背后,希望拿觀念壓倒對方,而不是自己站出來說話。
在《同甘共苦》、《洞簫橫吹》等“第四種劇本”的劇作中,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本來是為了反對一種激進的實驗方向(人的社群存在壓倒人的個體存在),卻又有了另外一種偏狹的危險(人的個體存在壓倒人的社群存在)。
三
整個十七年戲劇,假如從表面的創作實績上來說,確實是在一類對人的舊有生存方式進行批判的劇作中更能看到其成就,尤其是一些純粹的批判式劇作,由于與西方先鋒劇作的同構性,更容易進入今天我們的視野,比如《茶館》。
問世于1957年的《茶館》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生動的舊式生活方式的圖景:在這里,人群聚集,但彼此孤立,毫不交流,所有意愿、意志、理想,所有的掙扎與努力,都是極端個體化的,于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由社群性來聯系,而是被現實原則的“功能結構”緊緊地控制著,不管你愿意被控制也罷(宋恩子:“誰給飯吃,咱就為誰效力”),不愿意被控制也罷(常四爺:“自食其力”“憑力氣吃飯”),都逃不開這個結構的羅網(王利發:“這路事太多,您管不過來”)。常四爺憑良心干了一輩子,自食其力,最后也落得個“一事無成”。王利發精明強干,自以為看得清形勢,也只能是上吊收場。尤其是林兆華導演的1999年版,舞美設計使整個舞臺被一個過分巨大而歪斜破敗的木質樓宇結構從三面直壓在劇中人的頭上,顯得極其陰沉壓抑,更是吃透了劇本中所潛藏的這一層精神內涵:對舊式生活方式的批判。
老舍寫作《茶館》的時代,是寫的“過去”,所有在臺上演出的演員、在臺下觀看的觀眾,都是在看一個已經被埋葬的“過去”。這個“過去”越是讓“人”死去,那么大家所處在這個“現在”就越是讓“人”新生。那個時候的觀眾看這個悲劇,能夠產生一種喜悅情緒,因為這種不言而喻的社會大背景,讓觀眾能以“大我”的心態來觀看“小我”的卑微人生,覺得劇中人的所有掙扎與努力之所以沒有出路,是沒有擺脫舊有的生存方式,亦即個人主義的自我奮斗。日本友人看到當時赴日演出的《茶館》,也說“故事是暗淡的,但舞臺是明朗大方的”。可見這部戲當時是存在雙層表意結構的。
當時比較傾向批判舊有生活方式的戲,大多與建設新社會的語境相一致。從作家創作的戲如夏衍的《考驗》,到民間流行的戲比如當年紅極一時的滑稽戲《滿意勿滿意》,都是如此。《滿意勿滿意》寫一個合作食堂服務員抱著“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的舊觀念,因而鬧出許多笑話。它的喜劇效果,也是和當時的社會氛圍分不開的。它的很多批判性的笑料,也需要在時代的語境中加以解讀
還有一批優秀歷史劇,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漢的《關漢卿》、朱祖貽的《甲午海戰》等,也都具有十分鮮明的社會主義戲劇的氣質。《甲午海戰》在充分揭示帝國主義的陰險兇殘、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同時,著力描繪了人民群眾的抗敵精神。這種抗敵精神,與臺下觀眾的精神面貌是同構的。因而這樣一個描寫失敗戰爭的戲,也同樣有促人奮起的積極效果。這和《茶館》有相似之處。《蔡文姬》之所以能為曹操翻案,也是從大處著眼,把曹操塑造成一個散發著“大我”光輝的形象,因而他的各種行為就跳出了傳統戲劇“帝王將相”的個人主義的忠奸譜系。《關漢卿》也是如此。當我們看到結尾“盧溝橋送行”一場,見到那么多普通百姓、文壇摯友趕來送行時,終于明白:關漢卿之所以敢于迎擊整個罪惡社會的挑戰,是因為他并不勢單力薄,廣大的被壓迫者都在他這一邊。因此他才能以一個高大的“大我”形象來俯視那些蠅營狗茍的“小我”。
關于歷史劇的論爭,在十七年戲劇的歷史時期是一件大事。吳晗認為歷史劇必須要有充分的歷史依據,而另一些較為激進的論者則認為史書上的所謂“歷史依據”是統治階級“賴以認識并反映過去時代社會生活的一種材料”。[1]這其實也是相當先鋒的一種論調,與1960年代福柯提出的反對“遮蔽”的知識考古學隱約相映。
四
傳統戲劇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演員技藝,演員以其高超的技藝與觀眾直接交流,這往往是戲的關鍵。然而十七年戲劇有強烈的表意沖動,當然排斥這種演員和觀眾的直接交流,因為這種交流會把演出的能量在每個能量點上即時消費掉。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之所以能迅速主導社會主義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斯式提出,“和觀眾交流的最好途徑就是通過和劇中人的交流”[2],他發展出一整套方法,來促進演員作為角色的相互交流,杜絕演員與觀眾的直接交流,以此來保證不是依靠一兩個演員的技藝,而是依靠整部戲的精神力量來打動觀眾。
十七年戲劇時期,這種表演體系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導演和演員,尤其是在話劇領域,為許多優秀劇目的上演做出了貢獻。這其中既有翻譯劇作,又有越來越多的原創作品。然而,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意識到的,這種演員作為角色的相互交流和影響是非常不容易實現的。尤其是當劇作中的社群存在本身變得不甚真實的情況下,就會使一部戲充滿了互相假裝搭話的仿真的交流。這時,一部戲會失去最鮮活的劇場感,對白變得極其沒有效率,戲劇過程變得難以言喻的沉悶。
斯式晚年找到的解決途徑是“自我出發”,亦即用演員自己作為一個生命體,以此出發來體驗角色。然而這種解決方案在越來越激進化的戲劇實驗中是行不通的。
其實還沒有等到“文革”時期的徹底清算,早在1950年代后期,斯式表演體系就已經顯示出不能適應激進化的需要,于是戲曲表演的優點就浮現出來:手法簡潔有效鮮明生動,不需要搞繁瑣的對話和交代,就可以直接進行情緒召喚。話劇反而在這場競爭中敗下陣來。
于是戲曲現代戲崛起,用戲曲的手段服務于表意,迅速接替了話劇不太能勝任的角色。“文革”時期所謂“樣板戲”的“革命現代京劇”,都是在十七年時期就已經成形。像《紅燈記》原來是改編自電影的滬劇《革命自有后來人》,經過京劇和話劇的同時競爭,最后確立了京劇的形式;《沙家浜》原來也是滬劇《蘆蕩火種》;《杜鵑山》原來則是同名話劇;京劇《智取威虎山》也早在1958年就登上舞臺了;《白毛女》則更是成名已久的作品。
最終以戲曲形式沉淀下來的“樣板戲”,是這一場先鋒文藝實驗的頂峰。它在內容復雜性被最大縮減的同時,達到了形式的完美,即便在今天,還是能給觀眾帶來先鋒藝術的震撼。現在不少學者認為“樣板戲”的戲曲藝術可以與其精神內容分開,這本身就是相當概念化的一種認識。根據這種認識,刻意地對樣板戲的表意進行剝離,勢必是吃力不討好的。比如,近年有一部《白毛女》的改編作品《仙姑廟傳奇》,把八路軍這條線完全刪去,結果在臺灣演出失敗。臺灣學者、戲劇家王安祁見證了這一事件,并評論說“幾乎沒戲可演,原本靠革命激情撐起來的戲,一旦去掉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政治主題,就只剩裝神弄鬼了”。[3]
總結
今天,十七年戲劇的真正價值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關鍵在于如何從十七年戲劇的遺產中汲取經驗,讓戲劇的“大我”真正實現人的社群性存在與人的個體性存在的二維統一。我們今天許多戲之所以缺乏足夠的感染力,跟缺乏“大我”氣質是有關的。即便是時下一些號稱“打工戲劇”、“農民戲劇”的戲,也常常由于彌漫著跟普通戲劇一樣的“小我”的氣息,從戲的內容到戲的創作主體,不能脫離個人主義的局限,因而不能實現尖銳的表達力。在這個時候,重新檢視十七年戲劇留給我們的先鋒實驗,正為有益。
注釋
[1]參見張炯主編:《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178頁。
[2][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自我修養》,鄭林陵等譯,鄭雪來校,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3]王安祁:《刪去了八路軍之后——評京劇<白毛女>改編本<仙姑廟傳奇>》,《中國京劇》,2001年第2期。
鄧菡彬:上海戲劇學院
欄目策劃、責任編輯: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