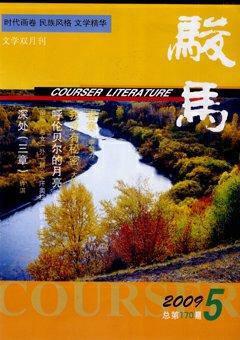隱秘家事
張殿權
一
是的,我是成年人了,不能像中學生那樣容易激動了,也不能像倔強的小孩子那樣任性了,更不能不計后果地做事了。
可是,心理學博士,我、我、我不是故意的。不不不,應該說“我沒有惡意”。您想想,她是我的親母親,我怎么可能有惡意,或是故意的呢?
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說的是不是有些亂?是的,我得承認,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幾天了,但是我心里依然很亂。請給我兩分鐘時間靜一靜,成嗎?……
心緒平靜一點兒,也許我才能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一點兒,當然,也更客觀一點兒。
是的,我要客觀地說。
二
噢,我還沒有告訴你,我叫張木,今年三十二歲,家住幸福西路周莊新區。對對,已婚,暫時還沒要孩子。
從哪里開始說呢?……
好好,我就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吧。
……
就從那天晚上說吧。
那天是八月二十號,星期三。眾所周知,當時北京奧運會賽程已經過了大半。當晚的《新聞聯播》報道,咱們中國已經獲得了四十五枚金牌,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并且還有多個奪金機會。國內外很多媒體和人士都預測,本屆奧運會中國將獲得金牌榜第一名。雖然我沒有奧運情結,或者也可以說我不是一個體育迷,我甚至對一些體育項目——比如馬術、壘球、棒球、射擊等感到莫名其妙,很不以為然。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市培養出來的體操運動員鄧琳琳獲得女子體操團體金牌,讓我還是為精彩的奧運賽事激動不已。——我說的可能有點兒遠了,但這并不是廢話。我的意思是說,那天晚上,起初氣氛還是很正常的,我也是很愉快的,父母也都是很愉快的。
誰也沒料到,會突然發生這件事。
《新聞聯播》快結束時,飯菜做好,端上了桌。小弟張力出去和同學喝酒去了,弟媳婦康園是公交車駕駛員,晚上八點半才下班,他們倆都不在。只有我和愛人謝佳、父母四個人吃飯。菜是豆芽、茄子,還有一個蒸菜。事實上,由于中午一點鐘就吃了飯,這時我和謝佳都很餓了,已先盛了一碗豇豆稀飯喝了。謝佳喝完豇豆稀飯,不喝了。我去盛第二碗時,她碰了我一下,輕聲說了一句什么,但我沒聽見。
我們邊看電視,邊正式吃起飯來。我還和父母熱絡地說起剛才《新聞聯播》里播出的男女蹦床決賽的賽況。我們之所以對此感興趣,并不是因為這個項目的男女冠軍都是咱們中國運動員,而是因為我們感到少見多怪。
謝佳的飯量不大,又吃了半塊饃和一點兒菜,就飽了。這時,母親起身去廚房拿什么了;父親雖然手里的筷子去夾菜,但眼睛仍盯著電視機看,半途中菜就掉到飯桌上了,筷子移到嘴邊時仍是空的。趁這個時候,謝佳用筷子指了指桌邊的幾個比米粒小一點兒、白色的什么東西,輕聲說:“你看,小蟲——”
我愣了下,看過去,抬起頭,不解地問:“什么?”
她說:“我從碗里扒出來的……”
我突然大倒胃口,但又不太相信,因為剛才我喝的那碗稀飯,雖然發現了幾顆蟲蛀的豇豆,但并沒發現有小蟲。我攪了攪碗里的豇豆稀飯,依然沒發現有小蟲。我害怕弄錯了,就定睛看桌邊的三個比米粒小一點兒、白色的東西,看了好一會兒才確認無疑:是小蟲——可能是豇豆或米里生的。
這時,母親從廚房里轉回來了。我突然就怒火中燒。因為,這不是第一次了!從我記事起,米或豇豆之類的糧食里生了蟲子,父母都是舍不得扔,簡單曬曬、簸簸或揀揀后照樣用來煮飯。現在,飯里居然又出現了小蟲!我不但覺得惡心,還突然覺得受了一種巨大的侮辱。
我想壓抑著憤怒,好聲好氣地向母親指出這一“重大”問題,可話說出口,發覺自己還是沒壓住。我指著桌上的小蟲,責問似的對母親說:“來來來,您看看這是什么?”
母親驚了一下,瞪了我一眼,掃了眼桌子,因為她是坐在對面,眼力也不大好,蟲又極小,就沒看見什么,沒好氣地問:“啥?”
“啥?蟲,稀飯里的!”我越想越覺得氣惱,“您看看您,天天做的都是什么飯?!”
母親也突然火了,說:“啥飯?好飯!你不想吃你就不吃!天天就你事多!啥活都不干就坐著等吃還挑三揀四的!”
現在想來,我是不對,不應當和母親這樣說話。這不但不敬,也不孝啊!可是,心理學博士先生,母親這樣說話,是不是也有點兒蠻不講理?假如她當時不說話了,或者說句適當的話——我不是說要她認錯,我的意思是她隨便嗚嚕一句什么也行,我就不會再說什么了,畢竟,她是生我養我的母親啊!
我并不是想吃山珍海味,也不是在雞蛋里挑骨頭,我只是想喝稀飯的時候碗里沒有蟲子。這,有錯嗎?
可是,母親說出這種不講道理的話,激惱了我。我大聲說:“好飯?您就天天做這樣的好飯?”
她立即就和我對峙起來,狠狠地瞪我:“咋了?蟲是我故意放進鍋里的,你能咋著我吧?!”
這是什么話!
我突然把筷子和手里的饃往飯桌上一扔,說:“不吃了!”
謝佳拉拽我,說:“你干什么你?”
性格沉默寡言慣了的父親看著,一直沒接話。
母親就大聲說:“你不吃,是個‘熊景!有本事,你天天下飯店吃去!”
我怒不可遏,立即就起身,走到門口拉開門,大聲叫謝佳:“走,以后不和她一個鍋吃飯了!”
母親抓起我扔在桌上的筷子,就摔到了地上,氣急敗壞地說:“你摔啥摔?你摔給誰看?”
我不想再搭理她,叫謝佳:“走!”
謝佳拿了她的包和傘,就跟了出來,說:“爸、媽,我走了。”
父親和母親都沒回話,我們帶上門就下了樓。
出了樓道,外面又下起了雨。我和小弟、父母同住在這個小區里,母親是三號樓,小弟在四號樓,我在五號樓。撐開傘,我們兩分鐘就到了我們的房子處。
進了屋,這時謝佳才告訴我:“今天晚上的稀飯,是咱爸做的。咱媽到咱大哥那去看小哲(大哥的三歲兒子)了,你回來時咱媽也才回來,你對她發火,她當然不高興了。”
我一驚:我錯怪了母親?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說:“她就是這樣的人,即便飯是她做的,她也照樣會這樣振振有詞!她就認為,無論她對不對她都是對的,當兒子的沒有資格說她一句!她根本不講道理!如果她像咱爸那樣,不說話,這事不也就過去了嗎?”
謝佳也很生氣,不能理解,眼睛忽然就濕了,哽咽地說:“我從小長這么大,結婚前在家時,還沒吃過有蟲的飯呢。其實,前幾天康園就跟我說了,那天她休息在咱媽那,就發現黑米和豇豆都生蟲了。就算您不舍得扔,也得把蟲處理掉吧?如果不是怕咱媽生氣,我當時就把稀飯倒掉不喝了。我是強忍著把蟲挑出來,喝完那碗稀飯的!”
謝佳覺得很委屈。
說實話,心理學博士先生,雖然我是母親的親兒子,但是我的委屈感并不比謝佳少。想一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即便是在偏僻的鄉村,還有幾個人會吃有蟲的飯,更別說是在城市了!母親這一輩人,經歷過六零年以至八十年代初的一段饑餓年代,他們珍惜糧食,生蟲的糧食也舍不得扔,我可以理解。可是,您得想一想吧,現在,您不覺得吃生蟲的糧食有什么,但孩子們是否愿意?事實上,我和謝佳也并不是那種苛刻的人,我們也不是說生幾個蟲子的糧食就絕對一口不能吃,但是,至少在做飯前,要先把蟲子徹底地清理出來吧?當然,他們也許清理過,只是后來又新生了蟲子。
可是,我把這個問題說出來難道就不對嗎?我就應該默默地吃進肚子里去嗎?我不是找碴,我是想要他們明白,以后不能再出現這些問題了。假如我和謝佳自己開火吃飯了,某一天把他們二老請到我們那吃飯,由于粗心沒發現飯里有蟲,但他們突然發現了,心里會是什么想法、什么滋味?
三
在母親看來,我小時候吃的很多東西都不衛生,吃飯前也很少洗手,大便后沒衛生紙也用過土坷垃或樹葉擦屁股等等,我不照樣長這么大了嗎?我承認,這是事實。可現在不是小時候了!小時候我還穿開襠褲呢,現在還能穿嗎?
結婚前,我就因糧食生蟲還用來做飯和母親爭吵過。但那時,過兩天也就過去了。可是這一次卻讓我忐忑不安,心里又壓抑又難受。
坦率地講,相對于婚前,這兩年我在發現母親做得不對時,表現得壓抑多了,無關大礙的事我就忍著不說,即便是說,也盡量用柔和、客氣的尊重方式。然而,脾氣火暴的母親不但從來不接受,之后也幾乎全都拒絕改正。比如,她的房間擺弄得十分雜亂,我就勸說:“媽,您看,以前住平房時家里弄得亂亂的,那時是因為您常出去干活掙錢,沒時間收拾。可現在住樓房了,爸也退休了,您天天也沒啥事了,您們把家里收拾得干凈利索一點兒,不好嗎?”
母親立馬就瞪我一眼,說:“我不能!我的事,你還管得著了?我亂我得勁兒,我又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你憑啥管我?”
父親在外縣一個水泥廠工作了一輩子,前幾年才退休回來,一直是一個勤快的人,干什么活都不講價錢。以前,他每次回來,都會把雜亂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條,可是退休回來后,在母親的“熏陶”下,竟也適應和習慣了這種雜亂,也很少收拾了。大哥和小弟也都說過讓他們有空把家收拾得利索一點兒,來了客人也好看一些。可是,誰說的他們都不聽。我們也就再不說了。
可是,牽涉我們的事,他們也是這種態度,讓人實在難以接受。比如,他們洗芹菜、白菜等時,根子不擇掉或葉子不掰開就洗。他們自以為洗干凈了,可實際上依然夾雜著土。因此,我們在家時,就搶過來洗。比如,洗油膩的碗碟筷,他們就是不用(或很少用)洗潔精,只用水沖洗,洗過的碗碟筷依然油膩,有時幾根筷子還粘在一塊。因此,只要我們在家,就是謝佳或康園洗。
有時候,吃到因夾雜有土而滯牙的菜,或抽出筷子發現是粘連在一起的,我也就忍著不吭聲了,心想:我不說惹您生氣的話了,反正再過一年或兩年,我們有了孩子,就不跟您在一塊兒吃飯了!
……
我們——包括小弟和康園,為什么結婚兩年了依然和父母合鍋吃飯?
怎么說呢?……
從客觀上說,這對我們都有好處。我們這兒原來是城鄉接合部,幾年前因房地產開發,大半個村進行了拆遷,集資建起了這個有五幢樓的新小區。二零零六年初樓建好后,我和小弟相隔六個月先后結了婚。我、小弟和父母各有一套房子。本來,我們是可以順其自然單開火吃飯的,可是,我工作的單位距家較遠,因此中午都不回家吃飯。謝佳在一家大型家電批發公司工作,中午有時回家吃,但有時也不回。小弟張力是一個出租車司機——給別人開,開的是白班;康園呢,是公交車駕駛員,他們倆中午都不回家吃飯,因為經常下班晚,康園晚上也多是在外面吃或回家后自己做點兒吃。因此,如果我們都分開吃,不但做飯麻煩,而且很浪費。在一起吃,既節約,又能吃得好一些。
小弟只是初中畢業,混了幾年才開始給人跑出租車,給私人跑出租車不是“正式”工作,每天也很辛苦;康園也是初中畢業,老家在農村,在公交公司買的工,起初是售票員,因為公司人員臃腫,工資很低。前兩年公交車改無人售票,康園轉崗學駕駛,無恥的公交公司一年多都不給他們這些人發工資,連生活費都沒有。因此,他們倆沒攢下什么錢,結婚和裝修房子時還借了一萬多塊錢的賬。而大哥接了母親的煙廠“地代工”工作,工資高,一家人生活上沒問題;我上了大學,和謝佳的工資收入也不錯。因此,母親內心里一直都覺得她和父親虧欠小弟的,想多幫他一些,加之小弟晚上常去和同學朋友喝酒,母親就不要他給生活費。不過,小弟和康園卻時常買菜回家。
但是,我和謝佳從結婚后的第一個月,就開始給父母生活費了。我和謝佳的單位福利還好,逢年過節會發一些油、米等,也都給他們。我們還時常買些水果、肉、蔬菜等回去。客觀地說,我們給父母的是多于我們吃的。
小弟和康園人都不錯,康園又是特別實誠的人,謝佳和她處得很好。他們不給父母生活費,我和謝佳都無所謂。
可是,不久我和謝佳卻發現,母親嘴里不說,可心里卻好像總是覺得我和謝佳工資都不低,應該多給她一些……
說到這兒,我忽然感到很難過。我親愛的母親,她知道這些年我是怎么過來的嗎?……對不起,心理學博士先生,我、我一想到這兒,就不好受。我為什么到了三十歲才結婚?是因為以前太窮呀!
十年前,就是一九九八年,我大學畢業。想必您也知道,當時全國大學生就業開始進行重大改革,不再包分配,實行所謂的“雙向選擇”。對于有錢有權的人,他們照樣可以給子女們安排進行政或事業單位工作,最差的也可以進一個好企業。可是,我們這些無權無錢的失地農民子弟,卻要自謀出路。
最初找工作的艱辛遭遇和感受,我就不說了。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進了一家效益不大好的國有企業辦公室工作。
雖然我憑自己的能力和人品贏得了同事和單位一把手的看重,可是這家企業因歷史遺留問題太大,一把手也無能為力,必須走破產這條路。因為工作的需要,也因為……因為我對外界的恐懼吧,加之單位一把手說破產結束后讓我和他一起到另一家企業干,我就一直待到了二零零四年十月單位破產終結。
這六年里,我從二十二歲變成二十八歲。這本來應該是一個享受青春和愛情的年齡,我卻是在煎熬、沮喪和恐懼中度過的。因為工資低,又沒有前途,我先后遇到過幾個女孩,可是因為窮,她們最終都選擇了分道揚鑣。那時候,我內心里是無比的凄涼,悲觀而絕望地覺得,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再擁有純真、美好的愛情了!
一個人只有一輩子,心理學博士先生,您能想象和體會到這種悲觀和絕望嗎?
父母雖然也為我著急,可是他們沒有能力幫助我!說句心里話,那時候我也怨過:為什么我是生在這樣一個無權無錢的家庭呀?老天爺太不公平了!
我就想:這是一個物競天擇的殘酷社會,誰都不可靠,最可靠的是你自己。只有自己成功了,別人才會高看你!
因為曾經的遭遇,后來我遇上了謝佳,一直都不敢把“愛”說出口。當時,她在一家書店做店員,工資也很低。后來,我們惺惺相惜,才開始談起戀愛來。
二零零四年,我們單位破產終結后,一把手沒能如愿到另一家企業任職,回了機關。這時,正巧有一家報社在招聘記者,我應聘上了。不久,謝佳也成功地應聘進了一家大型家電批發公司做職員。由此,我們的收入才開始改善,慢慢有了些錢。
二零零六年初,我們的安置樓建成,采用抓鬮兒方式分房。母親抓到的是四樓,小弟抓到的是五樓,我抓到的是頂層六樓。母親的房子小一點兒——九十八平方,我和小弟的房子戶型、面積相同,都是一百零五平方。三套房子加在一起的房款,與拆遷時的補償款大致相同,于是房款用的全是補償款,我和小弟都沒有掏錢。因此,小弟的房款比我的高了一萬元左右,但我和謝佳也沒有意見。
因為體諒到父母的不易,裝修房子時,我和謝佳沒讓父母出一分錢,甚至在父母幫我買裝修材料時,我還多給了他們一些“辛苦費”。小弟的房子裝修,也是他自己出的錢。房子裝修好后,我就結婚了。半年后,小弟也結婚了。
同樣是因為體諒到父母的不易,我和謝佳結婚也沒有讓父母出錢。謝佳嫁到我們家,母親僅僅給了她兩千塊錢。而后來,康園告訴謝佳,她和小弟結婚時,母親給了她六千塊錢。謝佳心里雖然有點兒不平衡,但是,我和謝佳也都沒怎么往心里去。
同樣是因為體諒到父母的不易,我和謝佳結婚后的第一個月,就開始給父母生活費了。
四
結婚前,母親對康園和謝佳都非常好。她倆每次來,母親都滿臉高興地張羅出一桌好菜。可是,我和謝佳結婚過后,她就“變”了。
起初,最糟糕、最突出的就是“早飯問題”。
因為母親做飯時常把不住量,或因我和小弟在外喝酒沒回來吃飯,晚上經常會剩稀飯和菜。第二天,母親就把剩稀飯和剩菜熱一熱,餾幾塊饃,當作早餐。但是,剩稀飯本來量就少,熱后還會起一層粘皮。沒有剩飯的早晨,母親也只是煮一點兒白米稀飯,或熱剩菜或干脆就只有醬豆、蒜瓣。因此,我就不吃,可是吃慣了早飯的謝佳卻覺得委屈:這能算飯嗎?
說句心里話,結婚前我就對此不滿,只有不吃。可是現在,母親怎么能還這樣呢?
于是,某一天趁母親高興的時候,我就對她說:“媽,您看,早飯能不能別天天熱剩稀飯、剩菜了?”我沒有說謝佳,但我以為母親聽了這句話會明白,即便是她不立即表態,之后也應該知道該怎么做。
可是,她卻掃了我一眼,帶氣地說:“你想吃就吃,你不想吃就不吃!事怪多哩!”
我很生氣,但是我咬著牙忍住了,沒再接話。
直到今天,我也沒和謝佳說過這事。
幾天后,我就對謝佳說:“天天早上到咱媽那兒吃飯,太耽誤時間,也不方便,不如,咱買點兒豆奶、面包什么的,早飯就在家吃吧,這樣省事。”
謝佳當即同意。
不久,我們又買了電飯煲,每天晚上把黑米、花生、豇豆或紅棗等淘洗好放進去,定好時。第二天一早,飯就煮熟了,洗漱后就可以吃了。
可是,我們依然每月給父母生活費。因為我每個月差不多有近一半的晚上都在外面吃飯,父母可能覺到我們給她的生活費明顯有些多,就說不用給那么多。于是,我和謝佳就每隔一個月少給她一百塊錢。
然而,慢慢地,我和謝佳卻發現,母親雖然嘴上不說,可卻嫌我們給的生活費太少似的,常常沉著臉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謝佳就有些生氣,對我說:“咱們給咱媽的少嗎?咱們一個月才在她那吃多少東西?張力和康園不給她一分錢,她怎么不嫌?”
我因為事多,整天忙,就想:反正我們給您的錢和東西,與我們吃的相比,足夠了。于是,也沒往心里去。
后來,母親就時常在我們都在,或我不在、謝佳和康園在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說,她做了一輩子飯了,現在還天天做飯,都做煩了!她想沒事去附近的街邊公園里遛遛,啥時候想吃飯了啥時候做。
起初我們都沒太在意,她說得多了,我們才咂摸到一些什么。
私下里,康園就和謝佳說:“咱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嫌咱們天天和她在一塊吃飯,要做的飯多,嫌累?”
謝佳說:“也有可能是。可是,咱們在家時,哪次不幫著做飯、刷鍋、洗碗的?她天天又沒有其它什么事,累什么呢?”
回到家,謝佳對我說了她和康園的看法。
我說:“別管她。她現在天天在家沒事,身體好好的,她不做飯叫我們做?”
心理學博士先生,說句不敬的話,當時我就覺得母親有點兒身在福中不知福。您想一想,兒女們結婚了,很多父母想讓他們和自己一塊吃都不能呢,現在母親卻煩起來了,她煩什么?何況我們又不是白吃她的!
這樣過了大半年,已是第二年春天了。一個星期六的中午,我正好沒事,在家吃午飯。謝佳吃完飯去上班了,我就把下個月的生活費遞給母親。
沒料到,母親突然說:“……以后,要不,你們自己做著吃吧,我們給你買一個新煤氣罐,灌滿氣。”
我心里一下子很難受:我們天天忙得要命,哪有時間自己做著吃?我就說:“過過再說吧。”
但是,這事我沒有和謝佳說。否則,謝佳一定會認為,母親是有意“攆”我們!
我以為我的回答,母親應該是理解的。可是,又過了兩個月,我再給她生活費時,她又提出讓我們自己做著吃。我也沒有同意。可是,出了門,我感到十分難過和氣憤:作為母親,您主動提這事,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為我平時不關心米面油鹽醋,當時不知道這些日常生活物資,已經大幅度漲價了。幾天后,我看到包括我們報紙在內的全國眾多媒體大量報道物價問題時,才意識到:母親是不是嫌我們給的生活費太少了?
我就悄悄算了算賬,但是結果顯示:我和謝佳給母親的生活費及平時買的肉菜等加在一起,彌補我和謝佳的花費后,仍有剩余。
那么,母親為什么會“不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來,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喝過酒后回家的路上,才突然想明白:母親是把家里一個月吃喝的所有費用,都平攤到了我和謝佳的頭上。可是,早飯我們并不在她那兒吃,午飯謝佳有時回來吃有時也并不回來吃,憑什么把總花費都平攤?!
母親為什么要這樣對我?她對小弟好,我和謝佳都沒有意見,都理解,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們給她的生活費已足夠了,她為什么還想要我們多給?
想到這,我難過極了。下了公交車,我的眼淚差一點兒就涌了出來……
母親啊,我不是不孝順您!是您太不理解我們了呀!我們為什么不大手大腳給您錢?是因為我和謝佳不是貪官富商也不是地主老財,手里雖然有點兒錢,可在這個社會里,依然是底層老百姓啊!我們將來會有小孩,吃、穿、用和教育等等將會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我們不攢點兒錢將來怎么辦?我所在的單位沒有編制,稍有失誤或惹領導不高興,就有可能被趕走。而謝佳,懷孕后將不能再從事現在需要操作電腦、工資較高的崗位了,生過小孩后也可能不會再轉回這個崗位了,因此她在努力學習,爭取將會計師資格證考到手,之后再要孩子,以便將來能轉到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都還好的會計崗位。我們的壓力多大,您不知道呀?再則,將來您和父親也會老,會需要錢,我們現在多攢點兒錢,那時候就可以多給您一些呀!
母親您老人家,能不能理解我們呀!
五
對不起,心理學博士先生,我的確又有些激動了,對不起,實在對不起。
……
您問我,父母都有哪些收入?……讓我想一想……
父母的收入,的確、的確是不高。可是,仔細想來,和這個城市的消費水平比較,他們也并不怎么捉襟見肘。現在,父親一個月的退休工資,大概八九百塊錢吧;在火車站附近一條偏僻的小巷里,我們家還有一間房子,每個月有近百元的房租;逢年過節,我們村集體也會分一些集體財產增值收入,一年一個人有幾百塊錢吧;偶爾,父親給人干點兒雜活,也有一點兒收入。應該說,刨掉日常開支,他們每個月還是有幾百塊錢結余的。這雖然不多,但現在國家政策好了,父親有退休職工醫療保險,母親也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應該說,在這個莊上,父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屬于中等偏上的,基本上是沒有什么后顧之憂的。在這個莊上,絕大部分和他們年齡相當的人,都沒有退休金,只靠每月一百多塊錢的“低保”和其它偶然性收入維持生活,有的甚至還要去干重體力活掙錢。
因此,我一直都認為,他們應該是能把日子過得更好的:自己生活愉快,身體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
可是,心理學博士先生,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向著這個方向去做或者說去努力。相反,母親還“愛上”了“亂花錢”。
我和小弟結婚后,父母的壓力大為減輕,心寬體胖起來。這時,各種打著“免費送藥”、“免費健康講座”、“免費體檢”幌子,實為高價賣藥(甚至是假藥)的活動,在這個城市里再度泛濫。可是,本市工商部門卻置若罔聞。
去年,也是就是二零零七年某一天,母親也參加了一次這樣的“免費體檢”,沒想到,一下子查出了高血壓、高血脂等多種毛病,母親感到異常害怕。我提醒母親說:“這些人,都是騙子。你不要跟著去啊!”
母親很不高興,說:“人家不要錢。”
此后,母親早晨開始遛彎鍛煉身體了,同時,依然偷偷去參加所謂的“免費健康講座”,被人忽悠住了,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幾袋從沒聽說過的“神秘”中藥和藏藥,泡茶或泡酒飲用。
可能是母親怕我說難聽的話,并“不敢”和我和謝佳說這些事,但卻都對康園和小弟說了。康園又私下和謝佳說了,謝佳又告訴了我,說:“你別說她啊,她相信那些東西能治病,對她有好處。你說她,她又不高興!”
可是,我還是沒忍住。
那天吃飯,我看見她和父親各倒了一杯藥酒飲用,我就忍不住說:“你真有錢啊,一千多塊錢就買了那一點兒東西。你可知道,他們這些東西最多只值一百塊錢,你被騙了!”我還把報紙上登的一些揭秘騙術的文章拿給她看,說:“很多報紙都登了!”
她立即就不高興了,拉下臉,說:“你別管!我花的是我的錢,我為了自己的健康,想咋樣咋樣,又沒花你的錢,你還管得著了!”
我被駁得啞口無言。好像我想阻止她健康似的!謝佳還拉我的衣服,不讓我再說了。
小弟也忍不住說她:“您是真上當受騙了。騙子就是利用你們的善良、期盼健康、分辨能力差和喜歡占小便宜的特點,騙你們這樣年齡大的人的錢!”
母親瞪著眼睛,把數落我的話又砸向了他。
我們無可奈何,只有苦笑,說:“好,好,我們不管您。”
母親仍一意孤行,之后又花了不少錢買這補藥那補藥,還有“健康枕”、“降壓手鐲”什么的……她不但買這些東西,有時還流露出她買這些東西我們應該給她掏錢的意思。我和謝佳、小弟和康園都裝作糊涂,不搭理她。
母親年齡大了,害怕得病,我們都理解。可是,她怎么就不明白日常飲食衛生和良好的生活習慣對健康的重要性呢?
后來,她又說誰誰老兩口的兒子和閨女經常給他們錢,他們天天過得跟神仙一樣快樂。又說誰誰的兒子娶的媳婦家里多有錢,陪送了多少多少東西、多少多少錢……
后面一句話,讓謝佳和康園十分不高興,她們倆私下里聊天時,都不滿地說:“你看咱媽,這話怎么說出口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不知是不是她從其它渠道也證實了她買那些東西確實是被騙了,心里很難受,但又不敢跟我們說。之后,好像是要把花出去的這些冤枉錢“省”回來似的,不但很少買葷菜了,甚至連青菜也減少了。因為我經常在外面吃飯,對此沒覺得有什么。可是,謝佳心里卻很不快埋怨說:“這天天吃的都是什么呀!”
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母親越來越顯出“俗氣”和“市儈”來。心理學博士先生,我這樣說,是不是大不敬?可是,不用這兩個詞,用什么詞呢?……
因為,此后,一個月三十天,哪天給她買東西——或肉菜或水果或其它什么,她就會表現得很高興,一家人顯得特別和睦、溫馨。而第二天沒買東西回來,她就沉著臉,很不高興的樣子。
不光是我和謝佳發現了這一點,康園也發現了這一點。因此,如果康園趕休息在母親那兒吃飯,就會買兩樣像樣的菜加餐。而很多時候,她也不愿去母親那吃飯了。為了讓母親的臉色好看一點兒,也為了能吃得好一點兒,謝佳比以前更多地買肉回來。
可是,我們晚上在母親那兒吃飯要比康園多,怎么可能每天都買東西給她?謝佳一進門,看見母親沉著臉,就不好受,后來就和我說:“不如,咱們自己吃吧?”
說心里話,我很看不慣母親總是沉著臉的樣子,這使整個家庭的氣氛很壓抑,而一個家庭是這種氣氛,早晚都會出問題!因此,在內心里,我也是不想和母親再合鍋吃飯了。可是,因為此前我說過的原因,同時,因為我不喜歡吃街上賣的堿面很大的機器饃,喜歡母親用酵子蒸的發面饃,就說過過再說吧。
讓我們——包括小弟和康園不能理解的還有:在這個家里,母親是“戶主”,父親好像只是她的“隨從”。有時候,母親會毫無道理地指責父親這不是那不對,說刺耳難聽的話,一貫老實、溫順的父親也不辯白……雖然母親本質上沒有惡意,但是一看到母親對父親無理指責,我和小弟就都會反感,忍不住說母親兩句。母親自知理虧,有時候就不說了,可有時候她依然會毫無道理地把我和小弟訓斥一通。
謝佳和康園也看不慣母親“訓”父親,她們倆說:“咱爸在外地辛苦工作了這么多年,回到家來該好好歇歇了,可是咱媽卻經常這樣給他氣受。咱媽怎么就不明白,如果不是咱爸的退休金,她怎么能過上現在這樣安逸的日子?村子里大營他媽只比母親小幾歲,腿還摔斷過,留下了后遺癥,一走一瘸的,可是兒女們不爭氣,她和老伴不照樣每天從早到晚去蹬三輪掙錢吃飯嗎,咱媽有啥‘資格沒事就‘訓咱爸?”
事實上,還有很多事讓我們都不能理解母親。比如,今年會計師資格考試時間原定于五月十六日,因為舉世震驚的汶川大地震突然發生,被迫延期到九月六日。謝佳想利用這多出來的難得時間,每晚多學一點兒,爭取能一舉考過關。同時,小弟張力每天中午十二點在外面就吃飯了,六點多回來已很餓。可是,母親每天都到我們下班回來后,才開始做晚飯,吃完飯時已八點多了,回到家再洗洗澡收拾收拾,就很晚了。我和小弟都建議母親晚飯早點兒做,可她置之不理,說:“我就不早做。”依然我行我素。
因此,在我和母親發生這次沖突前,謝佳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有時下班后在街上隨便吃點兒東西,就回家學習了。
還有,八月八號那天,因為晚上八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就要開始,中午我和母親、父親三人在家吃飯時,我就笑對母親說:“媽,晚飯做早點,好看奧運開幕式。”
可是,她卻用一貫的輕蔑目光斜了我一眼,說:“誰做早點?要做早,你自己做去。”
心理學博士先生,如果換成是您,聽到這種話,您會高興嗎?但是,我都忍在了心里,笑說:“好好,您不做就算了。那,晚上我們就在家自己做點兒吃了。”
母親又乜斜了我一眼,說:“你想干啥你干啥。”
……
明明,母親是可以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兒的,自己生活愉快,身體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可為什么她硬要往不開心、不高興的方向過?這是為什么?
作為兒女,尊重、孝敬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的!是必須的!可是,無論是兒女們,還是父母們,做任何事都應該有一個原則:那就是要講道理。
講道理行遍天下,沒道理寸步難行。
……
您說的對,我也明白:父母不是神,父母也是有缺點的人。他們不能任何事做得都對,無論他們年齡有多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做兒女的,應該尊重、理解、寬容他們……
……
您說什么?……哦,您問母親為什么會這樣?……讓我想想……
母親的本質當然是善良的,對我們當然是沒有惡意的。比如,她對小弟的同情,想多給他一些東西;比如,她曾和大嫂鬧過很多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怨大嫂有的怨她,但現在她不照樣天天樂顛顛看護大哥的兒子小哲……當然,從內心里說,她肯定也是愛我和謝佳的。
她為什么會——會有現在的這些問題呢?我想,第一,她一直以來就是一個脾氣不大好的人。從我六七歲記事起,這二十多年中,她都是這樣,恐怕再也改不了了。所以,她會說那些難聽的話。有時候,我也想過,我的性格不好,是不是也是她的遺傳?第二,這可能與她的生活習慣有關。她幾十年來都是這樣過的,要改變很難。從小到大,以至前幾年,母親都是在貧困中掙扎,吃過很多苦受過很多罪,只是這幾年生活的壓力才真正減輕下來,可是現在,她卻不再年輕、不再強壯,漸漸步入老年了。她內心里渴望過上更富裕的好生活,但是想過上十分優裕的生活,卻又不太可能,因為現實狀況在這兒擺著呢。
但是,母親如果認真想一想:事實上,她的日子雖然不是非常富足,但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因此,她完全可以放下心結,好好地過日子,過好日子,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家庭和睦。
其實,我和母親的這次爭吵,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我和母親發生過比這更厲害的爭吵,不久不也煙消云散了嗎?我稍微彎彎腰,來到她面前,賠著笑臉對她說上一句:“您看,您老人家還跟我一般見識嗎?”這事,也就過去了。
可是,我為什么沒有這么做?因為我懷疑:我這么做了,有什么意義?以后她會改嗎?她不會,她仍會是這個性格和態度。
這幾天,我的內心一直都惴惴不安著,感到很壓抑。因為,這一次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沒結婚,怎么說都無所謂;可如今,我已結婚兩年了,我這樣做,可能傷了母親的心,更傷了父親的心。
心理學博士先生,和您說半天話了,我一直都沒怎么提過父親。父親從小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也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不愿意與人發生矛盾,更不愿意看到家庭發生矛盾。因此,在這個矛盾過程中,他始終都是沉默的,他不知道該說什么、做什么。他在外地工作了幾十年,退休回來后,內心里渴望一家人能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因此對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一直都是懷著包容之心。因此,在這件事中,父親一直都沒有說什么。我深深地感到對不起父親。
我的內心感到很壓抑,還因為,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二年,我喜歡母親用酵子蒸的發面饃。可是今后,我只能吃街上賣的、堿面很大味道很差的機器饃了,因為我和謝佳都不會蒸發面饃。
當然,還因為當天晚上發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我和謝佳回到自己房子時,雨下得更大了。等我們洗好澡后,又打起了駭人的巨大閃電和驚雷。因為害怕雷擊,我們關嚴了窗子,關上了電視,只開了一盞臺燈和風扇。可是,一個很亮的閃電后,接著一個巨大的雷聲炸響,臺燈和風扇隨之就滅了、停了,房間里一下子黑了下來……當時我害怕地想:是不是老天爺看見了我和母親爭吵,這是在警告或者懲罰我呢?
想起這三十二年在母親臂膀下的生活,我的眼淚迅速就涌了出來。我對謝佳說:“咱們,虧待咱媽咱爸了嗎?我覺得沒有!她老人家怎么就不明白,咱們不和她合鍋吃飯了,她還能像現在這樣,經常吃到這么多好吃、價高的瓜果和其它食品嗎?她自己舍得買嗎?看著吧,兩個月后,她內心里就會后悔的。”
謝佳握著我的手,說:“好了,別難過了。夏天下雨打雷,是正常的自然現象。咱媽也不會太計較的,最多難過幾天就沒事了,畢竟咱們是她的孩子。何況,咱們也沒什么大錯……”
六
八月二十四日。
傍晚下班后,張木坐公交車回家。他到了家,開了門,換了拖鞋,走進書房。這時,謝佳下班還沒到家。
書房的桌子上,放著一本厚厚的心理學書籍。書旁邊是一摞三十一頁的稿紙,每一頁稿紙上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第一頁稿紙上面有一個標題:《向一個虛擬的心理學博士說說隱秘家事》。
張木將稿紙收攏起來,放進了左側書柜里。忽然,他眼前掠過一桶油:剛才進門時,他不經意地向餐廳看了一眼,餐廳的餐桌一條腿旁邊好像有一桶食用油……
他忙折身出去,步到餐廳,看見餐桌下果然有一大桶食用油,提手處夾著一張紙,紙里夾著錢,餐桌上還有幾個發面饃。張木把紙和錢取下來,錢是三百整。展開紙,上面是父親手寫的字:“小木、小佳:給你們拎一桶油,另外拿上三百塊錢,需要什么就買些什么吧。”
父母那有一把他們房子的鑰匙。是父親或父母兩人一起,趁他和謝佳上班時,把油、錢和發面饃送來的!
張木的眼淚迅速就滾落了下來。母親啊,我是尊重您的呀,我也是孝敬您的呀,我只是覺得,我們的生活應該能過得更好一些的呀!我們應該多理解您,也想您能多理解我們一些呀!母親啊,我多么想吃您蒸的發面饃呀,想吃一輩子呀!
(責任編輯 晉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