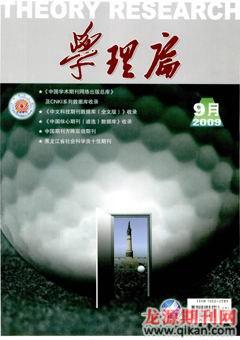以賽亞·伯林對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認識
柳 敏
摘 要:以賽亞·伯林是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在歐美政治哲學界享有大師級的盛譽。作為一名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他對蘇聯(lián)的文學藝術進行了深入批判,認為蘇聯(lián)時期的文學藝術與俄國傳統(tǒng)文學藝術相比是整體退步的、僵化的。
關鍵詞:以賽亞·伯林;蘇聯(lián);文學藝術
中圖分類號:I106.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3-0094-02
以賽亞·伯林是西方自由主義者中一位獨特的思想家,其思想根基扎根于對現(xiàn)實社會、政治的直觀認識中,其一生經(jīng)歷也就是他的思想之路。伯林曾先后三次到達蘇聯(lián),親眼目睹了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發(fā)展狀況,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更是在他的思想史研究中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
1945年9月,伯林以英國外交官的身份飛抵莫斯科。到達蘇聯(lián)之后,他對當時蘇聯(lián)的文藝狀況產生了極大興趣,會見了當時一些有名的蘇聯(lián)作家,其中與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的會談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伯林傳》中寫道,“他始終堅信對阿赫瑪托娃的訪問是他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離開俄國的時候,心中滿懷對蘇聯(lián)專制的憎惡之情,這種憎惡幾乎在他后來為捍衛(wèi)西方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而寫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間都可以看到”。[1]1956年,伯林偕同其新婚妻子艾琳再次造訪莫斯科。1988年,年近80歲高齡的伯林故地重游,最后一次穿過列寧格勒雨中的街道,經(jīng)過噴泉屋和阿赫瑪托娃的公寓。伯林前兩次訪蘇都留下了很多他的所見所聞以及和蘇聯(lián)作家的談話錄,記錄了當時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狀況及當時蘇聯(lián)作家的生活狀況,而最后一次訪問主要是一種“道別式”的訪問,筆者未發(fā)現(xiàn)他留下任何關于此次訪問的紀錄。
伯林對傳統(tǒng)俄國的文學及藝術有很高的評價,特別是19世紀的俄國文學與藝術。他在看待蘇聯(lián)時期的文藝時,必然與傳統(tǒng)俄國的文藝作比較。在他看來,蘇聯(lián)時期的文藝整體上是退步的,或者是停滯不前的,蘇聯(lián)時期能為人稱道的文學和藝術作品都是傳統(tǒng)俄國時期的遺留,或者是其傳統(tǒng)的延續(xù),而鮮有創(chuàng)新的東西出現(xiàn)。當然,伯林對蘇聯(lián)文學和藝術狀況并非一概否定。他認為,在1937年之前,蘇聯(lián)文學藝術雖然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僵化的趨勢,但由于種種的因素仍然在緩慢的發(fā)展,但是在1937年之后,斯大林加強了對權力的控制,蘇聯(lián)的文學藝術陷入了完全停滯。5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政治社會生活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赫魯曉夫當政,公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解凍”思潮成了當時主流思想。
一、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緩慢發(fā)展(1917~1937年)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文學與藝術,是以相對于普希金時期的“黃金時代”的“白銀時代”而著稱于世的,它是整個俄羅斯文化遺產和世界文化寶庫中重要的一頁。伯林對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學藝術的發(fā)展是認可的,“達到了自古典時期的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理后的最高峰。”十月革命的爆發(fā)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是給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作增添了新的主題與素材;另一方面則是伴隨著革命而產生的激進主義、左傾思想對文藝的負面作用,因此開始了從俄羅斯文學藝術向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轉型過程。
伯林認為,十月革命對俄羅斯文藝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但是并沒有抑制俄羅斯文藝的持續(xù)發(fā)展。十月革命給俄羅斯文藝的發(fā)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但是,他并非把這種負面作用歸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歸因于國家層面的政府壓制,或者說他認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種國家政府行為,是國家政權壓制的結果。他指出,“嚴格的檢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和觀念,除了那些經(jīng)過仔細挑選出來的之外,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勵與政治無關的藝術形式(特別是一些價值不大的藝術形式,如關于戀愛、神話和偵探故事,還有各樣的小說和拙劣的文學作品),機械地把大眾閱讀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實驗性的作品上。”[2]伯林認為,蘇聯(lián)文學藝術之所以能夠繼續(xù)前行的原因在于:革命剛剛勝利,國家對政權的控制還較為寬松,各種派別活躍促進了文藝的持續(xù)發(fā)展。
伯林把1928年至1937年這一階段蘇聯(lián)文藝的發(fā)展看作是逐步停滯、僵化的過程。他把1928年對聯(lián)共(布)領導人之一的托洛茨基的清算作為蘇聯(lián)新的正統(tǒng)思想建立的標志,從這一刻起,國家開始控制了政治、經(jīng)濟及文化等所有領域。但同時伯林認為,蘇聯(lián)的文藝仍在緩慢的發(fā)展,一些優(yōu)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創(chuàng)作,表達著一種自由的氣息,雖然這種氣息是非常微弱的。天才的作家們在一定程度上盡可能地發(fā)揮了他們的獨創(chuàng)性,在不打破正統(tǒng)觀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處罰和判刑的條件下,傳達非正統(tǒng)的觀念”。[3]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伯林認為是當時政治局面混亂而導致的結果,“政治迫害發(fā)生了,所有的異端,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陸續(xù)被‘揭露出來,并對這些有罪的異端者進行了恐怖的迫害;但是在非常殘忍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中,由于哪一方可能被清算并不確定——這也給知識階層蒙上了一層陰影——在片面性和夸大性的影響下,導致的結果是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在這一時期十分豐富,繼續(xù)給蘇聯(lián)的思想和藝術帶來了騷動與動力。”[4]在各種派別的斗爭中,時而這一派別占據(jù)上風,時而那一派別占據(jù)上風,使得知識分子無法摸清政治走向,而繼續(xù)堅持自己的觀點進行文學與藝術的創(chuàng)作。
二、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艱難前行(1937~1945年)
1937—1938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階段,它徹底改變了蘇聯(lián)文學和藝術的景象。國家全面控制了文藝界。伯林認為,大清洗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對于每一位蘇聯(lián)的作家和藝術家就像圣巴托洛繆的前夜一樣——這是他們中的任何人都無法全部忘卻的”。文學與藝術作品的創(chuàng)作完全遵從官方的要求,成為了官方的宣傳工具,作家和藝術家對官方的委曲求全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一時期的文藝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1941年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再次改變了文學藝術領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學藝術都服務于衛(wèi)國戰(zhàn)爭。在這一背景下,出現(xiàn)了一些以戰(zhàn)爭、愛國主義為主題的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伯林認為,這些詩人的創(chuàng)作是不同于那些專為宣傳而作的官方作家的,他們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藝術價值,“最好的戰(zhàn)爭詩人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他們創(chuàng)作的源泉來自豐富的愛國情緒,但是這些藝術作品太具有藝術性而不能被認為是作為具有直接宣傳價值的作品,而且他們的作品還因其宣傳力度不夠而受到黨內的官方作家的輕度的反對。”[5]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一種自由的創(chuàng)作,而沒有完全受國家政策的導向,成為國家宣傳的工具。這一點正是伯林所認可與稱贊的。在伯林看來,文藝的創(chuàng)作必須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創(chuàng)作才能產生好的藝術作品。
衛(wèi)國戰(zhàn)爭結束之后,國家立刻加強了對文化的控制。一切手段都被利用來宣傳蘇聯(lián)經(jīng)濟和文化在“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天才領袖”的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突出成就。М·А·肖洛霍夫在1954年12月的第二屆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苦澀地說道:“一股毫無色彩的間接文學的黯淡潮流成了我們的災難,這股潮流在最近這些年間自雜志上涌出,充斥著圖書市場。”[6]
當時對文學藝術著作的翻譯是非常流行的,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伯林舉出了兩個理由:一是相比獨立創(chuàng)作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翻譯“作為一種逃離政治危險的工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對翻譯的重視還在于目前不斷強調重視蘇聯(lián)邊遠地區(qū)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后果是那些流行語種諸如烏克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烏茲別克和塔吉克語的譯著,受到了政治上的獎賞。”作家們告訴伯林說:“列寧格勒沒有受到這種歪風的侵襲,而這在莫斯科已經(jīng)成風。對他們而言,他們不會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改變成烏茲別克或者阿塞拜疆式的詩歌的形式。”[7]36伯林所注重的仍然是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自由性。
三、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解凍”(1956年)
對于蘇聯(lián)50年代中后期的“解凍”,伯林有著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認“解凍”思潮的確使蘇聯(lián)社會政治生活發(fā)生了一些變化,給蘇聯(lián)的文藝發(fā)展帶來了一絲新的生機。但是,在伯林看來,這種變化并非本質上的,而只是表面上的變化而已,是政治統(tǒng)治方式上的一種暫時性的策略。他在1956年蘇聯(lián)之行時,與一些作家和藝術家的談話中感受到了這一點。伯林訪問了蘇聯(lián)文學歷史的主要機構普希金研究所所長阿列克謝耶夫教授,“阿列克謝耶夫教授說一切要比斯大林時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時代永遠的結束了。然而,文學研究仍然受到壓制,因為政府很明顯的偏好于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但這同1940-1953年相比較來說,已經(jīng)是天堂了。……我問到,他是否認為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的名譽可以得到恢復;他凝視了一會,看著另外一張桌子,說他不知道。氣氛變得有點冷,不久我就離開了。”[8]
1956年是蘇聯(lián)“解凍”剛剛開始的階段,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這一進程能夠進行到什么程度,畢竟他們都是經(jīng)歷過斯大林黑暗統(tǒng)治的人,高壓專制的陰影在他們的腦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伯林認為,赫魯曉夫繼承了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赫魯曉夫的改革,正是這一路線的體現(xiàn),是在斯大林高壓政策之后的一個緩沖期。帕斯捷爾納克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在國外的出版而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作為一個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伯林用自由主義的眼光來分析蘇聯(lián)文學和藝術,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理解和認識。他對蘇聯(lián)的文學和藝術狀況總體上持否定的態(tài)度,不僅僅是因為蘇聯(lián)文學和藝術的發(fā)展在政府的壓制下,在意識形態(tài)的禁錮下,陷入了低潮,還因為蘇聯(lián)文藝在種種的限制與壓制之下,藝術的目的發(fā)生了變化。
伯林認為,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而不存在其他的目的,但并不是說藝術和藝術家就不負任何責任,藝術應該關注道德和社會問題,但是這種關注并非使其成為它們的工具。那么,在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目的發(fā)生了怎樣的改變呢?伯林指出,在蘇聯(lián)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學藝術成了一種實現(xiàn)最終目標的手段,而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伯林的這種藝術觀在他認識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過程中是貫徹始終的。蘇聯(lián)文藝的目的發(fā)生了改變,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作失去了自主性,由此導致了蘇聯(lián)文學藝術的僵化與停滯。
參考文獻:
[1]伊格納季耶夫.伯林傳[M].羅妍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2][3][4][5][7][8]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6]М·Р·澤齊娜等.俄羅斯文化史[M].劉文飛、蘇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