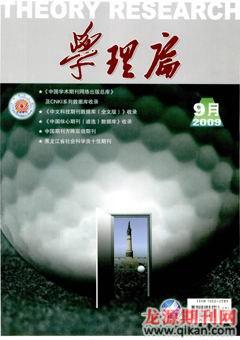邊緣化的“野草”
史 憶
摘要:本文從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對2007年諾貝爾獎得主、英國女作家多莉絲·萊辛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進行解讀,分析小說女主人公瑪麗悲劇命運的根源在于男權社會環境,瑪麗作為女性是男權話語社會的邊緣人,但作為白人,她身上還是帶著很深的殖民主義烙印,她最后的死亡結局不僅是她個人的悲慘命運,也象征著白人統治在南非大陸的必然終結; 男主人公摩西是南部非洲殖民世界爭奪話語權的黑色邊緣人,其具備高尚的品質,并為爭取話語權進行抗爭,然而他的行為只停留在個人行為的階段,還是萌芽階段的反抗。
關鍵詞:《野草在歌唱》;后殖民女性主義;男權;話語權;邊緣人
中圖分類號:I106.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3-0092-02
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是西方學術界“少數話語”的兩種主要代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批被稱作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批評家在二者之間開辟了一個新的理論空間,他們批評西方女性主義的白人中心主義和本質主義,并從后殖民立場對西方女性主義的經典作品進行了新的解讀。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小說家萊辛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一問世,便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它觸及了萊辛創作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婦女的生存環境及其社會地位,種族歧視制度和文化歷史背景對于個人生活的影響。書中通過對女主人公瑪麗具有典型意義的悲劇命運的描寫,深刻揭示殖民統治制度下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人與人之間的本質關系。
一、瑪麗:男權世界中的白人女性
小說的女主人公瑪麗毫無幸福可言。她的童年就是臺階上那所骯臟的小屋、嗚嗚的火車和父母間無休止的爭吵。她的雙親都是南部非洲白人。她的父親整日在鎮上的小鋪喝酒,使得家中入不敷出,于是母親每日除了籌劃家務,縫縫補補,還要到小鋪去吵鬧出氣。瑪麗非常“憎恨自己的父親”[1]。在母親死后,她“難得看到父親,父親雖然喜歡她,卻丟下她不管”[2]。而對瑪麗而言,“丟開父親倒是給母親生前的痛苦報了仇”[3]。瑪麗一方面痛恨父親,厭惡母親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又受母親“奴性”思想的影響,當提到父親時,她認為“他不是個男人嗎?他大可以隨心所欲”[4],而女性只是生兒育女,操持家務的物體而已。
可以說瑪麗的一生都在女性主義和男權思想之間搖擺。在父親死后,瑪麗感到“自由自在”[5]了,她希望自己這種平靜而舒適的生活繼續下去。她當上了老板的私人秘書,薪金收入相當可觀。“她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6],“但是這又違背了她的本性”[7],她仍然是一個要男人“帶出去”的姑娘。她好像并不把男人放在心上,“可是出了辦公室,出了俱樂部,她的生活便完全依靠男人”[8]。她不愿結婚,因為“一想起結婚,她就記起父親生前回家來那種醉的眼睛通紅的模樣”[9]。盡管瑪麗渴求獨立,然而迫于世俗的非議,她必須找一個丈夫。
于是瑪麗和迪克結了婚,她把對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經營農場的迪克身上。瑪麗和迪克并不相愛,是不得已和迪克結婚,而迪克和瑪麗結婚也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的夢想就是討老婆生孩子”[10]。在瑪麗的眼中,迪克“不僅是一個又瘦又長,彎腰曲背的男人,而且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滿腔熱忱被潑了冷水以后,還是一股勁地要拼命干到底”[11]。瑪麗一方面看不起迪克,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夠依賴迪克,“她需要一個比自己堅強的男人,她要設法把迪克磨練成這樣的人,如果他的意志力確實比她強,并因此真的占了她的上風,那她一定會愛他”[12]。瑪麗的所作所為既改變不了窮困的境況,也擺脫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終于,在極度痛苦中她決定逃離農場回到城里去,這是她向生活所做的唯一一次抗爭。但她又一次失敗了,城市拒絕了她,她的社會身份已經從經濟獨立的白領女子轉變為寒傖可憐的鄉下女人。
瑪麗的一生痛苦而矛盾。她向往獨立自由,但在男權體制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她的思想被打上了男權的烙印,渴望改變生活,卻寄希望于丈夫迪克。在唯一的一次反抗失敗和對迪克徹底絕望之后,她的世界就已經崩潰。死亡的結局是瑪麗一生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摩西:爭奪話語權的邊緣人
摩西在小說中占的描寫成份并不多,但與傳統的黑人形象被惡意污蔑、肆意歪曲不同,萊辛真誠、執著、勇敢地將摩西塑造成為一個有著獨特個性的南非黑人。
根據后殖民主義理論,話語是權力和知識的連接物,權力的擁有者控制了需要了解的事物以及掌握它的方式。“因而,由話語所體現出的權力和知識的關系尤為重要”[13]。
小說用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了在當時殖民制度統治下的南非失去話語權的黑人奴隸的生活境遇。小說開始,萊辛就以白人對這起謀殺案淡漠曖昧的態度向我們揭示:在白人話語中心,不能接受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仆發生感情糾葛。
“萊辛以正面、有力的形象塑造摩西具備的高尚品質,脫離了白人中心的西方語境,為處于邊緣話語的摩西所代表的非洲黑人民族遭遇的不公吶喊”[14]。在南非殖民地,黑人是沒有話語權的,黑人根本不能稱之為人。就連迪克也把和自己相處得不錯的黑色仆人稱為“不壞的老畜牲”。而當時大部分黑人也已經接受了這種歧視和不公。在瑪麗剛到迪克家時就發現黑色仆人薩姆森和迪克之間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主人家提防他偷竊,他卻毫不介意,聽其自然”。[15]因為白人“有警察、法庭和監獄作后盾,而那個土人呢,毫無依恃,只有忍氣吞聲的份”[16]。
在這群忍氣吞聲的土人中,有一個人要站出來說話,那就是摩西。摩西在小說中出現時,就被瑪麗用鞭子在臉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因為摩西分別用土話和英語表達了自己要喝水的需求。只是用語言表達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卻招致白人的鞭撻。一般白人都認為土人說英語是“厚顏無恥”,更何況摩西臉上還“帶有譏嘲的輕蔑神色”。“我要喝水”四個字象征著摩西爭奪話語權的開始,他不再沉默,開始爭取作為一個生命應有的權利。但這最基本的要求在白人看來是一定要用鞭子扼殺掉的。
摩西在教會里當過差,會讀書寫字,能瀏覽報紙。有一次他問瑪麗,“難道耶穌認為人類互相殘殺是正當的嗎?”[17]。對于摩西這種“懂得太多了”的黑人,白人是怨恨的。在白人看來,“無論如何不該教這些人讀書寫字,應該教他們懂得勞動的體面以及有利于白人的通常道理”[18]。
摩西身上處處表現出與白人一樣的人性,這是白人殖民主義社會無法忍受的。摩西自尊自愛,寬容善良。在遭到瑪麗鞭撻后,摩西的眼神里充滿了憎恨和厭惡,但當他看到瑪麗家境貧寒,體會到瑪麗的空虛絕望后,他容忍了瑪麗的刻薄和挑剔。他叫瑪麗“夫人”以表示尊重,他盡職于自己的家務,這一切都“迫使瑪麗不得不把他當一個人看待”[19]。
摩西認為自己和白人是平等的。在瑪麗的生活中,他自覺地充當起這位可憐的身心俱毀的白人女雇主的保護者,“直截了當,合情合理地對她表示關注,為她代勞”[20]。一次偶然的情況下,瑪麗撞見了正在洗澡的摩西,“這對她的感官實在是一種刺激”[21],也使她意識到摩西也是一個人。“一個非洲白人在偶然的情況下窺視到一個土人的眼神,看到那個土人身上也具有的人性特征(這是他們先入為主的成見最不愿意想到的),在他的仇恨感情中會生出一種愧疚,盡管他不承認,最終他會放下手中的鞭子”[22]。瑪麗正是被摩西身上的人性所打動,愛上了他。而摩西也認為,這位女主人最終是把自己當作一個人來尊重和愛的。但在小說最后,當托尼出現時,瑪麗立即背叛了摩西,這使摩西認識到,在白人眼中,即使是在自己所愛的瑪麗眼中,自己還是低劣的。摩西最終舉起刀刺向瑪麗來表達自己作為人的憤怒與反抗。
作為女性,瑪麗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在白人男權世界中處于邊緣話語。然而作為白人,瑪麗以白人話語身份壓制虐待奴仆,仇視黑人。帶著從小開始的殖民主義教育的烙印,瑪麗處處挑剔傭人,刻薄對待奴仆。“她恨他們這些人,沒有哪一個不讓她恨,從工頭直到最小的孩子”[23]。但正是摩西這樣一位黑人奴仆,給瑪麗帶來了被愛的幸福和愛人的沖動。摩西的尊嚴與平和,使瑪麗“不得不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待”[24]。盡管如此,當英國青年托尼發現他們的關系時,瑪麗立即與托尼站在一起而不惜傷害摩西,竭力維護白人的立場。
作為一名白人女性,瑪麗從小接受殖民主義教育。在她的眼中,黑色土著“是骯臟的,并且可能會對她做出可怕的事情”[25]。在黑人土著面前,瑪麗有著強烈的白人優越感,是一位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執行者。當她個體的人性與殖民環境發生沖突時,她立即站在殖民主義立場上,這是必然的。
三、結語
作為南非殖民地白人男權社會中的一名女性,《野草在歌唱》的女主人公瑪麗始終都在個人獨立與男權思想之間苦苦掙扎,而作為一名白人女性,盡管她發現黑色土人也具備與白人一樣的人性,但她無法擺脫殖民主義思想的束縛,最終還是站在白人殖民者的立場上。瑪麗最后的死亡結局不僅是她個人的悲慘命運,也象征著白人統治在南非大陸的必然終結。
處于邊緣話語的摩西具備高尚的品質,并為爭取話語權進行抗爭,然而他的行為只停留在個人行為的階段,“只有以民族大團結,民族自強、自立為后盾,非洲黑人所代表的第三世界才能擺脫白人話語中心的抑制,從世界話語邊緣進入世界話語中心”[26],而野草的歌聲也將在世界回蕩。
參考文獻:
[1]-[12][15]-[25]多麗絲·萊辛.野草在歌唱[M].一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8, 30, 30, 30, 31, 32, 32, 34, 34, 43,90, 132, 56-57, 126, 164, 165, 165, 166, 151, 151-152, 119, 97, 165, 61.
[13]羅婷主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35.
[14][26]張海波.多麗絲·萊辛小說的后殖民語境[J].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08,(5).
(責任編輯/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