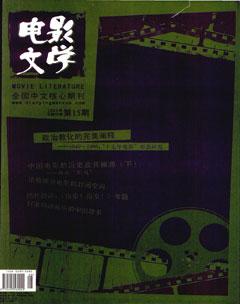角川=主人公?
鄭曉芳 崔 酣
電影《南京!南京!》(以下簡稱《南》片)帶給觀眾的第一印象是中國歷史上“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慘痛與敏感,充滿陰霾的黑白色調的電影畫面和低沉平緩的敘述節奏。尤其與眾不同的是,陸川導演選擇一名普通日本兵角川作為故事的敘述者。這種非傳統意義的故事敘述者(即主人公)的選擇.徹底顛覆了傳統意義上愛國主義影片的理論預設。觀眾似乎更習慣于從歷史事件本身出發,往往以情感因素模糊認知評價.或者采用中立的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評價,或者傾向激進的愛國主義乃至民族主義的判斷。二者均用真實的歷史取代了文本的真實,其實質是混淆現實與文本的差異,容易對影片造成誤讀。如果以結構主義符號學為理論基礎,分析影片的文本結構,就能回到文本并且把握文本的意義。
結構主義首先是一種方法,認為“事物的真正本質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們在各種事物之間構造,然后又在它們之間感覺到的那種關系”,將“構造”和“關系”作為理論的支點。其次結構主義追求“深度模式”——種存在于現象底層的內在性質。第三,結構主義注重文本的整體性,強調文本系統和外在的文化系統對文本解讀的重要性,而文本整體系統“并非事物本來的整體,而是分割事物找出各元素后再組合而成的整體”。在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之上,首先疏理《南》片文本中的基本人物關系:
A侵略者:角川、伊田……
B受難者:唐先生、小江……
c反抗者:陸劍雄、小豆子……
D援助者:拉貝、江淑云……
以人物關系為線索可以找到全文的要素單元。要素單元可以重構文本內在結構整體的內涵,單元之間又具有必須的關聯。
不難看出影片以A中的特定人物角川為敘述者的設定,作為具有敘述者意義的角川以一種異類的形式游離于A類之外,除了在A3占領教堂中的“誤傷”事件外,他參與所有單元的活動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見證,并在A2和A7中提示其教會學校的經歷,表明與其他侵略者的區別。單純將A中的角川歸入敘述者的行列,可以起到運用對立面來證實事實的作用,從而增加影片的客觀性與真實感,這是導演為其設定的基本功能。從1—13的經歷中又提供了一條由最初的盲目的戰爭參與者到見證戰爭暴行后試圖回歸人性卻最終失敗(即以自殺結束)的線索,暗示著反思戰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B作為受難者完成了從破除幻想到最終覺醒的過程。幻想來自A可能的憐憫、D提供的庇護和c帶來的殘存不多的希望。唐先生作為代表這一幻想的執行者一直在妥協中后退(B2、B3、B7),直到幻想完全破滅(B8中女兒的慘死和妹妹被掠)后的自發性的覺醒B9。這一僅存的自發的覺醒行為構成B向自覺抗爭的基礎,同時導致了D中姜淑云的轉化。
D類援助者在影片的出現充滿符號色彩,有“南京的辛德勒”之稱的約翰·拉貝只是作為背景存在于影片中,在D2、D6。D9的單元里都以極度弱化的姿態連接A和B。姜淑云的角色作為D類中的變數在影片中經歷由D向B的轉換,在D10順序中完成了身份轉化,由外來援助者的立場向自己的民族的受難者的身份的回歸構成了B自我覺醒的升華。由唐先生到姜淑云、由D到B的過程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體現。
c類的抵抗者形象是片中最難把握的部分。與D一樣,c的直接作用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陸劍雄的短暫出現給A帶來了打擊,雖不致命但震懾感明顯。為B帶來過希望但更帶來了絕望。作為力量象征的軍隊的反抗者的失敗使B的生存可能演變成了幻想。作為c中另一引人注意的角色——小豆子.完成著反抗(作為c的一員)一失敗(轉化成B)一希望(潛在的重新成為c)的過程,與B(唐先生)和D(姜淑云)一起重新回到傳統敘述者的立場。
A參與了以時間為序的1~13的每個單元,并且與B、c、D都發生關聯。只從縱行的角色歷時性上看,可以得到的只是各類人物的經歷;從橫行結合關系上可以得到故事的共時性脈絡。而故事的展開正是以共時性為基礎的,另類的敘述者角川不斷地由前景轉化為背景,只在All那場預言式的祭奠中尋找并觸發自我救贖的可能。在這種自我救贖的演變過程中角川的直接體驗包括在A3中與B發生的關系.在A8中與小江(B)發生的關系,在A11)中與姜淑云(轉化為B的)的關系,在A12中與小豆子(c)發生關系。其所有行為的結果都強化了B、c、D的變化過程,其敘述者的地位如同人物的命運一樣瓦解于故事的結尾。
結構主義代表人物格雷馬斯認為:“一切敘事都具有6個最基本的雙雙成對的行動元:主體/客體,發送者/接受者,幫助者/反對者。”主體是影片的主人公,客體是主體的目的,欲求聯系主客體,使主體朝向客體,去獲得客體。發送者是把客體發送的角色,使主體具有追求的目標,接受者是接受客體的角色,發送者和接受者可以與主體和客體重合。幫助者是幫助主體獲得客體的角色,反對者則是反對主體獲得客體的角色。這6個行動元在具體事件中構成了兩個軸系,一個軸系以主體欲求的對象客體為中心.另一軸系以主體欲求反映于幫助者和反對者的關系為模型。
在《南》片中將角川置于主體地位,影片就會以角川力圖脫離A的自我救贖為主要線索,得到如下結果。
主體——自我救贖的侵略者(《南》片中盲目參與戰爭的角川)
客體——救贖回歸人性(《南》片中最后自殺的角川)
發送者——血腥的事實(《南》片中A的暴行和B、c、D的生存狀態)
接受者——希望實現救贖的侵略者(《南》片中的角川)
幫助者——殘酷戰爭中的承受者(《南》片中B、c、D)
反對者——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南》片中A)
故事的進行依照角川擺脫自身原初立場A向自我救贖方向前進的過程,故事將以“不覺悟一覺悟一抗爭一失敗”的方式完成。格雷馬斯的理論在6個相關行動元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符號矩陣”,“符號矩陣”將歷時性的故事的過程轉化成共時性的系統,系統按照二元對立的方式組織.在二元對立中強調對立各方的轉換.而轉換和對立都是建立在3對6種基本行動元的結構上,最終完成共時性的靜態系統,即設立一項為x.它的對立一方為反x。除此之外是與x矛盾但并不一定對立的非x(反反x),又有x的矛盾方一非反x。
角川作為主體是故事的主角同時代表受蒙蔽的普通日本兵。他的目標客體是尋求自我救贖的人性回歸;軍國主義是反對者,它把日本的普通軍隊卷入戰爭并在血腥中將惡的人性放大,它從自身的需求(控制戰爭機器的主要構成部分“人”)出發反對角川們尋求自己善的人性:作為戰爭的承受者,以自己的慘痛境遇喚醒主體的回歸意識.用事實戳穿軍國主義者的騙局,從而成為角川走向自我救贖的推動者。這樣表面上構成了文本邏輯上的完整。
然而文本作者(即導演)與生俱來的文化背景注定對故事造成影響。角川們始終是沉默的參與戰爭的侵略者中的少數,故事以此為線索的敘述注定只能是導演的期待。導演
通過影片反思的應該是被淹沒于歷史中的受難者,不僅僅是同情他們的遭遇、控訴軍國主義的暴行.更是發掘這樣一個群體中的覺醒、抗爭的精神。此時故事的敘述者轉化為受難者(影片中以B為主并整合c、D),但是受難者的敘述是片段性的,只有在以A類群體即包括角川在內的日軍為整體的背景中進行。格雷馬斯模式中行動元雙軸變成了:
主體——殘酷戰爭中的承受者(《南》片中B、c、D)
客體——對侵略者的痛恨和自我不斷的覺醒(《南》片中B、c、D轉化進化的結果)
發送者——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南》片中B、c、D)
接受者——殘酷戰爭中的承受者(《南》片中B、c、D)
幫助者——由自發向自覺抗爭的承受者(《南》片中陸劍雄、姜淑云、覺醒后的唐先生)
反對者——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南》片中A)
受難者作為主體,包括影片中相互交集的B、c、D,他們的目的是反侵略;他的反對者是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抗爭作為目的也作為手段不斷推進著受難者的自我覺醒.這一過程也成為主體的幫助者并完善主體的蛻變。這里主體呈現了自我不斷覺醒升華完善的過程,目的與手段相契合為戰勝軍國主義者和反侵略戰爭的勝利預留了可能。
由此可見,影片敘述中雙重主體的存在實現了深層結構的構建,為表達有理性、有深度的認識鋪平了道路:也實現了文本導演、故事敘述者、故事角色不同立場的調和。建立了更多維度的觀察視角。角川的自我救贖從覺醒到失敗并最終導致自己的毀滅,但他為陸劍雄們、唐先生們和姜淑云們的自我覺醒、抗爭留下了希望和繼承者(小豆子)。兩個不同的敘述者在反抗共同敵人——軍國主義的斗爭過程中實現著同樣的價值。導演力求站在今天的歷史中反思過去的戰爭,構建自己的認識體系的意圖最終在敘述者的傳遞中一覽無遺。沒有激烈的控訴,沒有燃燒的憤怒,沒有冰冷的評價,也沒有過度的苛求與指責。在自己的故事里表達對歷史的尊重,對逝去受難者的尊重,對為反抗而犧牲者的尊重,對提供幫助者的尊重,對悔過者的尊重……在充滿隱喻和符號的影片中清晰凸現。導演的反思和希望同小豆子手里的蒲公英一樣去嘗試著在不同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參考文獻]
[1][英]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8.
[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33.
[3]張法.20世紀西方美學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