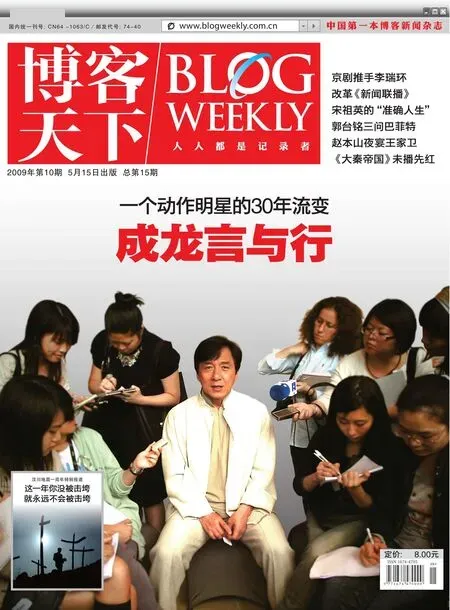梅婷的18歲青春記憶
■文 / 梅婷
梅婷的18歲青春記憶
■文 / 梅婷
記得姜文讓我試穿一件紅色的游泳衣,他說:你還是個小姑娘,還沒長開呢。我很不服氣,反駁道:我是大人,我什么都懂!
如果算上虛歲,我的18歲橫跨1993和1994兩個年頭。從1993年春節開始,我就一腳跨進了北京。如今想來,也許正是這第一步,改變了我今后的人生之路。
第一次上春晚
1993年
春節
春節前夕,我所在的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舞蹈隊接到一個任務—參加1993年的央視春晚。由于演員隊人手不夠,于是就從我們學員隊抽調了4個人充數,我便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參加的節目都有哪些,我有些記不清了。只記得,我的大部分演出都是伴舞,那是我第一次春節沒和家人一起過,從那以后就接二連三了;還記得,毛寧唱了《濤聲依舊》,因為我同屋的女孩給“那一張舊船票”伴舞,所以我們倆偶爾有機會和毛寧一起玩,他人很好,很隨和;還記得,趙本山就住在我們斜對門,他養了一只小京巴,三十那晚演出后,在趙老師的允許下,我抱著那只小狗,穿過央視大樓后面的民宅回賓館,一路炮竹聲震耳欲聾,仿佛頭頂臉邊都炸開了花;還記得,三十晚上我看到了施拉普納(德國人,1992至1994年間擔任中國足球隊主教練,是第一位擔任中國隊主教練的外國人)的后腦勺,他被一幫人簇擁著穿過走廊,在當年沒有一個明星有這樣的陣容,身邊有人發出感嘆:唉,真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我還看到了禹作敏,但剛到夏天他的神話就被滅了。
我還記得,我被陳佩斯選中了去演他們的小品《大變活人》,我就是那個從箱子里變出來的女孩。我還記得,我求朱時茂讓我開一下他的車,結果一踩油門就上了馬路牙子,那是我的第一次“駕駛”經驗……對不起,對不起,我的記憶出了點偏差,被選上演小品是第二年春節的事了,我給記混了。當然,那時我也還是18歲,你說是吧,我那轟轟烈烈的18歲!


記得當時年紀小,自稱什么都不知道
與“米蘭”擦肩而過
1993年
夏
放射治療每周5次,放射劑量如下:食管原發灶GTV為50.0~56.0 Gy,頸部淋巴結轉移灶GTV為55.0~61.6 Gy,胸段淋巴結轉移灶GTV為50.0~56.0 Gy,腹部淋巴結轉移灶GTV為50.0~54 Gy;全食管淋巴引流區CTV預防照射劑量為45.0 ~50.4 Gy。
入了春,我們便開始了緊張的訓練和排練。為了迎接畢業匯報,老師們和同學們都飆著一股勁兒。在我們男女練功房的中間有一扇門,門上不知被哪一屆的“好學”的前輩挖了個洞。一旦臨近下課,這個洞就會被一
只或幾只眼睛堵上,有時是男生看女生,有時是女生看男生,這要取決于哪一邊先下課。有一次,好不容易下課了,作為班長的我趕緊推門叫大家準備集合吃飯,結果撞上了一個男生的鼻子。很多年后,那位男生說他的高鼻梁是拜我所賜—我竟然把他的鼻梁撞斷了,而我卻一無所知。
這年夏天,我還被《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組選中去試米蘭這個角色(后來是寧靜演的),這讓我又一次可以去北京了。這次和上次不一樣,是夏天的北京;這次還和上次不一樣,沒有了部隊的管束,我跟著劇組的人到處玩,到處看。
其實當我第一次和夏雨、耿樂他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合適了。那時剛經歷完高強度的演出,我很瘦,和他們在一起顯得比他們要小一號。在那之前我已經讀過王朔的小說,知道米蘭應該是個很豐潤相對成熟的姑娘。記得姜文讓我試穿一件紅色的游泳衣,他說:你還是個小姑娘,還沒長開呢。我很不服氣,反駁道:我是大人,我什么都懂!
若干年后有一次碰到姜文,他笑著問我:你還記得嗎?你小時候說你什么都懂。哈哈!那時真是幼稚,現在經歷了那么多反而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回答。說完我就后悔了,我怎么又一猛子把自己說到絕路上去了:小時候是裝老道,現在又扮清純。
總之那一次我被淘汰了,以前每次劇組來挑人我總是被選上,這是第一次慘遭失敗,帶著沮喪的心情我回到了南京。其實心情也不是太差,因為有嶄新的生活在向我召喚,過了這個暑假,我們就成為正式的演員,開始領工資啦!
報考北京電影學院
1993年
冬
眼看著冬天就到了,這一年我們團又被選中了參加春晚。這次足足在北京呆了兩個月。
在北京期間,有一天我們放假,我去《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組探班。那天他們在莫斯科餐廳拍戲,記得王朔也來串戲,穿了一身舊軍裝,坐在長條桌的盡頭。那個鏡頭是一大長條桌人都舉杯歡慶什么,他也舉著杯子樂呵呵的,看上去有點靦腆。姜文讓我別走,演一個服務員。他們給我換上衣服,梳好辮子。不過一直等到半夜還沒有拍上我們那場戲,我實在等不及就走了,怕晚上我們隊里會查房。
在劇組的時候有人跟我說:你條件挺好的,可以去考電影學院,他們每年冬天都招生。這件事我一直惦記著,終于等到過完年回到南京,有一天,看到報紙上登了一條小廣告: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94級開始全國招生……
部隊培養了我6年,我們畢業時簽了合同必須為部隊服務多少年,具體多少年我忘了。所以我知道團里不會放我,更不會同意我去考什么電影學院。我們家是個傳統的軍人家庭,爸爸是軍醫,哥哥也在軍校里當老師。我說我要考電影學院,我爸首先反對!我媽也不贊成,但表示如果我非要去上海考試,她就陪我去一趟。可能她想的是沒準我考不上,很快就會回來。于是,我帶著我老媽和借來的《烏鴉與麻雀》就上路了。我當然沒跟團里說,只是跟他們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
沒曾想過五關斬六將,我竟然一關一關考到了底,一直走進了最后的體檢。記得體檢是在上海的八五醫院進行的,那是一家部隊醫院。醫生讓我們每個人拿身份證掛號,我掏出軍官證問:我是軍人,要收費嗎?醫生翻看著我的證件說:不用!哦,你是梅婷啊,我和你爸爸是軍校的同學,你爸爸現在還好吧!
而我爸這會兒正如坐針氈呢!團里打來電話,問我病好了沒,怎么還不回去上班。我爸本來就對我有意見,一想反正我專業課考試也通過了,干脆就和盤托出說我去上海考試了。于是,當我歡快地坐上火車,想著回去怎么跟領導說時,那邊已經準備好了大刑伺候!
《紅櫻桃》救了我
1994年
春夏
這是我過得最黯淡的一個冬季,雖然春的腳步已經臨近,但我卻看不到一絲回暖的意思。我被團里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扣除三個月工資、停止一切排練專心寫檢查、關禁閉不能和大家一起參加演出。
在這期間,我的同學們都出去演出了,我倒是免除了關禁閉這一說,反正周圍都沒有人。我每天反復地寫著檢查,但總也通不過。我就是想不通,考大學不是一個年輕人要求上進的舉動嗎?在這種情緒下,我反反復復寫了N遍,最后教導員終于放我一馬通過了。我跟她商量:能在私自離隊后面打個括弧,寫上報考大學嗎?也好表示我不是去干什么壞事。因為我聽說處分和檢討是要進檔案的,它們會跟著我一輩子。教導員回答:說明你還是沒有深刻認識到你的錯誤,不行!
那些原認為永遠沒有頭的日子,終于一點一點地過去了。我自然是不能參加高考,更不能離開部隊去北京上學。但到了4月,事情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
葉大鷹導演率張黎、楊亞洲到我們團來選演員,我被叫去和他們見了面,還試念了一段臺詞。我有一搭無一搭的,心里想:我這樣的落后分子,就是選上了也不會讓我去的。結果沒想到還真被選上了,而且團里還真就同意放我走了。我本以為,他們可能覺得沒讓我去上大學,還給了我處分,扣了我工資,這次就算是補償我一下吧。其實,是這部戲的編劇(叫江奇濤,也是我們南京軍區的)為我在軍區說了情,團里才放了我的。
這一年的夏天,我隨葉大鷹的《紅櫻桃》劇組和陸毅、郭柯宇等一撥小演員北上,去到比北京更北的地方—俄羅斯,一呆就是半年……當然,這已經是我19歲以后的事了。現在一年一年過得飛快,但在那時,日子總顯得那樣的漫長。回眸間,宛如一個青春的悠長假期。
聯系編輯:(010)67148585-8010 郵箱:bcj_1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