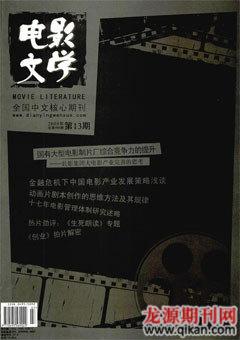藝術人生的還原 心靈史詩的呈現
陳旭光
[摘要]《梅蘭芳》代表了陳凱歌電影追求的新風貌,成為陳凱歌電影從前期電影濃厚沉郁的超越性哲理追求到回歸現實、人生的“世俗化”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影片具有濃郁的文化感同時又極為重視講故事,展示了一代京劇大師的藝術人生和個體化的心靈史,也飽含了導演陳凱歌自己堅忍執著、欲說還休的人文訴求和藝術情懷。
[關鍵詞]藝術人生;心靈史詩;陳凱歌;文化感;藝術精神
《霸王別姬》的成功尚未成為“忘卻的記憶”,我們無疑會對《梅蘭芳》抱有強烈的期待。
《梅蘭芳》正是在我們強烈的期待中,以優雅的風格、傳奇。富于文化感的情節,充滿人生感的戲劇張力——款款進入我們的期待視野。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電影的藝術軌跡和文化版圖上,陳凱歌無疑常常呈現出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的姿態,具有一種較為濃厚的精英知識分子氣質,堪稱“少年凱歌”,勃勃英姿。這與“五四”以來的一種“少年中國”的精神和“五四”新文化氣象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承傳性的。他一直自認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單純意義上的電影導演,他說,“與其說我是一個電影導演,我寧愿說自己是—個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敘說(用弘揚、宣揚這類詞對我來講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現在談對中國文化現狀的憂慮,是徒喚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積的呼應。但用電影表達自己對文化的思考。卻是我的一種自覺選擇。”他還宣稱,“當民族振興的時代開始來到的時候,我們希望一切從頭開始,希望從受傷的地方生長出足以振奮整個民族精神的思想來。”從上述自述,我們不難發現陳凱歌所一向秉有并在他的風格性化的,頗具“作者電影”味道的影片中感知那種“鐵肩擔道義”“舍我其誰”式的歷史使命感、時代精神、啟蒙理想乃至焦灼、沉郁的藝術意蘊。
在一定程度上,陳凱歌在他早期代表性電影作品《黃土地》《孩子王》《大閱兵》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傳達了當時整個社會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國民性、追求“現代性”、向蔚藍色文明大踏步邁進的高遠理想。雖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與其少年英氣不甚協調的悲涼沉郁和蒼涼迷茫,但總的氣象是積極向上的。此后在時代文化的劇烈轉型中,陳凱歌的探索似乎因其獨特的精神氣質似乎一直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他陷入一種矛盾和沖突之中,創作追求開始分化。
《邊走邊唱》在主題意向上有所偏移,更為凸顯的是精英知識分子的藝術理想,自我意識、人生追求等哲理主題,民族歷史感有所淡化。
15年前斬獲“金棕櫚最佳電影”的《霸王別姬》是各方面都結合得比較好的成功之作。主題宏大,試圖把京劇舞臺與歷史舞臺合一。巧妙地借用了“戲中戲”結構。影片非常重視戲劇化的視覺形式的建構,在視覺美感上頗具凄艷華美的意象美。《霸王別姬》的時間跨度很大,它以中國50年的歷史為背景,試圖表現人陛的兩個重要主題:迷戀與背叛。影片借用“戲中戲”結構,把京劇舞臺與歷史舞臺合一。對一種文化的歷史變遷表達了深情款款的關注,有明顯的包容萬象、概括歷史的雄心。
程蝶衣的形象似乎與陳凱歌《邊走邊唱》中的探索一以貫之。陳凱歌自己說過,“從創作的角度來講,程蝶衣這個人物是創造者的一個支柱。作為一個演旦角的演員,他的生活跟舞臺表演沒有辦法區分。”
總之,《霸王別姬》是一曲傳統文化的挽歌。既有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內省,也有迷戀與賞玩,對待傳統的態度比較復雜。
在陳凱歌電影創作的歷史上,《霸王別姬》具有一定的轉型性意義,它一反過去對理念表達和華美造型的迷戀,而是比較注重講故事和敘事性,通過生動的人物,曲折的情節,把一個悲歡離合的人生故事講得有聲有色。
此后的《風月》在題材上頗有獵奇、獵艷、奇觀化之嫌,其原意雖在于挖掘人性的深度,在情節劇中探索人的本真和生命狀態。但似乎略顯病態。正如有人評價的那樣,“陳凱歌的《風月》就是一次向精神廢墟的尋蹤。在昨日的廢墟里挖掘,在廢墟的迷宮里戀棧,從而也使他的理想主義在廢墟的陰影里失落的電影之旅。”
《荊柯刺秦王》讓人有莫名其妙之感,雖然氣勢很宏大,人物豐富復雜,心理世界的探人也頗為深刻,視覺效果極好,通過加字幕呈現的結構方式也很有特色,電影語言更是純熟老到。電影無疑是試圖借助歷史演義講述關于權力異化的寓言。一以貫之的是對秦王之人格分裂和異化的哲理思考,權力對秦王的異化是通過秦王與其父、與其母、與其友、與其情人等的多重復雜關系展開的。但這種方式太滿,個人主觀化、刻意化痕跡太重,此外影片結構性很強,似乎是對歷史進行重新觀照和結構,但有些負荷過重顯得不和諧。
陳凱歌的《和你在一起》雖是陳凱歌難能可貴的回歸平民和世俗之作,但世俗卻未能免于庸俗。把一個本來頗有現代性意味的關于個人價值自我實現與親情倫理沖突的復雜主題,簡化為未免簡單化的倫理價值評判,而且有一種倫理至上的意味。更不乏煽情。兩個對立的教授的設置尤其臉譜化和類型化,沖突的依據不足,缺少應有的張力。影片的影像堪稱流光溢彩,哪怕是大雜院的平民生活,都拍得很漂亮華麗,也很不現實。這既反映了陳凱歌之類成功人士與中國現實的“隔”,也折射了他一以貫之的那種精神貴族的格調。
總之,比起張藝謀的游刃有余,八面玲瓏,引領時代潮流,陳凱歌的電影探索,如《風月》《荊柯刺秦王》《和你在一起》《無極》等,往往是主觀意圖太強烈,想要表達的主題太復雜,總給人留下不和諧感以及諸多遺憾。在我看來,造成這種“錯位”的根本原因是文化語境的巨變。陳凱歌在時代文化轉型的巨變中顯得有些迷茫,這影響到電影文本層面(如敘述結構、悲喜劇風格、價值取向等)上的不和諧。往往是既反映了文化轉型的一些趨向(如視覺奇觀化、投合西方的“后殖民”傾向、封閉的淡化時代背景的大宅院、敘事性的增強、世俗化策略等等),同時又頑固地保留了第五代的一些理想(如歷史感的追求、寓言化的表意策略)。總之,其電影表意的復雜錯亂是文化轉型年代所有復雜性的表現。
進入新世紀。經歷了《無極》的低潮后,陳凱歌似乎憋足了一口氣,選擇回歸“文化電影”,又一次表現和解讀他體會甚深,或可稱駕輕就熟的中國文化精粹——京劇。取材于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的故事,拍攝帶有“傳記色彩”但又合理虛構的《梅蘭芳》,它代表了陳凱歌藝術電影的新世代新風貌,成為陳凱歌電影從常常有點“濃得化不開”的超越性哲理追求到回歸現實、人生的“世俗化”轉型的重要里程碑。
《梅蘭芳》聚焦于梅蘭芳的心靈世界,三段式結構雖未道盡大師一生,但這部具有濃郁“文化感”同時又極為重視講故事的“情節劇”,展示了一代京劇大師的藝術人生和心靈史,也飽含了導演陳凱歌自己堅忍執著、欲說還休的人文訴求和藝術情懷。
全片以梅蘭芳的人生軌跡為時間線,不同于《霸王別姬》將近半個世紀的感情糾葛和世事沉浮,導演這進行了刪減,只為我們展現了其一生中“死別”“生離”“聚散”三個重要片段。既大
刀闊斧,又細致入微,類似于中國傳統繪畫中潑墨寫意的筆法,點彩構砌,濃縮了梅蘭芳的藝術人生。
作為具有“傳記”性質的電影,傳主本身對導演具有約束性,不允許導演超越事實本原,進行天馬行空的情節虛構和悲情演繹,作為一代文化名人的梅蘭芳毫無疑問更應該是“雷池”多多的。導演首要做的就是“還原”原本,但是導演并不拘泥于“還原”與“再現”,而是進行“詩意”的處理和合理的虛構,使全片在寫實的基礎上具有“寫意化”的濃郁抒隋色彩和戲劇沖突性較強的情節劇特征。就片中的感情戲來說,那段梅孟之間由鐘情到幻滅的愛情,在導演那里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戲劇沖突。相反,充滿寫意性、撲朔迷離的愛情借用“京劇”來暗喻曲折表達。既含蓄蘊藉又充滿諍隋畫意。經過電影的這種“詩化”處理,這段感情顯得純凈美好并且勵志;顯得既是遺憾一世。更是千古必然,幾乎成了—個晶瑩剔透的傳說,—個勞燕分飛的慨嘆。一個流傳千古的愛情寓言。與此相似的是梅蘭芳與邱如白的關系,也是恰到好處。張力十足,耐人尋味而撲朔迷離。雖然導演并未刻意渲染,但如有觀眾(特別是對同性戀話題可能特別敏感的西方觀眾)往那邊猜測,我以為這反倒是影片吸引觀眾的某種“情節劇法“的成功之處。
影片的第一篇章主要關注梅蘭芳的京劇藝術革新問題,但往后第二、第三篇章,導演并沒有把筆墨的重點繼續放在梅蘭芳藝術的追求上,而是放在他怎么做人上,細膩真實地濃縮了梅蘭芳的藝術人生。即使是關注藝術革新,導演似乎也是更為關注怎樣做人。如“斗戲”段落。“爺爺”十三燕實際上成為一代老京劇藝人的文化形象。“祖孫擂臺”這場戲的結局使梅蘭芳開啟了一個屬于他的新時代。從這場戲中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梅蘭芳藝術人生成功的起點歸功于革新,也源于京劇自身所內蘊的生命力。正如影片中少年梅蘭芳所說“真正的好戲是人打破規矩”。十三燕期望梅蘭芳提拔戲子地位的遺言,和他在最后一次擂臺前的那句“輸不丟人,怕才丟人!”最終成為梅蘭芳藝術人生的導航。陳凱歌憑借他敏銳的洞察力、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流暢雅致的鏡語表達、有相當概括力度的臺詞等。具象了京劇藝術的文化精神與人生精髓。在我看來,通過十三燕雖敗猶榮。退出歷史舞臺的儀式化表現。陳凱歌對傳統文化獻上了一曲深情款款的挽歌,更留下了文化精神的照耀后世。而這種文化精神灌注于此后梅蘭芳的整個人生。這又毋寧說是陳凱歌對傳統文化的最高禮贊。
細細品味這濃縮的“藝術人生”,我們不難發現,影片以有限的篇幅,傳達了無限的人生內涵和文化感,這似乎和導演本人的“藝術人生”產生了某種“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了導演的藝術追求和藝術理念,誠如陳凱歌自述,“我所有的影片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從大的方面說這主題就是人性,然后每部片子還有不同的附題,但都有聯系,這聯系的紐帶是我自己的人生觀,也可以這么說,我所拍的影片都是反映某一時期之內。我自己的生命狀態,我拍每部片子時,我的生命本身都受到了考驗,拍片過程也自幌生命得以灌溉和培育的過程。”無疑,陳凱歌是一個自我意識極為強烈的導演,在許多影片中都寄寓了自己強烈的主觀意圖,刻下了自己強烈的個人化風格化印痕。也許可以說,就像陳凱歌曾表示的,在《霸王別姬》中,自己就是那個程蝶衣,在《梅蘭芳》中,陳凱歌就是梅蘭芳。就此而言,《梅蘭芳》堪稱陳凱歌的又一部精神自傳。
陳凱歌本人也曾表示《梅蘭芳》“讓他有機會將梅蘭芳先生的人格魅力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確,梅蘭芳的生命狀態和藝術情懷與陳凱歌不無“神似”。導演似乎是把自己文人情懷和藝術人生寄托、濃縮在電影中了。在影片中,我們不難找到導演的影子。例如,梅與邱對“藝術有無國界”、藝術是否純粹的矛盾也正傳達了陳凱歌自身的矛盾,兩種選擇正是導演心中的兩種力量沖突糾結的表現。而邱如白代表的是一個陳凱歌的另一個自我——“本我”。從邱如白帶有的明顯悲劇意味的追求和無法得到別人理解的悲慘結局,到梅蘭芳有容乃大、歷盡劫波而修成正果(正如影片最后一個梅蘭芳從臺階往高處走的仰拍鏡頭所流露的),暗喻了梅蘭芳自己從純藝術理想追求到人間煙火的世俗化追求的心路歷程。
“紙枷鎖”也許是導演對自己藝術使命的一種自我隱喻。在我看來,紙枷鎖有點像英國電影《紅菱艷》中的紅舞鞋,是一種掙脫不了的宿命,也是一種類乎浮士德與魔鬼簽訂契約的大無畏自覺追求。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梅蘭芳慢慢地隱忍于宿命而堅韌,他的選擇與堅毅正是導演給自己的心理暗示,就像導演自己所說“我從梅蘭芳這里學到的,就是不怕輸”。的確,梅蘭芳把一生都奉獻給了京劇藝術,就像穿上紅舞鞋那樣身不由己,也許是為了一種別無選擇的文化使命(或文化宿命),他放棄了愛情和自由,雖然收獲了巨大的成就,卻也收獲了無盡的孤獨!
顯然,導演并不著力于星現歷史的史詩感,而是全力聚焦于個人內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的豐富性和微妙性。影片是通過一個人的個體心靈世界的開掘而折射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重點在人而非史(或者說是以人帶史)。這與《霸王別姬》的史詩性取向是不同的。在《梅蘭芳》中,歷史只是一種寫意化的背景(北京、上海還是香港的地域交代甚至還有點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人物內心節奏的變化同京劇程式化的節奏起伏渾然交融,細膩中不乏渾然大氣。如果說《霸王別姬》富含了歷史史詩的韻味和氣魄,令人蕩氣回腸的話,那么《梅蘭芳》則呈現了一代京劇大家的孤獨、豐富而痛苦的個體心靈史詩,真摯、細膩而傳神。
從兩部影片的主要人物形象看,《霸王別姬》中的程蝶衣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藝術“異化”了,成為一種不無偏執的“為藝術而藝術”,戲內戲外不分的藝術精神的象征:而在《梅蘭芳》中,梅蘭芳則由原來人們心目中的精神載體、文化符號,而成為銀幕上血肉飽滿的“梅蘭芳”,甚至是一個“凡人”,一個仿佛就在我們身邊的真實具體的藝人,這是一種“去魅化”的回歸,一種心靈的“回歸”。影片對梅蘭芳不是“神化”而是“人化”,借此,陳凱歌仿佛也隱喻了自己的回歸。從《邊走邊唱》中為一種理想和宿命而活的瞎子、《霸王別姬》中的“癡人”程蝶衣到今天的梅蘭芳,我們足以感知時代的巨變以及陳凱歌心靈的流變軌跡。
導演陳凱歌曾表示,這部影片“寫人不寫事”,希望“把梅先生的精神世界表達出來。”他通過對梅蘭芳的心靈史詩性的呈現,表現的不是梅蘭芳的所謂“形似”,而是內在的“神似”,他是一個凝聚著中華民族精神的靈魂。就像導演自己所說:“這部電影能夠部分接近梅蘭芳首先是平凡人的內心世界,然后再看他怎么成為—個偉大的藝術家,成為一個優秀文化的代表。”梅蘭芳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精神的縮影,同時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導演找到了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一個這樣的“梅蘭芳”就這樣誕生了,他不是一個空洞的偶像或符號。也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他是一個人,一個經過導演的投射,從導演心中產生的,也活在觀眾心中的“梅蘭芳”!
這樣的平衡點也意味著陳凱歌找到了高雅文化和大眾趣味之間的契合點——一種文化中的個體人的命運、傳奇和心靈痛苦!在人物眾多而鮮活的塑造和井然有序的關系呈現以及表現劇情跌宕起伏的同時,他在這部高雅的、有文化的“情節劇”中灌注了很多精神層面的東西。當然這與影片哲理性臺詞、程式化表演性京劇元素的有機介入、優雅的寫意性視聽語言,復雜而順暢的鏡頭內部調度等都是分不開的。影片通過造型感強烈的視聽語言,在三個段落中通過不同的節奏和基調,傳達出人性、人情和人本的真實。“斗戲”部分的緊張激烈和“棄情”部分的凄涼感人在節奏上形成鮮明對比,使影片具有一種張弛有度的節奏感。
影片《梅蘭芳》讓我們欣喜,讓我們在2008年的冬天感到溫暖:陳凱歌濃縮、映射了梅蘭芳的藝術人生與心靈史詩。帶著他新的藝術追求與多年電影藝術和文化的反思,回到了我們中間!“與我們在一起”!
陳凱歌還是那個陳凱歌!不過,比以前更平易通脫而充實洞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