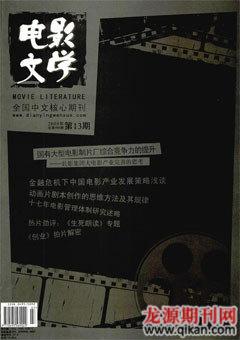論中國早期電影的現代性變奏
李煥征
[摘要]與當代影人力圖“丟掉戲劇的拐杖”不同,中國早期電影人很注意從文學、戲劇借力。認真從鴛鴦蝴蝶派、現代派、左翼文學以及西方電影那里汲取營養,發展自身。本文旨在通過早期影戲、鴛鴦蝴蝶派、現代派、左翼電影以及費穆實驗電影等具有代表性的電影形態,進一步研究中國早期電影在曲折前進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現代性變奏。
[關鍵詞]中國早期電影;現代性
當代電影有一種觀點認為,電影要發展就要“丟掉戲劇的拐杖”,甚至也要擺脫文學的影響,發展獨立的“第七藝術”。然而中國早期電影經驗告訴我們:中國早期電影不僅沒有拋開文學、戲劇,而是認真從鴛鴦蝴蝶派、現代派、左翼文學以及西方電影那里汲取營養,發展自身。當然,中國早期電影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曲折前進的過程中呈現為一種現代性的變奏。
一、早期“影戲”中的現代性觀念
被視為中國第一部電影的《定軍山》拍攝于1905年,然而中國電影的真正起步卻是在上世紀20年代。當時。“影戲”是中國電影人非常看重的藝術觀念。如我國早期電影的代表人物鄭正秋(1889—1935)就把電影看做戲劇之一種。現存最早的中國電影如《勞工之愛情》等,大都實踐著他關于“影戲”的創作理念。
對于鄭正秋來說,電影既是舶來品,自然要學習西方,如《勞工之愛情》這類滑稽戲,即是向好萊塢學習的成果。但是,電影主要是給中國人看的,所以,鄭正秋也深深懂得要適應國人的口味,如《孤兒救祖記》《姊妹花》等,力圖在“歐化”與“舊道德。舊倫理”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他認為:“照中國現在的時代。實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應當替大多數人打算,不能單為極少數的知識階級打算的,藝術應當提高,這句話我們也以為不錯,不過只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提高,否則離現代社會太遠。”這對中國電影而言是一種合乎實際的現代性的起點。
鄭正秋的影戲觀不偏激、不過火,在接納西方與發展民族文化的同時,為中國電影開創了本土化的敘事傳統。即便在他逝世后,這一傳統仍得到了繼承和發展。1947年,蔡楚生與鄭君里合導的史詩作品《一江春水向東流》可說是這方面的典范。影片采用中國章回小說的結構方式,又借鑒中國傳統戲曲的敘事模式,同時把來自蘇聯電影的蒙太奇觀念與好萊塢電影的敘事技巧結合進來,這確實體現出中國早期電影人非常現代的藝術觀念。
二、重新認識鴛蝴派小說與電影
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因為資本、技術、環境等方面的原因,電影業并不成熟。在這個時候,鴛鴦蝴蝶派進入電影。可以說是注入了一股活力。許多鴛蝴派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鵑、徐卓呆等都編過劇本。像《玉梨魂》《啼笑因緣》《荒江女俠》等由鴛蝴派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很受市民階層的歡迎。據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各影片公司拍攝的共約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參加制作的,影片的內容也多為鴛鴦蝴蝶派文學的翻版。”由此觀之,鴛鴦蝴蝶派對當時電影的影響可謂巨大,但在后來的電影史敘述中,對鴛鴦蝴蝶派卻都是貶斥的口吻:“他們帶給電影的主要影響是思想上的庸俗化;創作方法上的反現實主義。”“多數影片迎合社會淺薄心理,沒有正當的思想目的,藝術上人物形象雷同,情節結構千篇一律,特別其中所包含的庸俗的思想內容更給廣大觀眾不健康的影響”。
這種評價是不公正的。筆者的看法是,在辛亥革命后出現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本身就是社會現代化的產物。它所描寫的人物大都受過現代文明的熏陶,并且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行俠仗義、談情說愛,儼然已成為市民階層平庸生活里的消遣。普通五四大眾腦海里現代生活的想象和寄托。可見,鴛鴦蝴蝶派是適應了新的社會發展,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
三、從《上海摩登》回溯早期中國電影人
對現代性的認識
提到早期中國電影人對現代性的認識,我們不能忽略了李歐梵其人。在他看來,工業文明條件下產生的“城市”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基礎”。“而1930年的上海確實已是一個繁忙的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因此,《上海摩登》對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描述,與其說是在進行“懷舊”,還不如說是在追尋中國現代性的譜系。
在《上海摩登》這本書里,李歐梵似乎找到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根”。他從施蟄存、邵洵美、葉靈鳳等人的所謂“頹廢”作品發現了與西方的波德萊爾相銜接的現代性,并進而肯定了劉吶鷗、黃嘉謨等人所倡導的“現代電影”觀念。
1933年3月,《現代電影》雜志創刊,以劉吶鷗、黃嘉謨為代表的“軟性電影”論者將“新興電影”與“現代電影”分別稱為“硬性電影”與“軟性電影”。指責“新興電影”、左翼電影“內容偏重主義”,形式感單薄欠缺,認為“現代電影”應該多研究形式,少發一些空洞的口號。
這些觀點無疑都有可取之處,但是接下來的歷史卻沒有選擇這些現代派的文人們,而是選擇了正在崛起的左翼電影運動。
四、從《三個摩登女性》到《新女性》
——左翼文學、戲劇對電影的影響
柯靈曾談到:“在所有的姐妹藝術中,電影受‘五四洗禮最晚。‘五四運動發軔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時間,電影領域基本上處于新文化運動的絕緣狀態。”可見,“五四”對電影的影響遠沒有對文學來得那么直接而有力。但是“五四”新劇的發展畢竟帶給電影界“遲來的愛”,在這方面,田漢的探索是非常可貴的。由他領導的“南國電影劇社”。成為了中國左翼電影實驗的先鋒。
1930年,田漢在《南國》月刊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我們的自己批判》,認為:“電影早已脫出她的好奇的存在時代而成為一種普遍、極有力的新藝術形式了”。電影是“組織群眾、教育群眾的最良工具。所以我們應該很堅決而鮮明地使用它。”可以看出,這時的田漢已從“銀色的夢”中醒來。把電影完全當成了社會革命的有力工具、民族自救的有力工具。
田漢曾先后投拍《到民間去》和《斷笛余音》,盡管影片都沒有最終完成。但他的劇本及思想卻為電影界帶來了一股新的活力。
1933年,《狂流》《春蠶》《上海24小時》等一大批左翼電影登上銀幕。由田漢編劇的《三個摩登女性》也成為這一左翼電影浪潮中引起轟動的作品。影片塑造了代表三種社會類型的典型女性形象:追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虞玉。沉溺于小資傷感和絕望情緒的陳若英以及積極投身于勞動大眾爭取生存和自由斗爭的周淑貞。影片以鮮明的立場對前二人進行了批判,對周淑貞自食其力、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進行了肯定和歌頌。
1934年蔡楚生導演的電影《新女性》繼續沿著左翼電影的路往前走。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在民族危難和現代化轉
型過程中,個性解放、婦女解放與革命話語之間的糾結。鋼琴、小說、旗袍、舞會,構成了韋明(阮玲玉扮演)這位追求個性解放的“五四”新女性的生活舞臺。左翼電影通過塑造周淑貞、韋明這些人物形象。開始自覺地把自己的現代性追求與國家、民族以及人的現代化密切地聯系在了一起。
五、費穆:從戲劇的“電影化”
到中國經典電影的創造
在中國早期電影人中。費穆頗有點與其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比如說:為什么他在1948年拍攝了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生死恨》?為什么他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拍攝了《小城之春》?這些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費穆曾談及對京劇的電影化改造:“拍‘京戲時,導演人心中長存一種寫中國畫的創作心情——這是最難的一點。”由此可見,費穆在戲劇的“電影化”方面的努力,是為中國電影的現代化尋找某些獨特的元素。
事實上,從早期的《城市之夜》《人生》《香雪海》殘存的電影本事,到今天尚能看到的《天倫》《狼山喋血記》及《聯華交響曲》之《春閨夢斷》,我們都能發現費穆的可貴探索。尤其是短片《春閨夢斷》,其先鋒性與實驗性至今令人感到震驚。有研究者甚至聯系費穆1928年看過的德國影片《卡里加里博士》,稱其為中國的表現主義電影。
費穆的經典之作《小城之春》,其中所創造的長鏡頭、話外音和詩一般的東方意境,更是充分反映出我國早期電影人對電影現代化的一種反思和超越。
盡管1949年以后,大陸學者圊于長期的政治偏見,沒有能及時發現費穆及其作品的價值,比如新中國最權威的電影史著作《中國電影發展史》就認為:上映于1948年9月的《小城之春》“反映了費穆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藝術家的兩重性及其軟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戰爭的偉大時代中心情的苦悶、矛盾、灰暗和消沉。”但是。藝術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偉大的作品不能簡單地以一種意識形態的尺度去肯定或否定。作為《中國電影發展史》著者之一的李少白先生在原書出版33年之后,看法已有了很大的變化,他認為:“《小城之春》的歷史價值在于:它對既有現代特征又有民族風格的中國電影,作了大膽超前的實驗和成就卓著的求索。具有一種先行性的開啟現代電影創作思維的歷史意義。因此。正像巴贊評價奧遜·威爾斯的那樣,費穆也‘有資格在為電影史慶功的凱旋門的顯赫地位刻上他的名字。”應該說,這種觀點是相當中肯的。
也許,導演費穆并沒有想過《小城之春》會成為中國電影不朽的經典,但是,從他早期的先鋒藝術探索,到后來的京劇電影實驗。多年的藝術體驗都凝結在這部電影中,自然而然成為了中國早期電影的一座高峰。
六、結語
從1905到1949年,中國電影篳路襤褸、曲折前行。無論是早期影戲、鴛鴦蝴蝶派、現代派、左翼電影。還是自稱“歐陸派”的費穆電影,盡管各流派背景和認識有很大差異,但他們的現代性觀念卻非意識形態論爭所能概括,而是呈現為君子的“和而不同”,共同為中國電影的現代化鋪路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