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人員的養(yǎng)老生活
顏曉菁
浯塘村改成了現(xiàn)在的晉江市小浯塘社區(qū),不過大伙兒還是習(xí)慣地說著“我們村里來我們村里去”。對于所謂的“社區(qū)”,大伙兒一直都不習(xí)慣。小浯塘社區(qū)黨支書在接待我們的時候,也像先前那樣自我介紹道:“我是這里的村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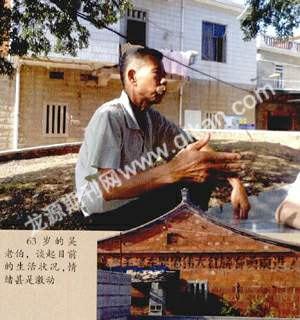
如今,浯塘村的村民可以算得上是城里人了。但在晉江這個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城鄉(xiāng)界線較為淡漠的新興城市里,似乎并不是什么令人興奮的事情。給我們帶路的晉江市勞動保障局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聊起,這里的人們,特別是老人家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被征地養(yǎng)老金可以再漲點。
好大一棵樹
小浯塘社區(qū)里,有一棵很大的榕樹。樹冠宛如一張撐開的大傘面,將樹下數(shù)百平米的空地置于一片陰涼之中。站在樹下,看著幾十米外白花花的太陽以及曬得有點滾燙的地面,身心一陣愜意。
閩南農(nóng)村,會說普通話的老人較為稀少。我們采訪的第一位63歲的吳姓老伯,曾經(jīng)擔(dān)任過兩屆村支書和兩屆副村長,算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一位老人。十幾年的村干部生涯,練就了他一口較為順暢的普通話表達(dá)方式,這給我們的采訪帶來了不少的便利。
初小文化的吳老伯早年當(dāng)過兵,因為表現(xiàn)好被推遲了兩年退伍,結(jié)果卻沒趕上退伍分配的好政策。吳老伯有個初中畢業(yè)的哥哥,后來進(jìn)城工作,現(xiàn)在退休金一個月2000多元。每逢說起這個事情,吳老伯心里頭既有幾分羨慕又有幾分感嘆:“當(dāng)年到我小學(xué)畢業(yè)的時候,家里面實在是籌不出錢供我念書了。沒辦法,只好去當(dāng)兵了。”
吳老伯家原來有兩畝多地,在2003年就被全部征完了。“一畝地一次性補償2萬多,不過,給兩個兒子辦完婚禮就差不多貼光了。”沒有了收入來源,吳老伯的心倒是慌過一陣子。“有地的時候,再不濟(jì),也能種點水稻、地瓜,糊個口總是沒問題的。”
2003年之后,靠著一點積蓄過日子總覺得不踏實的吳老伯做起了一點小生意。不過,兩年之后就停了下來。他說,老了,真是干不動了。
直到去年,吳老伯通過縣電視臺的宣傳和外村人的口耳相傳,才知曉了這個被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險。今年,吳老伯和老伴每人繳納了8120元錢之后,就開始每個月領(lǐng)起了280元的養(yǎng)老金,老人倆合起來領(lǐng)560元錢。吳老伯坦言:“這對于一些有抽煙喝酒習(xí)慣的人而言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想吃得多好也不可能,但是兩個人吃飯吃菜、保證溫飽是足夠的。”有了養(yǎng)老金之后,吳老伯說自己感覺每天睡得更踏實了,心更定了,人也更精神了點。而吳老伯的兩個兒子,退休還太早,只能選擇參加城鎮(zhèn)職工養(yǎng)老保險,但因他們只在附近的小工廠打零工,沒有被正式聘用,所以養(yǎng)老保險問題依然沒能得到落實。見記者沒有答話,吳老伯反倒安慰起我們來:“沒有關(guān)系,政策這么好,總有一天會解決的。”
問到現(xiàn)在感覺地是被征了好還是沒被征好呢,吳老伯想了想,頗有感觸地說:“很多事情真不是我們能預(yù)料的。早些年的時候,沒有想到有一天地會被征走;過了這么多年,也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領(lǐng)上養(yǎng)老金。”當(dāng)被告知晉江被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障是目前省內(nèi)的“楷模”的時候,吳老伯很自豪地笑著說:“是嘛,我們背靠大樹好乘涼啊。”
廢棄的老屋
地被征走了,農(nóng)民們搖身一變成了社區(qū)居民。但是這里的一切,依然保留著閩南農(nóng)村的風(fēng)格,家家戶戶,養(yǎng)雞養(yǎng)鴨養(yǎng)狗的不在少數(shù)。社區(qū)里的大榕樹下,一群鴨子躲在白色的旅行車下乘涼;一只大黃狗,正在離主人不遠(yuǎn)的地方酣然睡著大覺;廢棄的豬圈依然隨處可見……
許多年沒有整修過的蜿蜒小路,一直引著我們前行。這里的民房大多是三到五層的小樓房,底樓是一塊塊大青石砌起來的,門窗多為木制的。雖然年代大多比較久了,但因修葺得很工整,倒顯得有幾分古樸的氣息。二樓以上的房子大多數(shù)是后來添上去的,青磚紅磚相壘,鋁合金門窗,現(xiàn)代氣息較為濃厚。在許多新的民房中,時不時還混雜著許多廢棄的民房。往小浯塘社區(qū)的深處走去,這種廢棄的民房便會越來越多。由于語言上障礙,沿途問了村里的好幾個老人才知道,原來許多人的新家都是最近幾年地被征走了補償了一筆錢才建起來的,有的是家里老房子還可以住,舍不得青石屋子的冬暖夏涼,就修修底樓往上添新樓;也有一部分人的老屋實在住不得了,才舍棄老房子蓋了新樓。因為被廢棄不久,還沒想好要做什么用途,所以,廢棄的老房子隨處可見。
說話間,記者走進(jìn)了吳遠(yuǎn)太老人的家。這是一棟新房子,大廳非常寬敞。看得出來,這是一個殷實的小康之家。83歲的吳遠(yuǎn)太老人身體還相當(dāng)硬朗,知道記者的來意之后,他利索地從柜子里翻出被征地人員養(yǎng)老保險繳費記錄的小冊子給我們看,一臉的笑意。吳遠(yuǎn)太老人的兒子正好在家,他介紹道,地被征走后,附近的廠房就蓋起來了,村子里許多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似乎一下子全部找到了工作。

房子蓋好了、兒子有了工作、吳遠(yuǎn)太老兩口的養(yǎng)老問題又得到了初步的解決,吳遠(yuǎn)太老人說:“盼了一輩子,盼的不就是現(xiàn)在這樣的日子嗎?”當(dāng)被問及280元的養(yǎng)老金是否夠花時,老人家很滿足地說:“地沒了,有錢拿也可以。農(nóng)村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溫飽就夠了,別的就不奢求太多了。”
在一條小巷子的拐角處,記者看到了原浯塘村的老禮堂,紅色墻面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jìn)”的黑色大字依然清晰。而轉(zhuǎn)眼間,幾十年都過去了。
打牌的老人們
從進(jìn)了小浯塘社區(qū)開始,時不時地能看到一桌桌玩著四色牌的老人們。按說這打牌,算不上是什么好事。但在這個平日里只剩下老人和家畜的社區(qū)里,老人們?nèi)齼蓛删墼谝黄鸫蚺葡策^日子,倒是成了一幅幅美好的和諧景象。
老人們玩牌,多數(shù)是選了某個人家,茶水泡好、備好煙,悠閑地打。一位老人告訴記者:“年紀(jì)大了,什么也干不了,再不找點樂子那這日子真是沒法過了。但以前是每天靠積蓄過日子,牌桌散盡的時候回家會想著這要坐吃山空啊。現(xiàn)在好了,每個月領(lǐng)個280塊,我們也算是老有所養(yǎng)了。”說話間,老人家將幾張牌摸到了手,也不看,臉上就能表現(xiàn)出或喜或憂的表情。誰能想象,根根粗糙的手指,卻有著如此細(xì)膩的指上功夫,不得不讓人佩服。
見一位老人在旁邊蹲著看牌,記者便上前與他攀談起來。一問姓氏,發(fā)現(xiàn)又姓吳,再一問,才知曉,原來這個社區(qū)有一大半的人都姓吳。為了方便區(qū)別,我們稱這位吳大爺為老吳。老吳算是一個老牌迷,和我們說起他的打牌往事,原本有些羞澀的他,竟滔滔不絕起來。
“早年時候,秧苗得一顆顆地去地里插,耕田得拉著牛往地里一小塊一小塊地來,一年種上兩三季,每天累得倒頭就能大睡,只能是逢上下大雨不用下地的日子,才湊幾個人大伙來打牌消遣消遣。那時候大伙都不賭錢,輸?shù)娜司豌@桌底,倒是很有幾分樂趣。再后來,孩子們都長大了,外出工作了,生活壓力沒那么大了,許多人家開始種起了單季,農(nóng)活減少了一半,打牌的時間越來越多了,那時候的日子倒也逍遙。”
直到有一天,地被征走了,老吳徹底沒事做了,反倒在牌桌上不踏實起來:出來玩兩局就琢磨著要出去做點什么,總不能坐吃山空吧?那段日子,是老吳有生以來打牌打得最不舒坦的日子。這時候,旁邊一老人插話道:“他呀,直到今年才重新在牌桌前生龍活虎起來。”老吳不好意思地笑笑:“這每個月280的養(yǎng)老金,真是好啊,我的心都安了,這比靠兒子養(yǎng)老要來得實在多了。”
告別老吳,記者操小路出來,在一家小賣部旁邊的牌桌上,一位戴眼鏡的白發(fā)蒼蒼的老人,看見記者舉著相機(jī)在對鏡頭,大老遠(yuǎn)的用閩南話沖著我們吼。剛開始沒聽懂,問了旁邊的人才知道,他在沖著我們說:“來來,過來拍拍我們的生活,我現(xiàn)在好高興啊!”
采訪結(jié)束的時候,天色有些晚了。車子開出社區(qū),一家院子里的三角梅探出腦袋,朝我們招手。回頭間,那座紅色的老禮堂記錄著曾經(jīng)過往的農(nóng)村歲月歷歷在目,前方幾百米間的距離,中國馳名商標(biāo)才子襯衫的廣告牌清晰可見;而雅客食品的廠房,與村子隔著幾條小道,靜靜地,互相注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