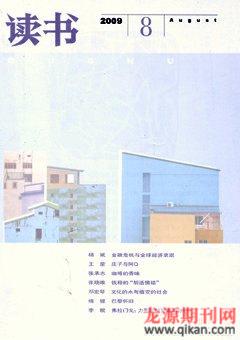組織的蛻變與危機中政府增長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滯脹,再到今天全球性經濟危機,幾乎每次危機都引發了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擴張。從有限政府到凱恩斯的大政府再到“幾乎沒有企業的哪個方面是政府不能干預”(喬治·弗雷德里克森語)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至于今天各國政府全面介入虛擬金融組織運行。人類社會致力于追求一個有限政府,一個最大程度不影響社會大眾自由生活的政府,但每一次的社會危機,不論大小,也不論是哪個領域,都會引發人們普遍認同的政府權力和責任的增長與擴張。政府權力整體上呈現為一個持續擴張的進程。政府在屢次的危機中被動提升權力,卻又屢次被新的危機瓦解。人們對社會經濟秩序的需求是否只能在政府增長過程中渡過?如果按照這一邏輯前行,應付危機與政府增長將是人類社會秩序演進的基本路徑。
每一次重大社會危機都會成為時代轉換的標志,引發人類認識上的歷史階段劃分,但對于歷史的認識而言,歷史階段的劃分并不是凸顯時代間的差異,也不是因為相互間存在不可超越的歷史斷層,相反,危機作為一個轉折點往往成為我們理解和認識歷史連續性與整體性的關鍵所在。如果能夠準確把握每一次社會危機發生的機理,并將一系列社會危機歷時性串聯起來,不僅可能把握歷史的走向,更有可能理解社會秩序演進的邏輯。我們把每一次危機后的政府權力增長視為一種應急性的舉措,但是它卻往往成為下一時期社會整體治理方式的基本體現。這似乎表明政府增長存在路徑上的依賴。政府權力按照某種模式增長和運行并不是政府本身所能左右,政府增長只能算是一種政府角色的轉換,或者說政府增長其實表達的是政府在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中政府角色的演進。如果說政府增長是社會秩序演進的需求,那么理解政府增長應當從社會秩序演進的角度來把握。而社會秩序這一宏大概念以及社會秩序演進這樣的重大問題只能在人與社會組織的關系中被解讀。
人是一種組織化的動物。由于組織本身具有信仰、秩序與庇護的功能,人們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會成為組織的成員。當組織成為一種共同體并圍繞共同體目標行動時,組織對外的勢力擴張便展開了,伴隨組織的強大與組織間沖突不斷,人們需要對組織間的利益與權力進行協調與規約,公共權力就順勢產生了。作為公共權力的政府權力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開始發揮作用。組織愈強大,對外擴張的要求越大,政府權力也就必然隨之增長,而且,組織間關系愈復雜,政府的責任也就越多,政府權力也就隨之不斷擴張。在這一意義上,政府增長是作為公共權力的增長,而且政府權力必然是作為社會組織權力(權利)增長的體現者。在現代社會的成長過程中,社會組織的理性和效率不斷降低權力和政治在社會治理和社會整合中的重要性,并使大量財富在組織中得到合法有效的利用,但不斷社會化的組織又成為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擴張的基礎,可以說社會組織的發展一方面削弱了政府權力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強化了政府履行公共權力職能的重要性。在政府權力“削弱”與“強化”的雙向同步走向中,恰恰體現了政府增長與社會組織的內在關聯,體現了政府增長與社會秩序演進的內在關聯。
組織的蛻變與政府增長
人們對現代社會組織的認識基于斯密對社會分工的論述。但在斯密這位奠定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基礎的思想家那里,經濟組織仍是一種簡單雇傭勞動關系。他所談及的經濟組織基本上都是手工水平的簡單加工組織,這一時期組織的簡單性使其缺乏權力性和對資本、資源的占有性,組織與市場幾乎構成一個統一的聯合體。正如德姆塞茨所描述的這一時期經濟組織是“完全分散化模式”,“完全分散化沒有給任何權威和控制的實行留有活動空間,尤其是沒有給企業提供任何理論基礎”(《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緯度》)。但大工業的推進使自由資本主義成為一個“特別的插曲”,自由市場競爭導致經濟組織迅速向規模方向靠攏。對權力和資源的占有越來越成為經濟組織輕而易舉從自由市場中獲取利益的奮斗方向。于是,規模經濟組織或企業本身的控制機制和權威開始在自由市場中凸顯出來,而建立在自由價格基礎上的自由市場則因為低效被規模經濟組織逐步拋棄。現代企業的概念在這一基礎上真正形成。
隨著工業化和專業化企業組織的不斷壯大,自由市場逐漸退化為工業化經濟組織追求利潤的基礎和工具。經濟組織在對資本與效率的追求中,不斷在機器的幫助下延伸產業鏈條,努力使自身成為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以支配整個行業,并使自身凌駕于自由市場之上。組織化資本主義的迅速興起本質上是專業化的規模經濟組織相對于完全分散化經濟組織的勝利,這一組織形式演化的重大成果便是現代企業制度的興起。規模經濟組織對自身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取代了對整個市場經濟效率最大化的追求。經濟組織與自由市場機制逐步分離,進而走向對立,最終引發競爭的失衡和經濟過程的中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從完全分散化的經濟組織到專業化的規模經濟組織,組織在不斷的蛻變中升級,這一過程也是一個組織由無權威轉向依賴權威生存的過程。因而也造就了政府權力的增長,以專業化經濟權力為主導的政治競爭和大量行業化的產業政策滋生,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結合起來。但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使政府的經濟政策由產業政策或對某一專業化經濟組織培植和控制轉向對國家整體的宏觀經濟調控,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整體均衡發展。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正是在這一邏輯基礎上興起的。凱恩斯宏觀控制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依靠單一產業或行業控制不能解決的問題,推進了戰后西方的經濟復蘇。凱恩斯主義推進了政府規模的急劇膨脹,并沒有擺脫傳統專業化、產業化的經濟組織對整個經濟秩序的影響,而是依賴它們進行綜合協調。但是,經濟組織形式并沒有按大政府的要求沿著其固有的方向發展,而是隨著不斷推進的產業革命日趨走向分散化和社會化。經濟組織逐漸擺脫專業化和產業化的劃分,組織與組織、組織與社會的邊界日益模糊,組織日益社會化。而依托傳統專業化和產業化為政策依據的凱恩斯主義必然因此失去其原有意義。急劇膨脹的政府在迅速社會化的經濟組織中不僅不能發揮宏觀調控功能,而且在組織社會化的進程中逐步失去其自主性能力。政府越來越陷入價值規律指導下的經濟波動,既不能消除積累過程的周期性紊亂,也不能有效控制替代性危機,從而導致行政行為強化經濟危機。
擺脫這種局面需要政府從經濟過程中抽身,讓大量的權力和財富在組織中得到合法有效利用,增強組織自身的治理能力。這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歐美各國推進的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很多人認為這是政府權力的收縮,是重歸有限政府理念的治道變革。而沒有認識到這是社會組織蛻變中政府在尋求新的治理方式,完全不是在限制政府權力,相反新的政府治理方式全面超越了有限政府理念,不斷追求更大的權力擴張,承擔更大范圍的社會責任。
傳統有限政府理念的確立基于以下三個條件,政府—市場的二元分離、專業化官僚行政以及對經濟最大化追求。伴隨社會組織擺脫傳統產業和行業的約束,社會整體結構扁平化,國家與社會重新融合,支撐有限政府理念的支柱性條件轟然倒下。各種社會經濟組織成為直接面對國家和政府的治理對象。政府的監管任務前所未有地擴大,帶動政府立法增多、公共機構增設、政府雇員增加,政府的權力范圍也空前擴張。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任何組織和企業的任何生產環節都是政府權力能夠觸及的范圍。如果凱恩斯主義的大政府是對有限政府理念的否定,新公共行政則不是對其簡單的否定,而是實現了理論與現實的雙重超越。
組織的虛擬化與新一輪危機
組織的高度社會化以及組織與社會邊界模糊,使組織構成方式不斷脫離傳統強調分工和集權的組織形式,由科層等級轉向自由契約組合。社會化意義上的自由契約,不再是對權利的轉讓、占有和買賣,而是一種平等協作。使用權的讓渡是程度問題,而授予權利的界定是締約問題。個人與企業的契約因此便呈現一定意義上的主動性,投入品所有者可以將投入品一次性轉讓,也可以出租,也可以參與專業化協作,還可以多方面進行合作。如果說使用權的讓渡和價格信息的傳遞僅僅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投入品所有者就有足夠的理由與企業進行平等基礎上的協商,并簽訂契約。確立在平等與自由基礎上的契約,必然導致經濟組織構成形式多樣化、結構松散化。企業可能小到兩個投入者之間的關系,如果允許企業鏈條擴展,它又可以大到整個經濟生活。在這一意義上,組織與市場關系再度回歸“完全分散化經濟組織”時期的融合統一。
在自由契約下,經濟組織由對權威的依賴轉向對信用的依賴。組織本身對權力和權威的擺脫,使組織的成長空間空前擴大,組織構成方式在這一基礎上日趨自由和多樣化,并逐步向虛擬化的方向演變。組織可以沒有固定的結構,沒有層級和縱向集中,參與組織的各方邊界模糊,松散聯合,可能不存在正式的合同關系,而往往是“關系合同”。這種合同形式只提供一個行動和關系框架,對合同雙方真實關系留下一定的解釋空間。虛擬化組織具有應對外界的足夠靈活性,組織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賴合同雙方的信任、自覺性和較高的忠誠度,也就是說組織協作是基于信任和資源的共享。虛擬組織的產生使組織徹底實現了從依賴權威向依賴信用的生存方式轉變。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組織社會化過程中,政府監管權力的急速推進往往針對的是實體經濟組織,而對剛剛出現的虛擬性組織缺乏應有的重視和應變措施,這一方面促使虛擬組織擁有更加自由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也導致努力規避政府監管的實體經濟組織迅速向虛擬組織的運作方式靠攏,不斷利用信用資源取代傳統經濟資源在市場競爭中的作用。對信用資源的獲取、占有甚至壟斷成為不斷虛擬化的實體經濟組織追求的目標。猶如當年壟斷組織對權力的追求一樣,虛擬組織對信用的追求也成為經濟組織最為便捷的成長路徑。對信用資源的占有量越大,組織越能夠超越自由契約中平等合約間的相互制約,越能夠更好地利用自由契約的運作機制獲取組織最大化的贏利空間和發展空間。組織社會化進程中自由契約這種普遍的經濟運作機制,越來越成為虛擬組織贏利和成長的手段與工具。虛擬組織對信用資源的操縱造成經濟組織與契約化運作的市場相分離,從而再現了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企業與市場的分離。最終造成原有經濟秩序的失衡和經濟過程的被迫中斷。
當實體經濟組織不斷與虛擬經濟組織聯系在一起,并依賴虛擬經濟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時,實體經濟的每一步發展都可能意味著在反向推助虛擬經濟膨脹。在持續的經濟循環過程中,虛擬經濟逐步占據主導地位。因為缺失虛擬經濟,實體經濟的運作就會陷入秩序空缺。這也就造就了今天各國政府不僅不對造成自由經濟秩序崩潰的虛擬經濟進行嚴厲懲罰,相反競相對其進行救助的原因。
從完全分散化的簡單雇傭組織到專業化的規模等級組織,到自由契約下的社會化組織,再到今天不斷發揮其巨大能量的虛擬組織,社會經濟組織在連續的自我否定中蛻變,組織的每一次蛻變都是一次新生和自身能量的重新聚積,造就了更大發展空間和更靈活的運作機制。每一次重大危機都是新生組織能量的釋放和對傳統秩序模式的顛覆,并引發政府治理模式的緊急應變和政府權力的一路高漲。組織越來越像一個怪物,以自身的蛻變來不斷玩弄市場、挑逗政府。對于這一次危機中的政府增長,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并不希望自己偏向社會主義,但站在讓信用回歸國家、回歸社會價值體系的角度,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又必須在這一選項之外不得不選擇讓政府權力增長的新路徑。
每一次危機過后的政府增長,都能展現出一個令人依賴的新秩序,但應當切記的是新的秩序形式不是政府造就的,而是組織蛻變和社會組織原則演化造就的,政府增長只是這種秩序的體現。
(《政府增長與秩序演進》,馬翠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八年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