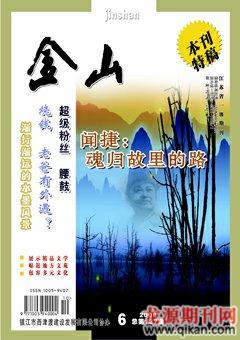漫議“改編”
花 原
近年來,有分量的原創影視作品不太多,其上乘之作更少。多的是改編作品,但優秀作品也不多。這恐怕與創作理想的缺失和浮躁心理的滋長有關。如果影視作品主要追求的是“票房”,那對于品質的追求就很難做到精益求精。高質量的作品,要深入生活,要獨立思考,要“板凳甘坐十年冷”,這哪里能趕得上市場的行情呢?于是,經典名著的改編,就被認為是一條“捷徑”。荀子有言:“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應為‘八之誤)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如果拿這話來提醒少數改編者,應該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改編也是一種創作,也需要嚴肅認真的態度,也要有生活、有思想,也要耐得住寂寞。如果以為改編就可以輕松討巧,那最后恐怕就一定“吃力不討好”。所以我認為,改編者首先應該對名著有一種敬畏的心情,首先要認真細致地吃透原著之精神,領會原著之精妙所在,然后才能使再創作得以切實有效地進行。總而言之,就是首先要“尊重原著”。
“尊重原著”當然也不是將它奉若神明,絲毫動不得:倘如此也就不存在改編或改寫了。怎樣在不違背原著基本精神的基礎上,正確地選擇,精要地濃縮,適當地發揮,盡量掌握好方向和分寸呢?我們不妨看看魯迅先生的《鑄劍》。《鑄劍》是一篇小說,講的是眉間尺為父親干將復仇的故事。但它有所本,在《列異傳》和《搜神記》中,都有關于眉間尺故事的記載,然而只是梗概,所以說《鑄劍》實際上是一篇“改寫”的小說。在《鑄劍》中,簡約的概述變成了具體的描寫,包括一些生動的細節;其中作為仇恨化身的黑衣人形象,更融進了對現實社會的諷刺;又通過狼的形象,突顯了黑暗社會的吃人本質,渲染出一種陰冷恐怖的氣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是在尊重原作基本精神和主要情節的前提下發揮藝術想象的,這堪稱再創作的典范。
但我們現在的有些改編,實在是太自由、太隨意了。不僅故事情節可以大幅度地增減改變,不僅人物形象可以從根本上另行設計,甚至連原作的基本立意都可以公然偷換了。去年看了新版的《京華煙云》,我就想,這還能算是林語堂的作品嗎?這本被有些人譽為“現代《紅樓夢》”的長篇小說,其重要特點之一是蘊涵了豐富的中國文化,但在電視劇中,基本上只剩下一個故事情節的空殼子。幸而林語堂早已作古,連搖頭嘆氣的資格也沒有了。
最近又看了《傾城之戀》,倒是覺得改編得還不錯,原小說所留下的大片藝術空白,被改編者填充延展得具體而生動。更難得的是,從時代背景的再現,主要演員的表演,到張愛玲敘事風格的模擬,都大體符合我們讀其小說時的感覺。這就很不容易了。但劇中關于白流蘇和白寶絡參與抗日活動的那些情節,就實在讓我感到匪夷所思了。本來,改編的《傾城之戀》比之原作,從思想內容上來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許多對于當時社會現實的批判了。當年傅雷評論《傾城之戀》時說:“一個‘破落戶家的離婚女兒,被窮酸兄嫂的冷嘲熱諷攆出母家,跟一個飽經世故,狡猾清刮的老留學生談戀愛。正要陷在泥淖里時,一件突然震動世界的變故把她救了出來,得到一個平凡的歸宿。……因為是傳奇,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因為是傳奇,情欲沒有驚心動魄的表現。幾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盡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游戲,盡管那么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練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很顯然,大家看了電視版的《傾城之戀》,就不是這樣的感覺了。這就是一種提高,一種升華,一種相當程度上的脫胎換骨;但至少它還是有基礎,有根據,可以算一種滲進時代精神的“為我所用”。即使張愛玲看了,恐怕也能會意一笑的吧!但要說到加進抗日的內容,張愛玲恐怕是要愧疚汗顏的。她寫《傾城之戀》時是在1943年的淪陷區上海,而且次年便和漢奸胡蘭成結了婚。于青曾經評論道:“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一段婚姻,恰發生于國土淪陷的亂世。正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婚姻,是成就于一個城市的毀滅一樣。”咱們現在賦予《傾城之戀》如此昂揚的政治傾向,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改編名著經典確實應該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記得當年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印象頗佳,就是覺得它比較忠實地傳達了原著的精神。但到了80回以后的部分,劇本完全采用某紅學家的意見,生編硬造,也一樣成為續貂之狗尾。至于同樣性質的另一部關于曹雪芹的電視劇,那簡直就不能看了。
小時候看過前蘇聯不少根據名著改編的電影,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白夜》,果戈里的《木木》,契訶夫的《帶閣樓的房子》,高爾基的《母親》,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等,具體情況雖已記不清,但總的印象是,無論改短還是改長,都比較忠實于原著,同時又在電影藝術方面有所發展,有所創新。當然其它國家也有不少成功的改編作品,為什么不好好向人家學習呢?
昨天晚上從電視上看了電影《畫皮》,看得出在立意構思、人物設計和情節安排上都下了不少功夫,演員也可以說相當賣力。但我再看看原著,就覺得電影與《聊齋》優秀作品的風格相去甚遠:蒲松齡雖寫鬼狐而富含人情味,雖寫神怪而頗具藝術美;可電影卻把一個本來很“俗”的世情故事,夸張成一個遠離人間煙火的傳奇,多少有點故作高深而又缺少生動的細節,反而使觀眾產生一種疏離感,也很難為之感動。不過這已是中上等的作品,至于平時常在一些省級電視臺播放的聊齋電視片,則又等而下之了。
我這樣指點熒屏大發議論,往往使我的“第一聽眾”大不以為然,但有時又好像覺得我有點道理,甚至會攛掇著說:“你自己改編一個嘛!”此言一出,我便頓時泄了氣,只好灰心喪氣地說:“我這就叫眼高手低。我這輩子就只能‘評了,下輩子再‘寫吧。”而且我心里還在想,我這“眼”恐怕也未必算“高”,但那些劇作家和導演們,為什么不能“眼”高一點,“手”也高一點,為什么不能去“法乎其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