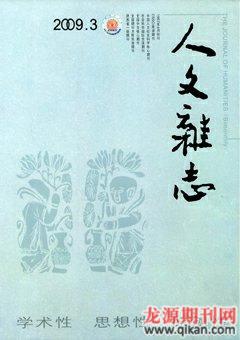國家的三面相與政黨——國家關系的三重邏輯
李 華
內容提要 建立民主、獨立與有效的現代國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目標和基本內容,探討現代國家建設問題的路徑是多樣的,本文基于對作為當然的自變量與應變量而存在于我們分析邏輯中的“國家”以及既有政黨—國家關系①論述的反思,提出國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現出的作為“共同體”、“權威體”和“界際的獨立體”等面相及其特質與意義,并論述了基于國家這三種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黨—國家關系邏輯,進而以全新的視角全面、深入審視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以及政黨—國家關系等基本問題。
關鍵詞 國家 國家面相 政黨—國家關系
〔中圖分類號〕D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9)03-0058-06おお
一、反思作為當然的自變量與因變量さ摹骯家”:問題的提出
人類社會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展現形態之一就是國家的出現,無論就中國傳統政治抑或現代政治的形態與邏輯來說,對于國家問題的探討是把握其特質及發展理路最重要的分析路徑,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更是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發展訴求中的最強音。早至陳獨秀和杜亞泉等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國家”語境下對于政治的個人觀的討論時,就揭示了“五四”時期三種不同的政治個人圖像:即作為“國民”的個人、與“國家”劃界的個人和作為材料的個人。
②可以看到,存在于國家圖式中的個人所具有的這些不同圖像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近代國家所具有的不同面相,就本文來說,存系于近代國家作為“共同體”及“界際的獨立體”中的個人與其“國民”的稱謂相契合,而受制于作為“權威體”而存在的現實國家中的個人則與其“公民”稱謂相統一。國家具有不同的面相,作為其受眾和組成者、維系者的個人因而被相應地賦予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個人在國家臨在的場合所秉有的身份、角色以及這種身份、角色在時空背景下的轉換正彰顯著國家的諸面。國家所展現出來的諸種面相與其說展現了國家本質的多元性,倒不如說是政治邏輯于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在國家身上的彰顯。因此,對于國家諸種面相的探討不僅是我們認識國家的重要方式,更是我們分析人類社會政治邏輯的基本視角。此外,國家展示方式的多態性也提醒我們,當我們分析國家以及運用國家作為我們的分析變量時,必須拋棄那種將國家當然地認為是——如我們對其簡單稱謂那樣——在人類社會政治運作和發展中作為完全一致性的、單一性的形象而存在的簡單做法,也必須深刻省思我們那種不加審視和分辨地將國家生硬地嵌入我們的分析邏輯時,以工具性的存在和價值來理解和把握國家,將國家當作無需加以界定和分析的、秉有當然價值和意義的黑箱式分析變量的做法。此外,就政黨—國家關系來說,基于國家的不同面相而形成的政黨—國家關系因而也是有著多重邏輯的,當我們以國家的不同面相的視角來分別審視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政黨—國家關系時,亦會得出對于政黨—國家關系更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① 本文中的“政黨—國家關系”如不作特別說明,僅指中國共產黨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② 參見顧紅亮:《“民族國家”語境中的個人圖像》,《浙江學刊》2007年第1期。
二、“共同體”: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國家面相
無論是就日常認知抑或學理探究,我們均無法找到統一性的完整實體作為我們認識和理解國家時的對象,國家也并非時刻毋庸置疑地以一種實體性的存在標示其作用和意義。國家的存在、意義以及作用的發揮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們在理念中對于國家的設想和建構,國家無論是在我們的政治認知抑或在其臨在的方式中都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我們理念的提升和創造,經由這一提升和創造的國家是一種無法與現實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任何關系加以比對的標識理念與信仰的政治體。在這一意義上,國家或被意識形態建構成為一個囊括所有公民的理想中的整體,或在有一般意識的公民政治認知中成為一個神圣而又形象的共同體。國家的這種形象在我們的政治話語中可以用“祖國”一詞加以概括,祖國是國家臨世的一種面相,亦是國家的升華。
可以看到,作為共同體而存在的國家不僅揭示出多面國家的一種面相,更彰顯出國家產生和存在的更深層次的價值意義。正如牟宗三先
生對于自由所進行的論述那樣:“我們不能只從結果上,只從散開的諸權利上割截地看自由,這樣倒更看不清楚;而上提以觀人之覺醒奮斗,貫通地看自由,這樣倒更清楚。…… 這很明顯,自由必須通著道德理性與人的自覺,這里并沒有什么抽象玄虛,也沒有什么易于引起爭辯的形而上學的理論,這是實踐上的定然事實,各種權利只是它的客觀化的成果而在民主政體中由憲法以保障之。”
②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2-53、47頁。)對于自由的理解應該如此,我們對于國家的理解復當如是。就國家的共同體面相來說,我們不能僅囿于那種對于“散開”的國家的認知和理解,我們需要一定意義上的“上提”,即將國家作為共同體而展現的面相所具有的普括性與超越性價值發掘出來,因為只有通過這一層面,國家中每個人的自覺、每個人的主體性才能夠與國家作為真正意義上共同體的存在和意義發生最為深刻的勾連。“國家是因人民有政治上的獨立個性而在一制度下(政權的與治權的)重新組織起來的一個統一體,故亦是理性之架構表現。假若是靠武力硬打起來的統一,人民無其政治上的獨立個性,對之無所事事,而只是個被動,則便不得名曰國家,而其統一也是虛浮無實的統一”②。也正如黑格爾就東西方人對于上帝與法律的不同的服從方式的論述所要說明的那樣,這種服從究竟是基于我們主觀內部的體認抑或是基于當然的設想:“我們西方人所稱的‘上帝還沒有在東方的意識內實現,因為我們的‘上帝觀念含有靈魂的一種提高,到了超肉體的境界。在我們服從的時候,因為我們被規定要做的一切,因為一種內部的制裁所認準的,但是在東方就不是如此,‘法律在那里被看作是當然地、絕對地不錯的,而并沒有想到其中缺少著這種主觀的認準。東方人在法律中沒有認出他們自己的意志,卻認見了一種全然陌生的意志”〔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14頁。)。就國家的“共同體”面相這一層面來說,我們對于國家的認知和服從的前提在于國家對于全體組成者的有效代表,而這種認知和服從的最根本之意義則在于作為組成者的個人的自覺、獨立與國家的成長、繁榮是決然不可分割的。因而可以說,國家作為共同體而展現的面相彰顯了國家最為深刻的價值與意義,因為正是在這一層面,國家可以有效地為人們所共同接受和信仰,方可以作為全民意識與訴求最有效、最真實的體現。此外,就國家的組成者來說,無論政治現實中人們的地位與作用如何,在國家的這一面相中,每個人都是國家所不可或缺的主體,都是國家存在價值的最終體現,無論是政治社會化的導向抑或個人的政治體認都在這一層面上趨于將國家視作一個代表和展現所有參與者的完滿意義上的共同體。總言之,國家這一共同體面相的完滿化與國家中個體的理性自覺、主體性的權位可以說發生了最為深刻和直接的勾連,而正是這一勾連彰顯出國家及其組成者各自的和互相增益的意義與價值。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上述國家的這一面相及其意義應該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應該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國家這一共同體面相有陷入被過度神話和完滿化之虞,而當國家被不合時宜地賦予過多的價值屬性與理性精神時,其易淪為反個人和反自由的說辭與工具。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霍布斯的利維坦到盧梭的公意思想再到黑格爾的作為絕對理念最高展現形式的國家都在醉人的理想與令人憎惡的現實之間徘徊,飽受爭議與指責。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國家這一共同體面相毋庸置疑地昭示著國家的存在及價值與作為個體和整體而存在的人們的自覺意識與主體性之間直接、必然的關聯,或許國家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方能真正有效地彰顯其全民性特質。無論國家權力在現實中的歸屬如何,當國家以基于想象和理念的共同體面相臨世時,國家就立即被賦予了不能為任何個人和組織所隨意代表和剝奪的全民性,國家中的個人也因此具有不被隨意忽略和貶低的地位與價值。正如卡西爾教授對于黑格爾的國家學說雖頗有詬責,但是他依舊指出:“然而,黑格爾的學說和現代的極權主義國家的理論之間有一點是明顯不同的。…… 在體現于國家(它被看作精神,因而是一種充沛的力量)的客觀精神之上,存在著一個更高的階段。它絕不應該企圖壓迫其他的客觀力量,而是應該承認它們,給它們自由。…… 甚至在他的《論德國憲法》的論文里,黑格爾就已經強調國家力量的強大不在于其居民和戰士的眾多,也不在于它的規模。憲法的保證毋寧說是在于那‘賴以構成憲法的民族的內在精神和歷史。對黑格爾來說,要使這種內在的精神從屬于一個政黨的意志或一個個人領袖的意志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上,他會駁斥和憎厭現代‘極權主義的國家觀。…… 黑格爾能夠對國家進行吹捧和頌揚,他甚至能夠神話它;然而,在黑格爾國家權力的理想化和現代極權主義體系的偶像化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明確無誤的區別”(注:〔德〕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334-336頁。)。更進一步地說,無論是我們現實的政治設計抑或我們的學術探究,都是需要有某種超越性的和本體性的追求的,個人、國家和民族應當于現實中堅守,但更應有某種能得到不斷反思的深刻價值和信念的引導和推動,也就是說:“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在其組織上說,一個‘定常之有是不可少的。”(注: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頁。)也正如黑格爾論述形而上學時所給予我們的啟示那樣:“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注:〔德〕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1、2頁。)
就黨與共同體面相臨世的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說,正如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能以自己的機構和意志來替代國家的機構和意志那樣,作為領導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以共同體面相臨世的國家的領導亦非一種替代性的領導,而是一種配合性的領導,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先進性特質并不能完全保證乃至替代以共同體面相臨世的國家自己所應當秉有的那種全民性、超越性價值的有效實現。就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來說,黨先進性特質的保有和歷史任務實現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有效確保作為共同體面相而臨世的國家實現其應有的那種全民性與超越性價值,作為共同體面相而臨世的國家所應有的意義和價值的有效實現是衡量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成果的重要標志,亦是衡量政黨—國家關系中黨的領導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標尺。因而可以看到,這一層面的政黨—國家關系可以說彰顯了政黨—國家關系最為深刻的邏輯,彰顯出黨與國家之間的深刻關聯與區分,而這一層面的關聯與區分是我們審視和探討政黨—國家關系時所必須明確的,后述作為權威體和作為界際的獨立體之面相而展現的國家與黨的關系最為深刻的理論和價值的肇源就是以共同體面相臨世的國家與黨之間此一深刻的關聯。
三、權威體:作為現實權力そ峁固逑刀展現的國家面相
國家在政治社會發展歷史與現實中,不僅以前述的那種共同體面相臨世,更以一個權威體面相而展現,即我們所言的國家,不僅完滿地和鮮明地存系于我們的想象和理念中,更是切實地存在于政治社會現實之中,并發揮著至為重要的主導作用。國家作為權威體的面相是我們在政治話語及政治生活中所描述的和所關注的最多的對象之一,如果說國家的共同體面相確切地標識了國家與政府之間的差異的話,那么作為權威體而面世的國家則與我們一般所說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緊密勾連的。以共同體臨世的國家先天性地具有了某種整合性和統一性,我們雖然可以簡單地以“國家”或“祖國”一詞來概括這一意義上的國家面相,但是這一單個詞匯并不能掩蓋以權威體面相臨世的國家本身所具有的那種內部的多層級和因此而存在的內在張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共同體面相展現的國家較之于以權威體面相展現的國家具有更強的統一性和整合性,這也就是為什么國家整合和統一的訴求往往肇發于作為權威體的國家面相而其實現則往往要求助于作為共同體的國家面相。正如羅茲曼在論述新中國成立后的全國通訊和省級政府時所指出的那樣:“各種級別上的影響力的變動是由許多地方的和下層基礎內在的原因引起的,不都是由北京的決定或《人民日報》的社論所引起的。光參引這家全國性報紙和其他一些類似的黨報,就會模糊中國各地政治生活中持續存在著的相當程度的多樣性,盡管這些傳播媒介后來多少也減弱了這種多樣性。”(注:〔美〕吉爾伯托—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8頁。)
當然,國家作為權威體而存在的形象和所發揮的作用是國家最基本的角色和功能。這一意義上的國家通過對權威的有效壟斷,從而進行資源的有效汲取與配置,進而保有社會秩序和發展。可以看到,無論是我們所探討的國家內部權力體系問題還是對于政黨—國家關系、國家—社會關系的探討等都是主要針對以這一面相展現的國家而展開的。其中,國家與社會關系決定了國家權力的最基本來源與最終標的,而國家本身的權力關系主要涉及橫向和縱向的國家權力體系的確立與運作,例如中央、地方各級國家權力的確立與行使以及縱向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等,此外,國家與政黨的關系主要涉及政黨的角色及功能與組織化、制度化的國家權力體系之間的關系。如果說以共同體面相而出現的國家需要我們以統一性乃至超越性的視角來加以審視的話,那么我們對于以權威體面相展現的國家的審視就必須基于現實和回歸現實,必須明確其內部的權力結構體系、內部的層級關系乃至內部的張力,在探討這一面相的國家與其他諸如政黨、社會之間的關系時,這種“散開”的和現實性的審視視角是必需的,因而,當我們在國家作為權威體面相的層面審視國家本身抑或以其作為我們分析的自變量或應變量時,應切忌對于這一面相國家的簡單化和單一化。
就國家作為權威體而展現的面相來說,政黨—國家關系主要涉及黨的地位和作用與國家權力體系之間的關系問題,一般我們對于政黨—國家關系的探討主要是基于這一層面而展開的,如果說前述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一重邏輯主要涉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角色與以共同體面相臨世的國家之間的關系的話,那么這一層面中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二重邏輯則主要涉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以權威體面世的國家中的角色定位問題。可以看到,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一重邏輯主要是于理念和價值層面展開的,而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二重邏輯則主要在權力關系層面、制度層面展開,因而較之于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一重邏輯,政黨—國家關系的第二重邏輯更為直觀、也更為現實。
眾所周知,國家——或者更為準確地說——現代民族國家是人類政治發展中所出現的最為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權威體,政黨無論就其性質還是作用來說與國家都是不同的,二者的性質與功能的差異決定了二者不可相互替代。在中國的政治邏輯中,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互動的關系在多大程度上與政黨—國家關系相關聯,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有效處理以及作為政治生活中平等的主體而出現的公民與作為階級、階層和團體存在著的人民各自的劃分及其各自與國家、政黨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等問題是當國家作為一個權威體面相展現并發揮作用時我們探討政黨—國家關系問題所必須加以梳理和明確的。
四、界際的獨立體:ぷ允佑詮際體系中的國家面相
國家的第三種面相可以稱之為“界際的獨立體”,也就是說,在政治生活中,國家不僅以前述的共同體和權威體等面相而展現出來,亦是以自視于國際體系中的界際的獨立體面相臨世并發揮作用的,國家的這一面相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有其特殊的意義。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這里并非是從國際關系與國際政治意義上對國家間關系進行探討,而是縱觀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歷史脈絡,論述中國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超大型文化體到一個自視于國際體系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政治邏輯。國家的這一種面相與我們的政治話語中的“中國”是相對應的,在國際層面,中國越來越展現為一個界際的獨立體,逐漸自視于國際體系之中,在國際體系中,國家試圖以及在事實上也逐漸以獨立的參與者面相展現出來,國家因而獲得了上述兩種面相之外的第三種面相。
傳統中國基于文化理念與現實認知的原因,是作為一個超大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而存在的,這個文化共同體以自我為中心向外進行差序性輻射,進而形成了華夷之別,地理上距中國文化中心的遠近就成為標示文明程度的尺度,正如吉登斯在論述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區別時所指出的那樣:“帝國形態不管存在多長時間,都不能像當今的民族—國家那樣,毗鄰于其他具備同等力量的領土。凡是毗鄰其邊陲的國家都是小國,而且一般說來,統治集團也會把它們歸入所有其他的野蠻民族。換言之,帝國在自己的版圖之內具有普遍化的特征。只有伴隨民族—國家的產生,‘國際這一術語才開始具有充分的含義,這是因為民族—國家具有嚴格的、相互區分開來的特征,因而相對于‘外部的多重關系,其‘內部關系也便具有非常特別的形態。”(注:〔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譯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210頁。)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的入侵和中國固有自我認知模式的全面轉變,中國逐漸走上了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道路。
新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就決定了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既沒有完全脫離人類政治發展的一般路徑,但卻形成了自己的內在理路。全新的中國雖然拋卻了傳統中國固有的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的認知定位,漸而成為中心多元化的國際體系中的一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中國在一段時期內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元而存在的,因而國際、國內政治環境以及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新中國當時的自我認知和定位,使得新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所展現的界際的獨立體面相有其獨有的特征,而這一獨有特征不僅是我們探討新中國的界際的獨立體面相時所必須明確的,更是我們探討新中國建立后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理路及政黨—國家關系等問題的重要視角。湯森和沃馬克對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進行的論述中就指出了這一自我認知與定位的特質與發展歷程:“如果認為中國已經加入‘國際俱樂部,那是有悖于中國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這種形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主導了中國人自己和外國人的看法。在這些年里,中國越來越表現出是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者,是世界權力結構的自覺反對者。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取代西方和蘇聯發展模式的一種新選擇,中國內部毛澤東主義的崛起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這里不準備評價毛澤東主義模式的特異性,但具有實質意義的是應注意到,中國人自己和許多外國觀察者已經習慣于把中國看作是超級大國世界的反對者和明確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現存秩序挑戰而不是遷就它的追求激進變革的力量。這種形象使現任中國領導人的立場復雜化了,自毛澤東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們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以追求國家安全和獲得繼續發展所必須的國外貿易、技術和資本。”(注:〔美〕詹姆斯-R-湯森、布蘭德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所以從國際層面并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理念來看,新中國雖然拋棄了傳統社會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的定位,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其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面相是特殊的,從傳統到現代,國家的第三種面相的轉換脈絡及其背后的邏輯并不是簡單的和線性的,如前所述,國家界際獨立體面相的確立和展現歷程的特殊性正是我們有效探究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特點與發展歷程以及政黨—國家關系發展邏輯的重要視角。
改革開放后,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發生了雙重變化,而這種變化也最終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以及國家第三種面相的確立和特質。中國已經越來越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一元,中國的建設和發展與國際性的時空背景發生了最為深刻的關聯,國家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第三種面相因而也越來越明確,越來越獲致鮮明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就國家這一面相中的政黨—國家關系來看,中國共產黨政治理念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和自我定位,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新中國的建立,將中國從之前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轉變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而也正是共產黨所秉有的社會主義國內、國際理念決定了新中國很長一段時期內在國際體系中界際的獨立體面相與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參與者以及當時國際模式的反抗者面相之間徘徊與權衡。因而就國家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面相來說,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不僅決定了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自身邏輯,也決定了國家在國際時空背景中的自我認知與定位。因此可以說,黨不僅與以前述兩種面相而展現的國家發生重要的互動關系,也與以界際的獨立體面相而展現的國家發生關系,而政黨—國家關系的這種第三重邏輯更進一步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發展歷史與現實中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的角色、地位與作用,因而國家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第三種面相是我們探討國家建設問題和政黨—國家關系問題時所不能加以忽視的。
五、結語:國家的多面相與中國現代國家建設
可以看到,上述國家的三種面相之間并不是決然相分的,將國家這三種面相中的任一種抽拔出來并將其作為無論是傳統中國抑或現代中國的存在和展現形式都是片面的。只有當國家的上述三種面相能夠有效契合,即作為權威體而展現的國家能夠從作為共同體而展現的國家那里汲取相應的合法性認同和價值上的關懷時,當作為共同體的國家能夠在作為權威體存在的國家那里獲致強有力的制度化的整合度與能效時,當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國家能夠從作為共同體和權威體而展現的國家中汲取相應的整合性的認同和獨立性的國家能力時,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的路徑方可以有效地展開,而當上述國家的三種面相中的某些方面薄弱甚至缺失抑或國家三種面相之間沒有實現有效的契合與互動時,國家建設就會面臨相應問題,縱觀從中國傳統到近代直至現代,國家建設問題的提出以及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基于國家上述三種面相中某一方面的缺失抑或其內部張力所造成的,因而無論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問題抑或其所承載的中國政治邏輯的展開和發展都需要我們深刻和全面地省思國家的多面相及其關系問題。具體言之:
首先,作為共同體而展現的國家所造就的國家認同會有助于以權威體而展現的國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確立以及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國家于國際體系中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的確立。反之,以共同體而展現的國家如果過多地和盲目地受到意識形態宣傳的左右和引導,如果國家認同及其作為共同體的意義僅被片面化和工具化地運用,那么作為權威體和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展現的國家雖然可以在一段時期內實現有效的發展,但是有失卻其精神動力和價值關懷之虞,從而使得國家的持續發展失去最根本的后勁和保障。黑格爾的國家觀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在于:“黑格爾不僅談及國家的權力,而且也談及它的‘真理。他是‘強權出真理的極大敬慕者。然而,他并不把這種力量和純粹的自然力量相混淆。他很清楚地知道,僅僅物質財富和力量的增長,并不能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興旺的標準。”(注:〔德〕恩斯特-卡西爾:《國家的神話》,華夏出版社,2003年, 第335頁。)
其次,作為權威體而展現的國家是國家最顯著的也是最有效的面相。就作為權威體的國家來說,如果國家內部權力關系能夠有效梳理,國家能力能夠得到有效的培育,那么國家就能獲致更有效的合法性認同,國家的合法性認同最為堅實和有效的基礎是國家政治能效的有效實現和輸出,作為界際的獨立體的國家亦需要作為權威體的國家提供強大的實力支持,從而使得國家于國際體系中能有效保有其獨立自主的地位,有效謀求國家應屬的自身利益。
最后,就作為界際的獨立體而存在的國家來說,伴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國家這一面相也越發顯著和重要。當國家能夠合理、有效地融入國際體系中去,即作為界際的獨立體之面相能夠得到有效的重視和展現的話,那么作為共同體和作為權威體的國家就能夠獲致有效的環境與動力,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建設問題已僅非國內環境所造就和決定,而已越發獲致顯著的國際性特征。
總言之,對于國家諸面相的探討是我們審視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政黨—國家關系乃至中國整體政治社會發展邏輯的重要視角和路徑,這一視角和路徑所彰示的不僅是政治學研究的新路向,也彰顯了政治學研究的基本關懷與方法原則。オ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責任編輯:劉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