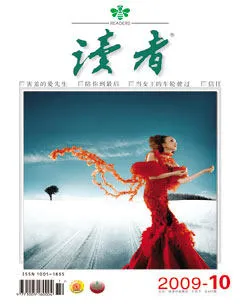其余的都是沉默
賈樟柯
我的老家山西汾陽(yáng)是一個(gè)縣城,地方不大,農(nóng)業(yè)氣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幫村里的同學(xué)收麥子。
人在這時(shí)候顯得異常渺小,在麥浪的包圍中,遠(yuǎn)遠(yuǎn)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個(gè)黑點(diǎn)。日落時(shí)分,努力直起彎曲太久的腰,一邊抹著汗,一邊把目光投向遠(yuǎn)處。遠(yuǎn)處的逆光中,柴油機(jī)廠的煙囪正高傲地冒著白煙。我就明白了為什么人們都爭(zhēng)著進(jìn)工廠當(dāng)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這是肺腑之言。那時(shí)候,工人雖然也是勞動(dòng)者,卻是和機(jī)器打交道,有技術(shù),吃供應(yīng),有勞保,還是“領(lǐng)導(dǎo)階級(jí)”。
縣里工廠不多,那時(shí)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機(jī)廠、一兩百人的機(jī)械廠已經(jīng)算是大廠了。20世紀(jì)70年代末,縣城里誰(shuí)家的孩子能進(jìn)到工廠里工作,對(duì)全家來(lái)說(shuō)都是一件榮耀的事情,因?yàn)檫@意味著每月有穩(wěn)定的工資,意味著暑期會(huì)發(fā)茶葉、白糖,冬天會(huì)有烤火費(fèi),也意味著家里人可以去工廠的浴室洗澡,每個(gè)月還發(fā)若干雙手套和幾條肥皂。而我們這些孩子,也可以拿著過(guò)期的票,跟著哥哥或姐姐混進(jìn)職工俱樂(lè)部去看《佐羅》。雖然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時(shí)可以順手扯一些棉紗,放在自行車坐墊下用來(lái)擦自行車,可以順手為家里磨幾個(gè)不銹鋼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為自家的電表順一卷兒保險(xiǎn)絲回來(lái)。
“以廠為家”的觀念讓大家變得公私不分,人們也樂(lè)在其中。廠里的福利房,將來(lái)鐵定不變的退休金,這不只是物質(zhì)好處,還是一個(gè)階級(jí)的內(nèi)心驕傲。
但,這個(gè)世界有什么是鐵定不變的呢?
我有幾個(gè)同學(xué)在高二那年,因?yàn)榭h柴油機(jī)廠招工,都輟學(xué)離開(kāi)學(xué)校,進(jìn)工廠當(dāng)了工人。那是80年代,一個(gè)學(xué)生能夠早日走入社會(huì),掙一份穩(wěn)定的工資,能夠進(jìn)到圍墻里頭,在有燈光籃球場(chǎng)的柴油機(jī)廠上班,真讓無(wú)數(shù)同學(xué)羨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還在北京讀書(shū)的時(shí)候,突然我的這些同學(xué)都下崗了。工廠在轉(zhuǎn)制,停工了,當(dāng)時(shí)只有二十五六歲的他們拿著一兩百塊錢(qián)的低保流落社會(huì),變成有渾身力氣但無(wú)事可做的人。
我自己沒(méi)有在工廠生活過(guò)一天,也沒(méi)有在體制里討過(guò)飯吃,但這種國(guó)有工廠凋敝所帶來(lái)的影響,工人從一個(gè)社會(huì)的領(lǐng)導(dǎo)階級(jí)被邊緣化到了四處打散工的境地,這種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夠理解。那個(gè)時(shí)候,從工廠下崗的同學(xué)對(duì)我說(shuō):“我們的境遇還不如農(nóng)民,農(nóng)民還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獲,播種時(shí)有收獲的希望。”危機(jī)之中的工人,或許真的就像《國(guó)際歌》里面唱的:我們一無(wú)所有。
我從事的這個(gè)行業(yè),最早出現(xiàn)在銀幕上的人物是勞動(dòng)者。這是一個(gè)雙重的偉大傳統(tǒng)。一方面,電影開(kāi)端于紀(jì)錄美學(xué);另一方面,人類第一次用電影攝影機(jī)面對(duì)我們真實(shí)的生存世界時(shí),就把焦點(diǎn)對(duì)準(zhǔn)了工人,對(duì)準(zhǔn)了普通勞動(dòng)者。
2000年前后,我特別想拍一部關(guān)于國(guó)有工廠、關(guān)于中國(guó)社會(huì)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關(guān)于轉(zhuǎn)型之中有關(guān)工人處境的電影。我寫(xiě)了一個(gè)劇本,名字就叫“工廠的大門(mén)”。這個(gè)劇本寫(xiě)兩個(gè)年輕人,同一年入廠,在同一個(gè)師傅手下干活,同一年成為勞模,也同一年戀愛(ài),幾乎前后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崗,同一年在宿舍里面無(wú)所事事、打麻將、酗酒。孩子漸漸地大了,兩個(gè)家庭決定一起去做生意。他們?cè)谑袌?chǎng)里面擺了一個(gè)服裝攤,一起早出晚歸經(jīng)營(yíng)這個(gè)小小的生意。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因?yàn)殄X(qián)的問(wèn)題,兩個(gè)原本和睦的家庭開(kāi)始有了猜忌。劇本寫(xiě)完之后,我得意了幾天。但是冷靜一想,覺(jué)得這部電影的主題,除了社會(huì)層面的問(wèn)題,諸如工人生活困頓之外,還有什么更多的東西嗎?我覺(jué)得工人這樣的群體,他們?cè)隗w制里面的生存經(jīng)驗(yàn)一定會(huì)有更多的可能性。這個(gè)劇本被我鎖在抽屜里,一直沒(méi)有拿出來(lái)。
2006年底,有一天新聞里講:成都有一家擁有3萬(wàn)工人、10萬(wàn)家屬的工廠“成發(fā)集團(tuán)”(又名“420廠”),將土地轉(zhuǎn)讓給了“華潤(rùn)置地”,一年之后,整座承載了3萬(wàn)職工、10萬(wàn)家屬生活記憶的工廠將會(huì)像彈煙灰一樣,灰飛煙滅,而一座現(xiàn)代化的樓盤(pán)將拔地而起。從國(guó)有保密工廠到商業(yè)樓盤(pán)的巨大變遷,呈現(xiàn)出了土地的命運(yùn),而無(wú)數(shù)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記憶呢?這些記憶將于何處安放呢?
這條新聞提示了我,新中國(guó)50年的工業(yè)記憶需要我們?nèi)ッ鎸?duì)。曾經(jīng)為了讓國(guó)家富強(qiáng)、個(gè)人幸福而選擇了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但50年來(lái)我們?yōu)檫@個(gè)試驗(yàn)而付出的代價(jià)是什么?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尋找自我的無(wú)數(shù)個(gè)個(gè)體,浮現(xiàn)在這條新聞背后。我一下子感到這是一個(gè)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從集體到個(gè)人,這是一個(gè)關(guān)于體制的故事,是一個(gè)關(guān)于全體中國(guó)人集體記憶的故事。我毫不猶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這家工廠周圍,決定拍攝一部新的電影。
到了工廠所在地草橋子,在420廠邊徘徊的時(shí)候,我看不到任何的驚心動(dòng)魄。在冰冷的水泥筑就的二環(huán)路旁邊,一邊是圍墻里面依然需要檢查工作證才能出入的廠區(qū),另一邊卻是世俗的場(chǎng)景。一排排6層居民樓構(gòu)成的工人宿舍區(qū)里人來(lái)人往,灰色的6層樓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鋪。到下午3點(diǎn)以后,陽(yáng)光漸漸變得溫和,宿舍區(qū)寬闊的街道上人頭攢動(dòng),那些40多歲不算老也不算年輕的人,和那些滿頭白發(fā)的老人混雜在一起,坐在路邊開(kāi)始打麻將,仿佛周圍發(fā)生的一切都與他們無(wú)關(guān)。這些曾經(jīng)握著螺絲刀的手,這些曾經(jīng)目不轉(zhuǎn)睛地凝視著車床的眼睛,這些曾經(jīng)出入于圖書(shū)館、實(shí)驗(yàn)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頭,呼嘯牌場(chǎng)。
我在這里面穿行,像穿行在一個(gè)靜止的世界。不遠(yuǎn)處的市中心燈火輝煌,各種各樣的品牌店拔地而起,而在宿舍區(qū),這里牌桌上的輸贏只在幾塊錢(qián)。當(dāng)夜幕降臨,人們各自回到家,我想這塊安靜的社區(qū)里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靜。
我決定拍一部紀(jì)錄片,去接近這些師傅的生活,去了解他們埋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話語(yǔ)。在《成都商報(bào)》的幫助下,我們連登了幾天廣告,尋找愿意講述工廠經(jīng)驗(yàn)的工人。某一個(gè)下午,我自己去接熱線,當(dāng)約定的時(shí)間到來(lái)的時(shí)候,那幾部紅色的電話機(jī)突然鈴聲四起,我在慌亂中一個(gè)個(gè)地接起。很多電話剛剛接通,那邊沒(méi)說(shuō)幾句話已經(jīng)哽咽不止。聽(tīng)筒這邊,我分明還能聽(tīng)到對(duì)方是在一個(gè)寂靜的房子里面講話。我能夠想象,或許他的愛(ài)人正在外面打麻將,或許他的兒女這時(shí)候正在課堂上為高考拼搏。而他——一個(gè)孤獨(dú)的中年人,坐在自己的房間里,拿起電話撥某個(gè)號(hào)碼的時(shí)候,才愿意講述他長(zhǎng)久以來(lái)不能說(shuō)出的心事。
這些工人師傅和更多的中國(guó)工人一樣,他們離開(kāi)工廠,但還有一個(gè)家庭可以接納他們。每一個(gè)人在家庭里面都盡量地維護(hù)家庭的快樂(lè),特別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們從來(lái)沒(méi)有眉頭緊鎖,從來(lái)沒(méi)有把自己的焦慮跟夜不能寐的壓力變成一種家庭氣氛。每一個(gè)家庭還都有餐桌邊的歡聲笑語(yǔ),人們?cè)谧h論電視劇的情節(jié)中度過(guò)一個(gè)又一個(gè)平靜的日子。而在無(wú)人的時(shí)刻,他們有了眼淚,他們有了無(wú)法說(shuō)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記好了這些想要講述的工人師傅的名字和聯(lián)系方法,然后開(kāi)始了采訪。
進(jìn)入工人師傅的家,仿佛回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幾乎所有家的裝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黃色的雙人床,立柜,沙發(fā),墻上交叉掛著的羽毛球拍和釘子上掛著的潔白的羽毛球……幾乎所有的物品都停留在80年代,唯一能夠提示當(dāng)代氣息的是孩子們的相片——那些穿著耐克、染著黃頭發(fā)的工人師傅的下一代,他們?cè)谡掌袥_著我們微笑,無(wú)憂無(wú)慮。
當(dāng)攝影機(jī)面對(duì)這些工人師傅的時(shí)候,往往他們激情澎湃地講述的都是關(guān)于別人的事。我不停地追問(wèn):“您自己那個(gè)時(shí)候在做什么?”幾乎所有的工人師傅都說(shuō):“你不要問(wèn)我的故事,我的生活很平淡,沒(méi)有故事。”50多年的集體生活對(duì)一個(gè)人的影響,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夠更改。在過(guò)去,每個(gè)工人都認(rèn)為自己處在集體里面,是這個(gè)集體的一部分,是機(jī)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而今天,當(dāng)他們?cè)僖膊挥门c其他幾千、幾萬(wàn)工友穿著同一款工裝,在同一個(gè)時(shí)間擁進(jìn)廠門(mén)的時(shí)候,當(dāng)他們坐在各自的客廳里,講述自己的生活的時(shí)候,這是一些活生生的個(gè)體。但是把話題帶入個(gè)人的講述,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它讓我知道,過(guò)去的體制生活是多么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guó)人。
每一次訪談將要結(jié)束的時(shí)候,都伴隨著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沉默。我一直在想:在這些工人師傅講述之余,在他們停下來(lái)不說(shuō)話的時(shí)候,又有多少驚心動(dòng)魄的記憶隱沒(méi)于沉默之中,那些沉默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小 吉摘自山東畫(huà)報(bào)出版社《二十四城記——中國(guó)工人訪談錄》一書(sh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