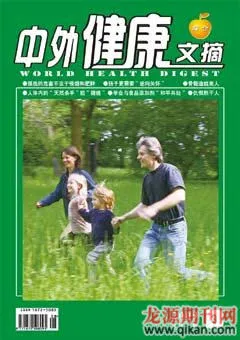當與死神謀面時
陳 彤
“你最害怕什么?”如果你在兩年以前問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絕對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會跟你說,我最怕沒有錢花、沒有事做,我怕老、怕丑、怕失去朋友。當然,這些事情依然是我今天所擔心的,但已經不是我的最怕——我最怕的是失去健康。
幾乎眨眼之間,我的生活轟然倒塌,像一場生命的“9·11”,事先沒有任何征兆——前年7月,很尋常的一個星期天,按計劃我第二天就要飛赴泰國度假。我坐在露天咖啡座上,想到新書馬上要在海外發行的時候,突然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眩暈……
我完全沒有準備好——在最短的時間內,我先是被告知懷孕,然后被告知孩子保不住了,再后來被告知生命危在旦夕——我還沒有來得及為懷上孩子欣喜,就被推進了手術室;我還沒有醞釀好情緒為失去孩子悲傷,就必須鼓足勇氣面對自己的生命難題——我得的是什么病?什么叫“惡性滋養細胞腫瘤”?必須化療嗎?最短要幾個療程?最長還能活多久?
我原來以為我會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我錯了,因為我低估了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同時也高估了自己對生命的達觀。
我問大夫,如果不治療,我有自愈的希望嗎?大夫說有,萬分之二。一萬個人中,有兩個可以自己康復。
其余的呢?全死了。
如果肯治療,一定能好嗎?不一定,但至少有50%的希望。
我怕打針、怕疼,怕天天躺在病床上任人宰割,怕口腔潰瘍,怕頭暈惡心,怕給親人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更怕因為生病而失去朋友,遠離社會……但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
我在醫院的入院須知和治療方案上簽了名字——我同意住院期間,不邁出醫院大門一步,我同意化療,我對化療所產生的一切副作用都接受——不接受又怎么辦?誰讓我貪生怕死!在所有人都叫囂著提升“生命質量”的時候,我卻在為延長“生命數量”而苦苦掙扎。
孩子沒有了,工作沒有了,銀行卡里的數字瘋狂下跌,并且沒有絲毫反彈的跡象;頭發掉光、皮膚失去光澤,以前天天見面的快樂朋友越來越少,四周看來看去都是和自己一樣穿著病號服,連說句話的力氣都沒有的腫瘤患者……
這樣暗無天日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去年2月。
醫院大夫把住院病人結束治療叫“畢業”,但他們不肯給我“畢業證書”。他們只同意讓我“肄業”——停止所有治療,回家休息,定期檢查,如果不復發,那么就算獲得“同等學歷”。
于是,我開始了新的怕——我幾乎每次去“隨診”,都會碰到一個新的復發病人——我去問大夫,為什么會復發?我會嗎?
大夫說,如果他知道為什么會復發,誰會復發,他就能得諾貝爾醫學獎了。
不過他勸我——你不要試圖預支痛苦,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健康人,快快樂樂的。如果不幸復發,到時候再說,總比從現在開始就整天擔心要好吧?
也許,他說得是對的。怕,是最沒有用的。
文/陳彤
劉紅苗摘自《南國都市報》